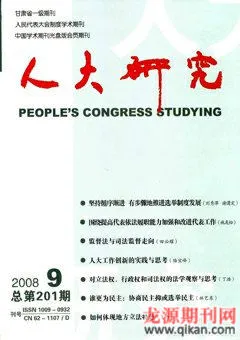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巡警式监督与火警式监督
2008-12-29谢艳杨君
人大研究 2008年9期
一、巡警式监督和火警式监督的提出
在现代民主社会,立法机关把大量的政策制定权授予行政机关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授权的结果,学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亨廷顿、尼斯坎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信息和专门技术,而立法机关的成员往往不具有这种信息和专门技术,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偏好不一致,那么行政机关的政策方案就可能偏离授权的目标,甚至使得新方案比现状更加糟糕,于是立法机关的授权实际上就成了弃权。以麦克宾斯、施瓦茨、温格斯特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立法机关的监督、预算、行政程序等手段足够用来减轻授权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
最早提出巡警式监督和火警式监督这一对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马休·麦克宾斯(Mathew D.McCubbins)和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在他们提出这对概念之前,有很多学者抱怨,立法机关授权之后正在忽视它们的监督职责,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它们几乎失去了控制。但麦克宾斯和施瓦茨却认为,立法机关表面上看是无所作为,抛弃了它们的监督职责,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更加理性和有效率的监督方式而已,即监督方式从巡警式监督转向了火警式监督[1] 。
根据监督的启动机制不同,以及立法机关在监督过程中的主动性、集中性、直接性不同,可以把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分为“巡警”式监督和“火警”式监督。
巡警式监督是指,立法机关如同巡逻的警察一样,积极主动地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以查明其是否违反授权目的,并对违法的行为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立法机关审查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查阅文件、进行实地考察、询问、质问、举行听证会听取官员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等等。巡警式监督具有权力集中、主动、直接等特点。
火警式监督是指,立法机关无需主动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授权的目的,而是通过建立一套规则、程序以及非正式的惯例,赋予单个公民和有组织的团体一定的权利,使他(它)们可以审查、检举、揭发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包括预期违法行为)和其他目标偏离行为,立法机关或其他国家有权机关根据公众的报警而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在立法机关建立的这套规则体系中,有的规则为公众提供了信息知情权和行政决策的参与权,有的规则为公众提供了向上级行政机关、法院、立法机关申诉的权利,有的规则赋9ndGaBW5BiRDDl7D9shbRA==予了其他国家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还有一些规则有助于分散的公民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而立法机关的角色主要在于创建并完善这套规则体系,偶尔也对公众的抱怨和申诉进行积极回应。麦克宾斯等人为火警式监督做了个形象的比喻:“(立法机关)不用到处巡视火灾的情况,他只要在街角放一个火警报警器,在附近建一个消防站,有报警的时候分派一下吊钩和梯子就可以了!”
火警式监督与巡警式监督各有特点。巡警式监督集中、主动、直接,有利于追踪行政官员的行为。但是对立法机关而言,火警式监督虽然不如巡警式监督那样集中、主动和直接,但它具有成本上的优势,因为立法机关以外的当事人分担了部分成本。这也是麦克宾斯和施瓦茨认为巡警式监督比火警式监督更优的基础所在。针对学者对立法机关忽视监督职责的批评,麦克宾斯和施瓦茨争辩说,立法机关看似忽视了自己的监督职责,实际上是选择了火警式监督这种更加有效率的监督方式而已。
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缺陷。巡警式监督的缺陷在于它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成本高昂,因而导致立法机关不可能大量实施这种方式。火警式监督的缺陷在于火警可能出现不真实、不可靠的情况,这些不真实的警报会误导立法者,使得立法者很难区分真实的和虚假的情报,从而导致火警式监督失灵。就像麦克宾斯自己所说的那样:“那些被赋予报警机会的人同时也获得了一个通过报警欺骗立法者从而获利的机会。总之,错误的警报随时可能发生。”[2]
二、巡警式监督与火警式监督有效实施的条件
巡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要求立法机关有足够强的监督能力,包括立法机关应该有充足的预算,以及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专业知识过硬的人员队伍。而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不仅依赖于立法机关自身的权威,而且依赖于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因此,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比如公众参与的愿望和能力,其次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制度,在此规则制度之下,公众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具体而言,这些规则制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普通公众“报警”的前提是,他必须获得有关行政机关违法或违反授权目的的信息,但行政机关和普通公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普通公众明显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赋予公众通过查阅、复制、下载等形式利用政府部门信息的权利。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敦促行政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其中影响最大、体系最完备的莫过于美国国会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1974年制定的《隐私权法》及1976年制定的《阳光下的政府法》。《情报自由法》规定政府文件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除国家机密信息等可以不公开的九种情形外,政府文件都应公开;一切人都具有了解政府文件的同等权利,任何人均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查阅、复制行政情报;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政府文件,公民或社会机构可诉至法院寻求救济。《隐私权法》则赋予公民对个人信息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和政府官员最低程度的隐私权。《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目的在于让公民充分了解联邦政府作出决定的程序。我国也有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但散见于不同级别的法律文件中,且大部分规定信息公开的文件效力层次较低[3]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广,获取信息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廉,这将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2. 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还需要保障公众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权。公众仅有知情权是不够的,因为缺乏参与权的知情权仅仅是一种信息的单向传输,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决策的结果,不利于事前预防和控制行政机关的违法与偏离行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可以解决以下控制难题:首先,在多方利益群体参加决策过程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决策相关的信息,因为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会把所有的信息披露出来,基于充分信息的决策才可能更加理性和科学。其次,通过公众参与程序,使得所有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来,这样行政机关面临的环境更接近于立法机关面临的环境,即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直接体现了政治上占优势的政治力量的利益,确保了立法决策和行政决策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公众参与程序将立法决策面临的政治环境“映射”到了行政决策过程中,使得行政决策更真切地反映立法机关的授权意图。最后,公民的参与还能提升公民对决策结果以及对政治制度的满意度,从而保证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执行。为保障公众的参与权,立法机关往往制定一些程序性规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或作出某项行政决定时,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例如,美国1946年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为行政立法过程设定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程序,即通常说的“听证程序”和“通知与评论程序”,这两种程序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权利、扩大政治参与、增加行政公开透明度。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法律也设立了听取公民意见的各种制度。
3. 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要求立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注。火警式监督的运作机制是,立法机关并不主动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而是根据有关行政相对人的举报或申诉来启动审查和救济程序。然而,公众的利益并非一块整石,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表达能力是有差别的。对于那些组织良好的强势利益集团,火警式监督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绝好机会,而那些弱小的、利益分散的群体的声音很可能被湮没。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维系社会体系的健康、顺利运转,需要立法机关有意识地采取倾向性措施,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适当“照顾”。这些措施包括:立法机关必须保证分散的公众有足够的利益诉求渠道,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游行自由等,由于他们人数的众多,采用这些方式也更有利于引起有关人士和权力机关的重视;立法机关应加强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并赋予代表其利益的中介性团体组织以法律上更高的地位和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 [4] 。
4. 火警式监督的有效实施还依赖于对说谎者的惩罚机制。巡警式监督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披露信息的渠道,也为立法机关获取信息提供了一个相对廉价的渠道,但是,报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撒谎,从而导致立法机关无法准确辨别信息的真伪,也难以判断行政机关的方案是否偏离授权目标。如果存在一个对撒谎者的惩罚机制,那么报警者撒谎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且立法机关还可根据报警者提供的信息准确推测行政机关的方案是否偏离授权目标。惩罚机制的存在改变了报警者的成本—收益计算,除非撒谎的收益大大高于撒谎所付出的成本,否则报警者没有撒谎的动机。对撒谎处罚的力度越大,报警者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就越高。根据报警者提供的信息,立法机关可以更加准确地推测行政机关的方案和现状之间的差距。关于惩罚机制在火警式监督中的作用和运作机制,麦克宾斯等人在《从监督中学习:火警式监督和巡警式监督的重构》一文中给出了详细的论证 [5] 。
5. 火警式监督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立法机关的权威性。火警式监督是由公众启动的,但公众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惩戒的强制性权力,而要依赖于立法机关对这些申诉的回应。当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申诉时,立法机关应该有强有力的救济方式,这种救济可以由立法机关亲自参与,也可以授权其他机关。但无论是哪个机关采取救济方式,这种方式的法律后果必须足以震慑违反法律和授权的机关和个人。如果行政机关违法和偏离授权目标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戒的话,“报警”的公众的积极性将会受到严重打击,从而导致火警式监督的失灵。由于立法机关在宪政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各国立法机关都拥有一系列制约行政机关的资源和技术,例如财政拨款权、对高级官员的任命权等等,只要立法机关的成员们能够同心协力,完全有充裕的资源对行政官员进行奖励或者制裁,从而引导他们按照立法机关的意图行事。温格斯特(Weingast)和莫兰(Moran)曾经对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的行政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政机关的行为随着国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偏好的变化而变化[6]。这充分说明了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两种监督机制对我国人大监督的启示
从法理上讲,我国人大具有至上的权力和最高的权威,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大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人大的监督效果离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为树立人大监督的权威,健全人大监督的机制,各级人大和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人大监督不力的原因,指出了完善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路与方法,如设立人大专门监督机构、建立督察员制度、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制度、引入公共预算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制定了《监督法》,该法规定了听取汇报、质询、询问、检查、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措施的内容和程序。但是,不管是学者提出的改革建议,还是《监督法》规定的监督措施,基本上可以归入巡警式监督的方式。虽然这些建议和措施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对特定的事项能起到明显的效果,但局限性是明显的。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大代表数量相对较多,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代表都是兼职代表,这些因素决定了巡警式监督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人大要真正担负起监督的重任,除了完善巡警式监督的各项制度外,还要注重对火警式监督机制的应用。
事实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火警式监督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大大增强,人权和法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公民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愿望日益强烈。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中窥见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比如,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治理理论的兴起、非营利组织研究的蓬勃发展等等。火警式监督机制的提出顺应了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且与人大监督权的治理范式[7]相吻合。在现实生活中,也涌现了一些成功运用火警式监督机制的案例,例如,人大与传媒携手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监督[8] 。但是,从总体上讲,火警式监督机制还未能得到大量的实施,其优势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诚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火警式监督除了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但目前许多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火警式监督的优势,人大应该为火警式监督机制的实施创造各项条件。首先,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新闻自由法》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保障公众的信息知情权、行政决策的参与权、信息披露的自由权,以便最大可能地动用社会监督资源。其次,赋予司法机关更多的审查权,保障“报警”的公众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最后,完善对弱势群体的各项援助制度,保障他们的话语权,防止火警式监督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公平。
参考文献:
[1] Mathew D. McCu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