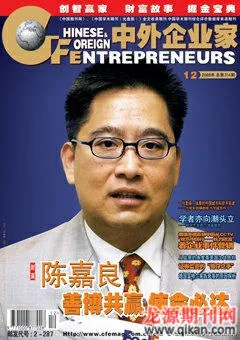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2008-12-29王旭宏淦晓磊
中外企业家 2008年12期

社会资本原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术语,在社会学那里,社会资本基本上指的是人们通过社会交往(往往是直接的)而形成的某个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如常见的家庭、家族、街区、社团,以及朋友熟人关系等人际交往网络,网络成员在这些交往网络中可以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短缺资源(布朗,2000)。近年来,社会资本跨越了社会学,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资本理论将价值观、文化、历史和道德规范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使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因的解释跳出了传统的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的窠臼,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和规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一、社会资本的提出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谁开始的,社会资本的界定还没有一致的观点,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开始的。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李惠斌、杨雪冬,2000)。因此,布尔迪厄成为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这也是目前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占主流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Na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赵延东,1998),尽管他们当时用的是“社会资源”而不是“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还有人认为,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例如,在对市场运行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市场的成功运行不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还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明确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李惠斌、杨雪冬,2000)。因此,我们倾向于用这句话来概括,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思想早已有之,但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二、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
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成了许多学科关注和分析的重点,其中对社会资本研究最出色的两个领域,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企业家伦理的“新经济发展社会学”,另一个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研究。这里,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科尔曼在其巨著《社会理论的结构》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在他看来,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以下三种资本:其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其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其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赵延东,1998)。普特南的研究则完全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意大利近20年的实证研究,在1993年出版了《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对其研究发现进行了系统阐述,其结论是社会资本影响制度的效能,社会资本的不同造成了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在这本书中,作者尽管对这种新的资本形式没有实现概念上的创新,但是他通过20年的研究,从经验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对政府效能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使得社会资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普特南发表了《孤独的投球手: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等一系列论文,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资本的大讨论,其中心思想就是围绕美国社会信任是否在丧失,公民参与是否在衰落,社会核心机制是否在削弱,以及公共道德是否在受到侵蚀等问题展开讨论(李惠斌、杨雪冬,2000)。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
遵循着西方学者的传统,我国学者则从个人和集体层次或者说是从微观和宏观层次来定义社会资本。边燕杰是从个体层面上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他认为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2004)。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张文宏,2007)。有的学者则认为对社会资本不应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如刘林平(2006)区分了社会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动用的、用来投资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但是不一定就是直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蕴涵在关系网络之中,表现为通过关系网络借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关系网络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它的成本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构建关系网络的投入或费用,即网络中的交易费用。因此,他不同意将社会网络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资本。
在文化和人类学界,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历史遗产,它来自长期的文化积淀(Dore,1987)。现在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们之间普遍的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Putnam,1993,1995;福山,1998;Colman,1998;科尔曼,1999)。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也认为人格因素、人际关系等对新人的形成也有影响(怀特利,1999)。
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资本跟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往往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社会资本的结论(Kreps,1986;Fudenherg&Tirole,1992;张维迎,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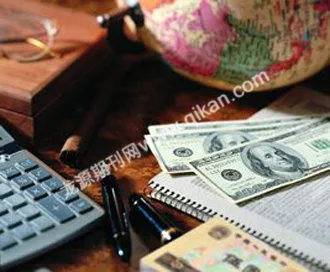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重大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非正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作用于人际网络关系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在脱贫中具有其他资本类型所没有的独立性,贫困者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将其转化为经济或其他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市场就充斥着假电器、假烟酒到现在的假棉被、假米、假药、假化肥以及最近的中国乳制品业添加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事件,一轮打假事件结束一轮又起,产品从日用品到关乎百姓健康的产品,不仅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社会效应,人们对社会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目前造假不仅仅限于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大量的上市公司有组织地报表造假,虚报业绩;在建筑市场上,“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今年的汶川大地震我们就因为学校教学楼不合格工程使得多少青少年丧失宝贵的生命;在劳动市场上,假合同、假雇佣、拖欠脱逃工资现象严重;在学术界,论文抄袭、学术造假使得整个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充满了商业化的气息;在教育界,买卖学历、文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荣誉和政绩,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种现象都是社会诚信缺乏的结果,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张维迎,2001)。
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福山,1998)。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同时,按照这些经济表现,一种文化或社会可分为高度信任度和低信任度。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而根据一些理论预设和实证观察,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被认为是最缺乏信任的群体之一,被经常提及的证据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小,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由家族经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人格化色彩。目前,针对中国社会资本偏低的事实对经济的实证分析的研究国内并不多见,张维迎、柯荣柱利用中国的跨省调查数据,通过解释不同省份之间信任度差异的来源解释中国人的信任机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中国是低信任的,并回应了有关信任和经济绩效的相关研究;刘江会、宋瑞波通过对证券市场中券商违规失信的研究分析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缺乏信任的不良经济行为。但由于这些经济学者研究目的和范围的局限,他们并未从宏观上把握深入研究社会资本偏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