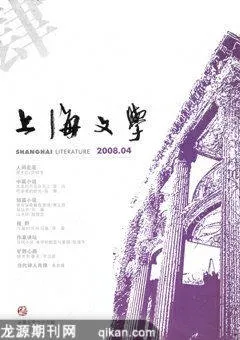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下)
2008-12-29蔡翔
上海文学 2008年4期
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干部和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者说,任何一种形式的“动员”都必须依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动员—改造”的叙事结构中,都会出现“干部下乡”或者“知识分子下乡”这样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开头,乃至成为小说情节的叙事动力。但是,“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在动员群众的同时,自身又往往会成为群众改造的对象,而这样一种悖论性的现象,恰恰表征出中国当代极其复杂的政治乃至文学想像。
三、 干部
小说《战斗的青春》中,写枣园区区小队露宿野外,区委书记许凤“悄悄地起来把棉袍给她们三个姑娘盖好。一看李铁也查了哨回来,蹲在旁边给人们盖棉袍”。
“盖棉袍”这一细节似乎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相似的细节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办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①
从政治想像到制度实践,再到小说虚构,这一细节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文学隐喻。当然,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细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一细节蕴含着的,是对干部,也即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管理者的某种想像。
这一想像,乃至想像的具体实践,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震撼力或者凝聚力量,是很难低估的。这一力量,显然在于,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政党政治通过“干部”完成对群众的动员和改造,因此,干部在这一结构中所承担的功能即是非常显著的,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者甚至治理者。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整理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廿六、廿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而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尽管国民党俘虏兵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即使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者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其中,一个十五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的道理我又懂得了一些”。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综合这些资料,部队士气高涨的原因除了政府确实照顾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等等,还和官兵平等,尤其是干部关心群众有很大关系。②
导致这一对“干部”的想像乃至具体实践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对平等的乌托邦诉求却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传统中国确实将所有人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政治或宗法),那么,革命所要首先摧毁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或宗法制度,同时,为了防止一种新的官僚制度的复活,就必须对“干部”进行重新的想像。而在这一想像过程中,文学也必须相应地重新编码乃至进一步地虚构。
《山乡巨变》写刘雨生担任农业合作社社长的第一天,千头万绪,“这时候,又围上一大群妇女,……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吵吵闹闹,对刘雨生提出各色各样的要求和问题。‘社长,你说怎么办哪?我又丢了一只鸡。’‘社长,我那黑鸡婆生的哑巴子蛋,都给人偷了,偷的人我是晓得的。他会捞不到好死的,偷了我的蛋烂手烂脚。社长,帮我整一整这个贼古子吧。’‘刘社长,我们那个死不要脸的,昨天夜里又没有回来,找那烂婊子去了。’”这一细节的出现是非常有趣的,刘雨生不仅要管理农业合作社的“大事”,还得处理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在当代文学中,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细节,相反,在许多的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类的干部形象,梁生宝的合法性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贫苦乡民的关心并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行动上。而关心群众生活,也历来是革命政治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之一。对群众生活的关心,不仅仅是由此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同时,也即把政治延伸到群众的私人生活领域。实际上,在当代社会,并不存在公共/私人之间绝对的分治,而是始终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将公共和私人这两个领域积极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即是所谓干部的存在。而在干部身上,始终体现出的,则是一种“国权”。一方面,经由干部体现出的“国权”向私人生活领域的延伸,的确表达出一种政治控制的意图,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时表达出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照顾和关心。忽视或者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遮蔽这一时期政治的整体性或者复杂性。而处于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干部,其意义或者功能就远不是现代科层制中的“官员”这一概念所能解释的。这一干部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对记忆犹新的旧官吏的颠覆,而另一方面,则又多少延续了某种传统性的想像,比如古代的“循吏”。《儒林外史》写萧云仙在青枫城,便是先动员百姓开渠、垦田、植树,生活小康之后,又请儒生来此办学,实行教化,实施的正是儒家“先富后教”的政治文化设想,也是“循吏”在文学中的理想性延伸。而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强调:“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甚至设想:“(农民)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③显然,在当代中国,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通过战争、运动等“大事”体现出来,同时也渗透在群众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中。
也许,另一类细节也同样值得注意,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是,当工作队完成了对乡村的动员—改造的任务后,治理乡村的任务即交给了本土出身的干部,在《暴风骤雨》是郭全海,在《山乡巨变》则是刘雨生。这一权力的移交,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信任,同时也包含了政治和乡土社会的某种默契和认同,就像盛妈对邓秀梅所说:“这都是劳烦你们操心,替我们挑的一批牢靠的角色。社一办起来,大家都只问主任要工作、要饭吃,吃饭的一屋,主事的一人,没有刘主任这样舍得干的人,我们是难放心的。”像刘雨生“这样舍得干的人”普遍出现于当代文学之中,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等。这一“舍得干”同时包含的是“公而忘私”,是“舍小家,为大家”。我以为,这不仅是政党对其组织成员的要求,而且,这一要求因为基层干部的本土化,多少还表现出宗法社会的某种功能性转换。或者说,这一根植于宗法社会的对领导者的理想性诉求被革命政治有效地吸纳,并转换为一种新的“带头人”形象。而正是这样一种兼具宗法社会功能的“带头人”(本土干部),才能获得乡土社会的高度信任。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当代社会,乡村干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官员,但是国家却依靠这一类干部,有效地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并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政治结构之中。而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乡村,即使在城市,工厂的干部也在开始完成科层制的转换,这一转换也相应激发出对干部的另一种理想性的想像。比如,在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描写“漕阳新村工人住宅造好之后,沪江纱厂也摊到四户”,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余静“也分配到一组,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肯要,因为细纱车间工人多,这一组也交给细纱间,经过讨论,这一组便分给秦妈妈了”。而余静也正是经由这样的行为,获得工人的信任,获得信任的,同时也是革命政治。显然,在革命中国的政治设想中,首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干部的高度的献身精神,从而完成国家对基层的重组乃至重建。
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一觉悟,才是衡量一个干部的最为根本的标准。几乎在所有的当代文学中,干部的落后乃至堕落,都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的丧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如此,《创业史》中的郭振山也是如此。因此,这一干部在理论上又是极其现代的,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而绝对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利益集团。当我们强调宗法社会的某种功能性的转换时,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的复活,恰恰是,由于强调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这一关心就有可能导致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就其根本,国家利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罗丹《风雨的黎明》④,在描写解放前夕的鞍山钢铁厂时,就反复强调了地方主义对革命政治的危害性。而在1960年代,扬剧《夺印》(包括后来改编的同名电影),就是围绕“私分稻种”展开叙事,而所谓“私分稻种”正是在关心群众利益的名义下的行为。显然,这一高度政治化的干部,保证了国家“政令通畅”,同时又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乃至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赢得基层群众的信任,而“关心”的形式则使政治延伸到中国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一“干部”形象地解释了什么是革命中国的“全能政治”。在这一意义上,革命中国所致力根除的,又正是传统社会“有限的地方性”。
正是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干部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既要承担“动员—改造”的政治任务,同时又必须将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的统一愿景之中,因此,塑造“好干部”就成为当代文学必须致力的任务之一。当然,这一“好干部”最终通过“焦裕禄”这一符号被经典地表达出来。
如果说,当代文学通过这一类“干部”,也即社会主义“带头人”的形象描述,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官员”的想像,并试图以此来重新结构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么,它的另一个任务则必然是对现实中的另一类“干部”进行批评乃至批判。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文学主题。
恰如我在上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现代政党,因此,它势必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任何一种形式的地方利益集团包括由此派生的地方主义,都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1959年出版的《风雨的黎明》再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鞍山解放初期的混乱状况,而这一混乱状况实则正是因为各个部门(利益集团)的乱拆乱搬所造成。小说正是通过宋则周、易秋繁和娄堃华、臧冲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再现了一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地方主义或者地方利益集团,在当代文学的表述中,更多地以另一些形态出现,比如地方利益常常被归结为官员的个人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则被描述为某一政治派别,而这一派别或者是错误的政治路线,或者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说,这一描述往往是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的。这一描述固然有其政治的原因,而作为叙述者,却也同时含有“反官僚、反特权”的理想性冲动。这一冲动不仅来自于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同时包含了对未来的统一的国家制度形态乃至政治生活的想像。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收录了二十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重点批判的短篇小说,其中涉及干部和群众关系的有十二篇。而姚文元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⑤,重点批判了所谓的“反官僚主义”,其中既有冯雪峰、徐懋庸等人的言论,比如,徐懋庸当时特别强调:“官僚主义既然还有,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能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充分享受民主的形式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也有涉及“反官僚”主题的小说,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等。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反官僚主义”和“揭露阴暗面”被有意识地等同起来,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歌颂”与“暴露”的历史论争借此获得了现实的延伸。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的另一段叙述:“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踞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的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间必遭覆灭的命运,批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官僚主义,当然也应当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在此,姚文元把“揭露”的合法性只是限定在对社会主义“外部”(“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之中,同时把官僚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官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或者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产生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社会现象,所涉及到的,已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那么,所谓的“继续革命”就将失去它的理论支持。尽管“继续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局势乃至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它实际包含的恰恰就是80年代展开的“异化”问题的讨论。而我下文可能涉及的,则是在60年代,这一问题如何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重新展开讨论,而所谓“官僚阶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而我以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隐藏着的,可能正是对“现代性”,包括“科层制”的某种焦虑,所谓科层制,正是包含了官僚化与专业化两个特征。
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党内高层从未放弃过对“官僚主义”的思考甚至由此引发的焦虑,即使中国作家在某种政治压力下,也没有因此拒绝“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某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一直贯穿于中国作家的写作之中。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这一“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尽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少中国作家也因此获罪,但是,这一主题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去,而且,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写作模式。
如果我们将《重放的鲜花》中的某些作品置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加以考察,那么,这一时期的“反官僚主义”的写作,应该说,仍然是相对温和的。在许多的作品中,这一“官僚主义”仅仅被叙述成为一种“作风”问题,这一“作风”问题既有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原因,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等等;也有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脱离群众的现象,比如刘绍棠《田野落霞》、李国文《改选》,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对“阴暗面”(姚文元语)的“揭露”,仍然遵循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也就是说,仍然被严格限定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政治范畴之中。
但是,1958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一类“干部”的批评,已经远远超出了“作风”问题,也不是仅仅用“官僚主义”这一概念就能解释的。或者说,对“阴暗面”的“揭露”,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逐渐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尤其是在60年代。尽管这一对“阴暗面”的“揭露”必须依托“正面人物”的存在,而且往往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但是,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中,仍然若明若暗地延续着1957年的“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然,这样一种结构也同时受制于另外一些政治因素乃至作家自身的思想深度的制约。
在此,我想顺便提及“隐蔽的写作”或者“文本的隐蔽性”这一可能并不十分规范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于某种政治压力的存在,写作者不得不将自己真正的个人的思考隐蔽在一种“正确”的政治叙述之中。这一思考有可能来自于理论的启发,也有可能源于对实际生活的观察,而后者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尤为主要。
在赵树理的《三里湾》或者柳青的《创业史》中,相继出现了范登高和郭振山这两个“干部”形象。在“土改”时期,这两个人物曾经是乡村革命的积极的推动者或直接的参与者,也因此,他们占据了乡村政治权力的核心位置,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成为这一政治权利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这一利益,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三里湾》含蓄地写范登高“就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范登高老婆解释说:“其实也没有高了些什么,只是分的地有几亩好些的,人们就都瞎叫起来了”)。实际上,在更早的作品,比如《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已经深刻地涉及到中国乡村革命中的这一既得利益的“干部”群体,而这一群体极有可能成为乡村中的新的权力压迫者。而在《三里湾》中,进一步的解释则在于,这一“既得利益”实际上帮助了范登高“原始资本”的积累,用马有翼的话说,范登高用以商业活动的那两头骡子“那时候不是没人要,是谁也找补不起价钱。登高叔为什么找补得起呢?还不是因为种了几年好地积下了底子吗?”而这一“原始资本”的获得乃至继续的积累,则可能使这一群体形成乡村中新的利益集团,并开始背离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要求,按照郭振山的话来说,就是“人们都该打自个儿人过光景的主意了”。这一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动员”结构开始出现断裂现象。柳青在《创业史》中,反复描写了在郭振山那里,“政令”如何不畅,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郭振山“自个儿人过光景”,逐渐失去了乡村社会的信任。显然,赵树理和柳青的焦虑,有着明显的现实原因的支持,⑥而干部问题,直接影响的,正是“动员”结构的完整性。这一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是中国革命有无可能产生它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并进而构成一个新的官僚利益集团。
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史的演化过程中,“土改—合作化”是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历史/现实”故事,而这一故事的被反复讲述,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一故事集中了太多的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它既涉及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内含的自我否定性,以及这一自我否定所带来的结构内部的紧张、对峙、矛盾、冲突,也涉及到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彷徨、苦闷、失落,以及新的希望的寻找;既涉及到被解放出来的个体如何面对新的风险机制的挑战以及作出怎样的回应,实际上,这一主题已经存在于现代文学的叙述之中。在鲁迅,正是以“娜拉走后怎样”作出了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而当代文学则以“集体化”的方式重新回应了这一现代性的主题,同时,这一过程也涉及到这一历史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干部”问题。显然,所谓的“动员”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随着“动员”的政治内涵的变化,从而必定要求“动员”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为了保证“动员”的有效性,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再次被凸现出来。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即使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是,这一主题为什么仍然会反复出现,而且,逐渐地激进化。当然,这一主题的写作,在50年代,应该说,仍然显得相对温和,并没有将其上升到“敌/我”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只有到了60年代,才基本完成了这一主题的激进化的叙事。而标志性的作品则是《艳阳天》、《夺印》,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艳阳天》看作是对《创业史》的进一步续写。小说所要描写的时间已经从农业合作化的早期延续到了这一运动的成熟阶段(高级农业合作社),而故事的核心则是围绕“土地分红”展开了东山坞的冲突和斗争。相似的细节实际上也出现在《夺印》之中,比如其中的“私分稻种”。这一故事的核心事件所涉及到的正是所谓的“分配”问题,而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恰恰是革命中国所要致力于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制度的重新订立,更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冲突。当然,无论是在《艳阳天》,还是《夺印》,这一“分配”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国家”的利益。在1949—1976年中,中国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着意从农村汲取资源,这一点,已有学者详细讨论,并成基本共识。在这一资源的汲取过程中,任何一种地方主义或者地方利益集团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干部问题,尤其是农村干部问题,便会被反复提及,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政令”是否通畅,还包括共同体的建构以及领导权问题。显然,在分配问题上,“东山坞”已经面临经由合作化运动重新建构起来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问题,这一分裂的可能性通过东山坞的“沟北”和“沟南”的空间冲突而被形象地再现出来。但是,村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围绕“土地分红”展示的阶级冲突,包括延伸出来的“资本”(土地)和“劳动”(人力)的意识形态冲突。应该说,这两个层面既涉及到了现实问题(国家/地方),也涉及到了历史问题(阶级/政治),当然,小说在这两个层面的叙述很难说是深刻,甚至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国家利益,而完全忽略了群众利益。⑦这既受制于作家个人的思想乃至学识修养,也为那一时代的整体性历史背景所限制。当然,我在此想要讨论的只是和本文主题相关的马之悦这个人物。
如果我们把马之悦放在范登高、郭振山等这一人物谱系中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将发现,马之悦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概念开始进入“干部”这一群体内部。因此,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就不可能仅仅只是官僚作风、个人利益、错误的思想观念等等的斗争,而这一冲突则构成了《三里湾》或者《创业史》主要的叙事模式之一。但是在《艳阳天》中,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却是高度政治化的冲突,这一冲突又以“权力”的争夺为其核心表征。与小说中的另一人物马连富(生产队长)相比,马之悦支持“土地分红”的原因并不是“沟北每一户给……添个斗儿八升的”。马之悦的志向不在于此,马之悦要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东山坞的统治模型,这一模型实际上暗含的是一种地方官僚政治为主导的乡村权力结构。实际上,早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已经开始思考在乡村消灭了地主阶级以后,有无可能出现新的利益—压迫集团,而这一新的利益—压迫集团极有可能由官僚政治构成,应该说,赵树理的思考以及相应的表述是极具前瞻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够那么突出的原因之一。浩然的贡献则在于,他把赵树理的思考延伸到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历史语境在于,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包括以后的人民公社,其基本的构成单位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村社的共同体形态,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传统的消灭并不是非常坚决也不是非常彻底的,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这一传统的村社共同体形态的保留,便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地方官僚政治,而这一权力结构的模式可利用的资源也仍然可能是多重的,比如残余的宗族结构包括文化心理的积淀。因此,在《艳阳天》的“阶级斗争”的叙述模式中,我们也依然可以感觉到宗族冲突的痕迹(比如“沟北”和“沟南”的空间冲突以及马、韩等种姓之间的斗争)。应该说,浩然对此问题的涉及,已经关联到社会主义制度(包括这一制度的构成形态)本身有无可能产生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坦率说,在这一方面,浩然的思考并不深刻,或者说,有意回避。浩然的解释更多地纠缠于历史原因,比如在《艳阳天》第一部的第六章中,叙事者详细地解释了马之悦的个人历史,并以此说明马之悦连革命的同路人都不是,“马之悦根本没抱过什么革命理想,也就不存在(革命)到头不到头的问题了”。这一点,根本区别了《三里湾》中的范登高,或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甚至《山乡巨变》里的谢庆元。因此,马之悦的个人历史极其容易地使叙事者将他定义为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这一定义同时自然地使叙事者过分夸大历史或外部的原因,比如地主马小辫的存在。显然,马小辫在小说叙事中具有真正的重要性或者成为这一解释模式的主要的理论依据。马之悦—马小辫的结构性存在,才决定了这一故事如何成为“阶级斗争”的故事,而萧长春和马之悦的冲突也自然成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逻辑性的延续,并因此获得自身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解释却又多少显得简单、生硬,同时阻碍了对问题的更加深刻的思考。但是,浩然的解释却成为60年代相关文学的主要的叙事模型。
1963年3月号的《剧本》杂志刊发了七场扬剧《夺印》(后来改编为同名电影)的文学剧本,而这一戏剧的出台显然暗合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在戏剧中,生产队大队长陈广清被描述成为因私心过重而被阶级敌人腐蚀的干部,这一形象已较多地见于当时的作品之中,比如陈登科的《风雷》,其中区委书记熊彬正是因为追求个人的享受而逐渐背离革命宗旨(继续革命包括自我否定),妻子黄美溶则成为熊彬与黄龙飞的叙事中介。而在《夺印》中,更重要的人物则是陈景宜,所谓“想这小陈庄,明是陈广清当大队长,骨子里却是我陈景宜的天下”。而陈景宜这个人又被叙述为过去是“财主的好帮手”,解放后,因为“见风转舵来得快,事事积极在前头”,并且成为“队委”,进入了小陈庄权力结构的核心。这样的叙述,可以明显看到《艳阳天》、《风雷》等共享的结构模式,即“腐化堕落的干部+隐蔽其后的阶级敌人”,这一阶级敌人有时被叙述为历史遗留的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如地主马小辫,等等),有时被解释成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如马之悦、陈景宜,等等)。在这一解释模型中,某类干部实际上成为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而所谓的阶级敌人也仍然是“人还在,心不死”,并形成内外勾结的政治局面。由此,权力问题的重要性被再次凸现出来,并形成一种“危机”叙述。我们暂且不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陈景宜这样的出身有无可能进入乡村权力结构的核心,包括对这一叙事的真实性的质疑。仅就这样一种“危机”叙述而言,由于过分夸大了残余的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这些“外部”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真实性,却多少回避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无可能异化的重要问题,或者说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简单化了。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叙述,尤其是将权力危机的基层化,不仅成为当时主要的文学解释模式,同时还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实践模式,这一模式不仅见之于当时所谓的“四清运动”,也见之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并因此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甚至程度不等的人身加害。⑧
相对于文学家的叙述,政治家的思考要深刻得多,同时也拥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比如,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时,曾多次提及“死官僚主义者”这样一个概念。1963年9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中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1964年7月《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提出了“特权阶层”等概念。当这些概念和方法再次被用于国内情况的分析时,1965年1月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在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至1975年,终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理论断言。⑨导致毛泽东这一理论思考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后来被描述成为所谓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挑战,其中包括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及其决议中,所提出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改革方向,等等。⑩也含有毛泽东对商品经济形态本身的警惕,尽管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针对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的“左倾”观点,批评说“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实现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违反客观规律的”。还进一步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但是,在理论上,毛泽东并没有把商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特征之一,而是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遗迹,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因而必须限制它。因此,他对于用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手段之一,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所以,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再次批评了否定商品生产的看法,却又提出,商品时期搞个三十年,少则搞上十五年。而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再度的深切忧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1}而在围绕这些思考的周边原因中,新中国重新确立的分配体系,尤其是干部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就是近年逐渐被学界重视的50年代开始的“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过程。{12}而在研究者看来,供给制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改变严重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平等社会,正是共产党人发动革命的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更是其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规定和要求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供给制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其本身已经包含了内在的等级差别,而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也极其复杂,既有工作性质不同而存在的特殊需要,也有因为统一战线的背景而需要以此差别来吸引或留住某些人才的特殊考量在内。{13}但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亦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一影响不仅表现在主要领导比一般干部的标准要高出三四倍,同时这一差别也更加等级化并进一步地制度化。这一政策的调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强烈指责,其中最著名的当是1942年春天延安整风之初,王实味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这种规定等于是在推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但是,这些差别在当时毕竟还是十分有限,再加上供给制使公家与个人严密结合,确保了党的纪律与干部的相对廉洁。因此,不仅毛泽东对这一制度屡次表示称赞,朱德在1948年中共准备进城之初也曾明确说过:“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并且预言:“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可是,“新的国家”很快就放弃了这一供给制度,而转向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当然,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而在新的职务等级制度中,“苏联模式”也再次产生了影响。据研究者杨奎松先生介绍,在苏联顾问最早来到的东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将工薪人员划分为十三等三十九个级别,最高和最低工资相差九倍。而中共进入东北大部后,迅速依照苏联模式开始推行工资制,并在激励进步的理由下,开始把苏联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也照搬过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此后欧洲国家程度不等地努力尝试近似的分配方法。但是苏联所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及其党内干部内部的分配差别,甚至大大超过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差距。然而,因为当时普遍相信苏联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从而认为在新的分配制度中,必须扩大各个不同等级的级差系数,才能符合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合理的分配原则。因此,1955年颁布的新的干部工资标准中,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三十一点一一倍之多。同时,有关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苏联的做法,这些做法包括警卫、秘书、专车等等的配备以及住房的分配。{14}从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度的转变,其所包含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杨奎松先生已有详细的论证,至于职务等级工资制度的合理或者不合理性,此处可以不论。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这一职务等级工资制度的施行,显然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当新中国明确了自己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诉求目的时,这一诉求目的必然会导致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而这一方式也自然会相应地要求社会的重新分层,干部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正是这一科层制倾向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上的一种回应方式。然而,这一分配方式又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抵触的,因此,它不仅导致了“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内在冲突,也相应导致了“苏联模式”和“延安道路”的日渐明朗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因为干部可能因此脱离群众,而且极有可能因此而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正是后一点,尤其引起毛泽东的焦虑,他曾再三提醒说:“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而且后者一定占大多数,因此,“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而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则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15}毛泽东所采取的对可能产生的特权阶层的限制措施是否合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毛泽东的这些思考乃至相应的叙述中,实际所涉及到的,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无可能“异化”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而在60年代,毛泽东的这些个人叙述,似乎并没有完全深刻地进入当代文学的写作,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但是,它可能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讨论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政治的时候,并不能把毛泽东的个人叙述作为唯一的解释依据,也就是说,影响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政治的解释力量实际上来自多个层面,甚至多种力量。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1957年“反右”运动给中国作家带来的持续性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中国作家在公开的表述中,大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问题的思考。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当代文学的原因之一。可是,这一“危机”叙述的基层化倾向,毕竟放弃了对制度问题的深刻讨论,而转向残余的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并将其视为最为重要的“危机”原因,这一原因的归纳也相应地使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简单化了。同时,把基层干部作为这一危机的主要叙述对象,也带来了泛危机化的倾向。即使就职务等级工资制度而言,尽管其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低级别的干部的收入并不比普通工人高多少,而在1956年,甚至还低于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平均收入,而大批乡一级工作人员也只是在1955年才被列入国家干部,即享受工资待遇的人员系列中,{16}至于村队干部,则完全被排除在这一系列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说的重要意义的缺失。起码,它触及到了当时,尤其是乡村共同体内部的危机问题,这一问题同样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关联包括,由于村队干部被排除在国家干部(即享受工资待遇的人员系列)之外,他们的收入就和农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的财富的聚集将直接威胁共同体内部的农民的利益,而且这一财富的聚集如果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化)勾连,则可能导致乡村中新的权力阶层的出现,进而可能导致这一新的共同体的分裂。
而问题的重要性仍然在于,由于科层制导致的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一集中同时与高工资、高待遇结合起来,就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官僚化,而这一官僚化的政治将直接威胁非制度化的“动员”结构,包括群众参与的政治热情以及“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
四、 知识分子
在当代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类叙述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毛泽东的“皮/毛”理论,也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焉将附矣”。毛泽东的这一断言,不仅直接取消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政党(或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持续性的改造、批判乃至斗争。南帆在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中,曾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隐形的二元结构,而在这一结构中,“大众”开始成为革命的主体,而知识分子则被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17}。显然,自8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历史上的命运,就成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叙述的焦点,而理论性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因此,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问题,此处可以不论。我在此主要关注的,仅仅只是知识分子在所谓“动员”结构中的位置,包括由此引发的对“知识”问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仅就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且主要是政治命运,便归纳出革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藐视乃至鄙视,并进而总结出中国革命的“反智主义”的倾向,我以为,那是并不完全的。起码,在各种公开的政治文献中,我们仍然能感觉到革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之心,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迫切需要”之心。比如,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中就强调:“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8}。客观地说,这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做得相对成功的,而且,不仅在延安时代,供给制的内部等级差别即有留住某些人才的特殊考量在内,{19}即使在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治批判运动中,也并没有完全取消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物质上的相对的优厚待遇。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在这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原有知识分子”,已经暗含了某些重要的政治区别在内,也就是说,“社会原有知识分子”更多的可能仅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将其理解成某种政治上的不甚信任,也未尝不可。因此,当“大量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对这些“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包括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即成为革命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一改造和自我改造则在1942年5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这一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自我改造所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而我以为,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则可能是围绕什么才是真正的或者有用的“知识”的辩论。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加了三撇……”毛泽东经由这一例子,进而引申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0}而据标语的制作者钟灵回忆,1951年,“有次在中南海勤政厅陪同毛主席,汪东兴对毛主席说: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批评的那位写‘工’字拐弯‘人’加三撇的,就是钟灵。我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挺紧张。没想到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并问我:‘你现在还那样写吗?’我说:‘毛主席批评过了,我哪里还敢那么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都改过来了。’毛主席听了略一沉吟说:‘那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还应该怎么写,狂草、小篆不是更难认嘛,书法作为艺术,还是要尊重传统的。我当初批评你,不是说你写了错别字,而是觉得你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是在向大众作宣传,不该用这种大众难懂的字体写。你有机会见到书法界的朋友们,替我解释一下,隶书也好,篆书也好,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不必受我那篇文章的影响。当然,有时也要看对象,理解我的本意就好了。’毛主席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心中再也没有一点儿委屈情绪了。”{21}毛泽东这一非正式的谈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究竟有无影响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文学,此处可以不论。但是,在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宣传”。
显然,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始终是其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要将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则必须首先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因此,宣传的重要性,也历来被革命政治所重视。{22}而宣传则是需要文化知识支持的,所以毛泽东又曾断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3}这一“宣传”本身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是高度工具化的,因此,被纳入这一“动员”结构的知识也必然会被政治化,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确宣布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也被工具化,“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4}经由这样的叙述,在这一“动员”结构中,所谓“知识”包括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或者独立性,实际上已经很难存在。而重新确立的中心主题,则正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5}。如何重新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并不是我在此要做的主要工作,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此一对知识的政治化乃至工具化的处理,固然造成了对知识包括文学艺术的过于狭隘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高度政治化乃至工具化的知识,又的确有效地完成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比如,陈登科回忆1943年4月《盐阜大众报》刚创刊时,“半月一期,每期只出二百份,没有订户,是赠送的”。后来明确了“走工农兵路线,面向工农兵”的办报方针后,“每月收到来稿一千七八百篇,信四五百封,报纸发行到五千余份。出刊期也从半月刊逐渐改为周刊、三日刊。在广大农村里,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盐阜大众’,每期报纸一送到村里,小学教师和村里的文教委员,就把报上发表的墙头诗,一字一句抄写到农民的墙上。每个村上都写满了墙头诗……‘盐阜大众’上发表的小故事、小通讯,成为农村冬学里的教材。……经常给它写稿的工农兵通讯员有几百个。”{26}当然,这一问题我在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当知识被政治化或者工具化之后,也就必须对知识的定义进行重新的解释,这就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重点强调的:“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哪?没有了。”{27}而那些仅仅拥有“书本知识”的人,在毛泽东看来,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显然,在毛泽东的论述背后,始终存在的,正是“实践论”这一重大的理论支持。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当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它要解决的正是“山沟沟里能否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的理论命题,也就是“延安道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不仅明确宣称:“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同时还从斯大林的论述中寻找到了这一论断的支持:“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这也正是“延安整风”的实际含义之一。但是,这一“实践论”支持下的知识定义的解释,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乃至尔后中国革命对知识的理解。强调知识的实践性的一面,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并以此弥补知识分子原有知识(“书本知识”)的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激发的,正是破除对某些“经典”知识的迷信以及这一“经典”知识的垄断格局,同时,为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知识支持,或者说知识自信。也可以说,在群众的政治性参与的另一面,还包括群众的知识性参与。事实上,1949年之后,曾经普遍化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创新,甚至所谓的工农兵写作,等等,都无不和这一知识的“实践性”的肯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然,另一方面,由此也多少导致了知识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对另一种知识形态(“书本知识”)的轻视甚至批评。{28}
在这一“动员”结构的模式中,对知识的服务性的要求而导致的知识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以及对何谓“知识”的重新解释,必然会进一步引申出对知识的主体,也即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这一改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二是情感。前者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地位,而后者则认为知识分子只有“感情起了变化”,才能进而完成“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9}。从理论到情感,最终要解决的,正是世界观的问题,这一世界观不仅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顺利地完成了自我的转变,我以为,并不能将这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完全叙述成为一种“违心”的行为。我还以为,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上,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拥有着一种强大的解释力量,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在晚清以后众多现代性话语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相对较晚进入但却最终胜出,这并不是“政治—权力”说就可轻易解释的。同时,对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乌托邦想像和相应的社会实践,等等,都可能决定知识分子的立场变化,包括对知识的实践性的认同。当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一改造表示出了某种不适应,某种困惑,甚至某种抵触。这一抵触也不完全是政治的,更多的原因来自于对知识的不同的解释,也即对“书本知识”的固守。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书本知识”恰恰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也即所谓的“学统”。而构成知识分子传统的,也不仅仅是xrzcjL0UZtDxLY4/HjwlBg==知识,它还包括生活方式、心理、趣味、习惯、情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希望在“动员”结构之外,寻找“知识”或“学问”的路径,或者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很多年后,杨绛在小说《洗澡》中,回忆并生动地再现了50年代,她(他)们在这一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所遭遇的种种生活细节。
在重新解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时,钱理群认为,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特别感受到作为知识个体的无力与无用,迫切希望和有力量的人结合起来,融入一个战斗的集体,因此,毛泽东发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是能够得到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和反思的支持的”,而且也是“深得人心的”。但是,“把知识分子视为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对象,不仅外表要工农化,内在的心理、思维、情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得‘工农化’,‘化’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消失。……工农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这一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命题,就变成了单一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命题,工农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蜕变为改造与被改造,一方‘化’掉一方的关系。”{30}我以为,这多少是一种持平之论。
显然,只有在“动员”结构这一模式之中,我们才能明白政党或者国家对知识乃至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的具体的历史原因、意义和内涵。这一要求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一重视有其明确的服务性的要求,也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承担宣传、教育和动员民众的任务。但是,在对这一要求的历史合理性的解释之外,我们必须看到,它所带来的另外的种种影响,除了钱理群所描述的这一历史合理性的“蜕变”现象,对知识的实践性的过度强调,也极其容易把“知识”狭隘化,甚至造成某种对“书本知识”的偏见,而形成这一偏见的,恰恰是某种工具理性的支持。同时,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期待,也必然导致对“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改造、批评,甚至政治歧视。因此,在一种激进的也是极端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导致了教育制度的过于偏激的改革,同时也形成了对1949—1966年的教育的基本评价。{31}
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则是,在这一“动员”结构中,尽管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只能以更加曲折的方式或者干脆以一种主流的政治方式进行表达,这一表达方式形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文本的隐蔽性”。可是,它仍然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丧失,在教育制度上,则是大学自主性的被取消。其结果,则是“文化政治”的“退出”,而按照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中的解释,“真的知识阶级”是必然要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而且,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
结语
我想我应该重新强调的是,这一所谓的“动员”结构事实上只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模式,但是,它却拥有强大的政治能量,包括社会能量。一方面,它是对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对制度的压力,甚至会成为制度的反对力量,尤其是当制度的官僚化和专业化逐渐趋于僵化的状态,或者说,这一高度科层化的制度阻绕了意识形态的想像,甚至本身成为“继续革命”的障碍,这时,所谓的“动员”模式就会对社会进行重新结构,并给政治运动提供一种强大的结构性的支持。
这一“动员”结构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提供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性的前提,则是在这一结构中,肯定了群众的政治主体的地位。而我始终认为,理论包括由此导致的政治想像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可能为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一种强大的行动支持,同时,由于历史情景的变化,这一理论会逐渐趋于“空洞化”的状态,而空洞化的理论状态,恰恰为重新解释这一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可能。因此,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理论包括由此导致的政治想像,才可能深刻地进入历史,包括什么是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尽管这一热情在具体的政治运动中又常常会异化成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可是,这一政治热情的持续性存在,却是一个极需打开的文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一持续性存在的群众的政治热情,给予更为深刻的解释。
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这一“动员”结构片面地理解为一种群众自发性的政治或社会运动,在这一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某种支配性政治,政党或者政党领袖的个人意志构成了这一支配性政治的重要内涵。可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在这一支配性政治的主导下,所谓的“社会运动”因而夭折,或根本不曾存在。吊诡的地方在于,群众往往会通过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合法性的形式,公开或隐蔽地表述自己的利益要求,{32}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诉求,正是社会运动的表征之一。因此,中国的社会运动这一复杂而隐蔽的特征,不仅通过合法的政治运动的形式被表征出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依托了这一“动员”的结构性存在。
当然,政治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根本性的方法或路径,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运动”的意义并不能被高估或被无限夸大。但是,完全离开社会运动的支持,或者说,根本排除群众的具体或物质性的利益要求,政治则有可能被抽象化,并因此丧失政治的群众性基础。我以为,这一“动员”结构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一种激进的也是极端化的发展,这一发展的特征,正在于政治的高度抽象化,这一高度抽象化的政治,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疲惫,也导致了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蜕化,并进而形成群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这正是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去政治化”的根本性的历史原因之一。
这一非制度化的“动员”结构,当它成为制度的某种补充的时候,会和制度达成某种默契状态。可是,一旦它成为制度,尤其是僵化的制度的反对力量的时候,某种分裂包括激烈的对抗也就不可避免。问题则在于,由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批判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某种文化政治,而是一直企图诉诸于某种政治运动的形式,然而,由于这一“动员”结构缺乏转化为制度的可能,因此,持续性的政治运动,却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制度创新,即使“文化大革命”这一极端化的政治形式也是如此,所以,钱理群在自己的回忆中会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33}当然,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即有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也包含着内容与形式的断裂。而在根本上,正是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意识形态企图突破现代性的规约,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又仍然是现代的。这一制度设计不仅是国家的管理模式,甚至包括国家形态本身。在这样一个现代的格局中,制度创新实际上成为一个极其重要但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经由这一“动员”结构所表征出来也是未能解决的社会运动、文化政治和制度创新,将依然是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路径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动员”结构的存在,隐蔽地支持了当代文学中“动员—改造”的叙事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不是非常稳定的,相反,由于对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际的甚至是悖论性的解释,小说叙述又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这一模式的制约,甚至在文本中包括文本的形式上留下许多的“裂痕”,而这些“裂痕”的存在,则有可能促使我们放弃“成见”,重新也是更深刻地打开文本。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 杨奎松:《开卷有疑》第150~15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③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④ 罗丹:《风雨的黎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⑤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北京:《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
⑥ 这一现实原因即是当时存在的干部中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党员雇工剥削的现象,而围绕党员致富问题,当时党内高层也有过争论,参见罗汉平《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第21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而核心问题则在于,党员“雇工剥削”的资本究竟来自何处?这就涉及到“土改”的分配问题。周立波《暴风骤雨》中也已涉及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的时候,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常常具有优先选择的权力。
⑦ 这一“分配(粮食)”问题的颠覆性的改写,则是张一弓发表于80年代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一问题,我在另外的文章会继续讨论。
⑧ 这一模式同时也是政治模式,比如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明确指出:“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江山主编:《共和国档案》第19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⑨ 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1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⑩ 郑谦:《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1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1} 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200~20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 比如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对这一演变过程就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并且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我在此主要参考的观点和引述的材料均出于他的研究。详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 比如当时延安的一些著名文人就享受着较高的供给制待遇。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4} 比如,据杨奎松介绍,上海市在1956年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其中,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制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而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等等。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15}{16}{19} 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17}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第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8}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0}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1} 周杭生:《他把书法写上天安门红墙——与著名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对话》,上海:《档案春秋》2006年第5期。
{22} 比如,毛泽东在叙述“长征”经验时,就曾将红军比喻为“宣传队”。
{23}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5} 朱鸿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120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 陈登科:《同志·老师·战友——忆钱毅》,《红旗飘飘》(第一集)第1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27}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28} 有关知识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我的《主人意识、工匠精神和知识参与》一文。
{2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8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30}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102~103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
{31} 这也是所谓“教育革命”的基本内涵,即“五七指示”所强调的:学生要“以学为主”,“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北京:《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而1971年8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则明确提出了两个“估计”,一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另一个是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6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32} 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也就是“反右”之前,部分工人就曾在运动中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某一工厂的大事记就曾记载:“5月9日,部分职工受到社会上大鸣大放的影响,有的职工抢了尚未分配的空房,职工对生活福利意见较多,情绪激烈,由于领导思想准备不足,一度造成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混乱。5月,党委着重抓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党委领导团结一致,改进作风转被动为主动,从党内到党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办法,层层做通职工代表思想,及时、迅速地抓整改,解决一批意见比较集中的住房、小食堂、家属进厂、托儿所、浴室、交通车等问题,很快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上海二纺机党史大事记》第151页)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组织更是以集体的形式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就是所谓的“经济主义妖风”。
{33}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46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