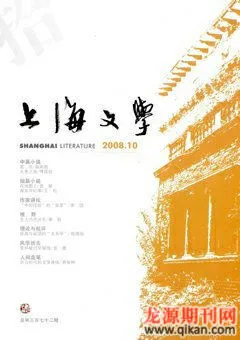没事你就看看河流
2008-12-29林雪儿
上海文学 2008年10期
一
河谷宽了,河流像四分五裂的家庭,各自劈出一条河道,湍急地向前涌动,到乌龙凼才汇合在一起,平缓地向远方流去。安子坐在河边,像扔在河滩的一块石头,没有颜色。背柴的、种地的乡亲挽了裤腿从山那边趟河过来,目光在他身上扫过,却没有一个人肯停下来对他说话。年轻的姑娘从离他较远的地方上岸,溜一眼他,想到“流氓”两个字,脚下加快,仿佛稍一停留会坏了圣洁的名声。
蒲草快要淹没他的时候,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坐到他身边。松散的身子紧张了,他的手插进沙里,好一阵才说:“我在等你。”
女人说:“我也在等你。”
眼前有两只蜻蜓点水,上上下下闹着,交结在一起,停留在蒲草尖上。安子的呼吸忽然粗重起来,血全涌到身体的某一个地方,他扑过去,肆无忌惮地喊:“秋秋……秋秋……”
安子问队长什么时候分给自己责任田,队长并不急于回答,而是拿出烟让他抽,问他“下山”后有什么打算。安子说没打算。队长忽然变得很慈悲,称赞他长得有模有样,年纪不算太大,劝他好好找一个,最好倒插门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安子把烟丢在地下,使劲用脚揉搓,说:“我哪儿都不去。分给我田。”
队长说:“你要留下来可以,别再沾染秋秋。她是别人的女人。”
安子只反复一句话:“分给我田。”
队长说:“等下一次分田的时候再说。刚结婚的、才出生的还不是和你一样,没田。”
安子说:“我是上过山的。‘山上’能把羊养成狼。”
队长张了张口,想发作,却又压了火气,平静地说:“别老是把‘山上’‘山上’的挂在嘴边,那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再说乡里乡亲的,能帮衬就帮衬。你到河滩开一片地先种上吧。”
安子在靠近乌龙凼的河滩没完没了折腾那些沙石地。他记得小时候,河的中间有一片突出的沙地,那时是种了庄稼的。他耐心地挖,捡出的石头放进河里垒起一条路,枯水的季节,乡亲不脱鞋就能过河了,可有人偏偏要当了他的面脱鞋过河,为的是不走他垒的路。安子只有埋头挖地,像是还没想好种什么,开出一大片还空着。
队长建议栽红苕,安子却种上了棉花。这里的土已经十多年不种棉花了。
安子的棉地开出一片绚烂的花,好些乡亲像被梦魔了,不敢走近那一片棉地。队长女人说在黄昏时总看见死了的独眼王婆在棉地旁放鹅,于是那片棉地沾染了晦气,安子和他的母亲也沾染了晦气,没有人靠近他们。只有秋秋常常在黄昏潜入那片棉地,安子在那儿等她,他们做爱,和在十多年前的棉地里一样;他们不做爱,还是和十多年前一样,安子的头枕在秋秋的大腿上,静静地听河流的声音,看天上微亮的星光。
秋秋摸索他的脸,手指滑进他的嘴里。她言不由衷地说:“也许我应该放了你。”
安子坐起来,把她压在身下,说:“我不会放你。”
他们做爱的声音让棉花恣意开放,花朵极尽喧哗,1zFg/iWs/Yi5xkg80Bv+DggrrjDZi/AgATYv57WO1zI=却没有挂一个桃。家里本是猪吃的红苕都被人吃了,猪当给了别人,换回一点大米,眼看又要见底了。
队长从山上挖红苕回来,倒了一堆在安子的棉地里。安子没好气地说:“拿走。”
队长的扁担在沙砾上一跺:“你他妈的不孝!你妈盼着你回来有个依托,可你还干少年人的事。你和谁赌气?啊?”
安子先被队长的阵势吓着了,等他回过神来,明白已经包产到户,队长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时,队长已经挑着剩下的半筐红苕走了。
安子踢一下红苕,骂一句“日你先人”,捡一个踢伤的红苕在河水里洗了,大口大口地啃。他把棉秆拢在一起,点上一把火,浓烟罩了河谷,河流虚幻起来。他在浓烟里哭,只有河流知道。待烟雾散尽,河流、滩地、卵石又清晰地呈现出来。
他把燃尽的草灰撒在地里,提着一个小包离开了村子。
安子再回来时,母亲在他开出的地里种上蔬菜,他也不管。他天天用竹子编成一个个圆桶在河滩上挖了坑埋下去,再从山上挑来山土填平。母亲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队长也不知道,只有秋秋知道。秋秋帮他担土时,村里人都看着,嘲讽的,羡慕的,嗤之以鼻的,他们俩都像是没看见。队长要秋秋注意影响,秋秋说,拉他一把,帮他一把,让他重获新生,不是上面来的干部在会上说的吗?再说我们是劳动,劳动光荣。
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劳动的权力。等他们已经埋下几百个这样的坑时,已经是春天了。安子又出了趟门,弄回一捆捆橘苗,在挖好的坑里栽下去。他买来果树栽培的书,对照书上说的修枝、浇水、挖坑、窖粪。橘树长到一人高,却没有挂果。队长女人逢人便说:“老天爷眼睛睁着呢,想挂果?门都没有!就像女人不是自己的,再撒多少种子还不是白撒?”村里人就笑。
母亲又开始长吁短叹,劝安子和秋秋断了,说:“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安子安慰说:“妈,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安子从外乡接来一个人,那人三下两下就把长势还好的枝条剪了,然后用一根小枝条重新嫁接到橘树上。村里人站在路上看稀奇。“那是外乡的农技员,安子的狱友。”秋秋对疑惑的人群说。有老人语重心长对秋秋说:“你一定中邪了,怎么就和那样一个人黏在一起呢?”有男人猥亵地笑:“秋秋,跟我吧。我保证比安子会搞。”
秋秋脸色煞白:“流氓!”
男人哈哈一笑:“你不就是喜欢流氓吗?”
秋秋啐了一口,毅然走到安子身边,帮他把剪下的树枝挽成一个个可以烧的柴火,一边示威似地看着路上越聚越多的人,嘴里骂骂咧咧。安子听了,拿着刀往路上一站:“是男人就对老子说,别他妈的欺负女人!”
众人见他凶神恶煞的样子,纷纷噤口。秋秋的男人刚到,就有人起哄似地喊:“六指儿,六指儿……”被称为六指儿的男人看到秋秋又在帮安子做事,嘟哝了一句:“流氓还长脸了。”
安子说:“你闭嘴。”
六指儿环顾一下众人,见队长的女人正往这边走,壮着胆说:“嗨,吃屎的还能把拉屎的怎么样?”
安子说:“再说,老子折了你的六指。”
六指儿下意识地把六根指头的左手往身后藏。队长女人走来,双手往腰上一插——六指儿是她侄子,安子欺负六指儿不就是欺负她吗?她放开喉咙大骂,安子作势要砍人,嫁接果树的外乡人忙上来拖走了他,又把秋秋劝走了。
安子知道他又一次得罪了村里人。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外乡人,只有守着河边的果园,看新叶一片片长出来。许是诚心感动了河流,夏天涨水时,河流紧挨着山那边去了。水虽然漫上河滩,因为有竹筐保护,果树安然无恙。
当果子金灿灿挂满了枝头,荒芜的河谷仿佛突然间脱胎换骨。村里人却有了妒意,愤愤不平地说,河谷是大家的,果树也是大家的。
秋秋对安子说,六指儿同意和她离婚了。安子忽然有些手足无措。秋秋抓住他满是茧子的手放在胸脯上,说:“等卖了果子,我们就结婚。”安子猛然醒悟过来,张开双臂像一只鹰把秋秋罩在他的翅膀下面。秋秋说:“我们去乐山看看大佛吧,给大佛上支香,保佑我们。”
河谷第一次在夜间如此热闹。狗吠声此起彼伏,火光像游弋的鬼火,时亮时灭,结满了果实的橘树被汹涌而至的人潮围着,哗哗作响的枝叶绝望地呼救,回应它的只有邪恶与贪婪的喧嚷,压抑而焦躁的抢夺、争执。一个女人的呼喊凄怆地划破夜空:“乡亲呐……乡亲们呐……”
两天后,安子和秋秋回来,发现河谷空了,到处是断枝残叶,成熟的果子掉在沙地里,被无数双脚踩过,黄色的果肉翻出来,触目惊心像是在控诉。安子双眼血红,顾不得看秋秋一眼,飞奔回家。母亲躺在床上,队长坐在床边,看到安子进来,立刻不安地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母亲重重抽了口长气:“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把树挖走了……”东西砸在地上发出愤懑的巨响,霍霍的磨刀声中,母亲用尽全力喊了一声:“安子……”安子跑到母亲身边时,母亲的嘴唇全乌了,只缓缓吐出两个字:“忘掉……”就闭了眼。
队长召集一些人把安子母亲葬在她丈夫的坟旁,对安子说:“你母亲一直有心脏病……”
安子跳起来:“她是被你们杀死的!”
队长长叹一声,脸上笼着一层忧戚:“不要冲动,再进监狱,给你母亲烧纸的人都没有了。”
“我不会放过带头的人!”安子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气。
队长说:“你去看看哪家没有挖过树,你能杀了全村的人?”
安子把果园被毁的事告到了公社。公社派人调查之后,答复说,第一,果园不是属于个人的,因为河谷属于大家;第二,村里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行动,法不治众。果园的事不了了之,有人说,秋秋是故意引开安子的,而她男人早把这一切都计划好了。安子不相信,但秋秋却像隐身了一样,找不到她。
看不到秋秋的安子失了魂,日复一日沉默地守着河流。
队长每次路过河边,都会陪他坐坐,引他说话,可安子好像失语了一样。队长叹一声:“作孽啊——”佝偻着身子离开了安子。
秋秋再出现时,是个寒冷却有太阳的冬日。安子坐在河边,看见秋秋随着阳光跑来,后面跟着六指儿,再后面是队长女人及一些乡亲。队长女人高声嚷嚷着什么,安子听不清,只看着秋秋一直向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跑,到了乌龙凼,突然从河岸上跳了下去。
太阳碎了,一河的光影全碎了。在深不可测的乌龙凼,秋秋一下没了踪影。六指儿哭丧着脸喊:“秋秋——”安子猛地冲过去,却被队长女人拦住:“你还想怎样?”安子鲁莽地推开她,纵身跳下了河。旁人这才醒过神来,几个水性好的男人也纷纷跳下河救人。
没人找到秋秋。老榕树半边枯了的最后一截树枝掉进河里,激起一片水花。队长女人脸色发青,嘟囔着:“见鬼了,见鬼了。”
安子最终在老榕树下找到了秋秋,她被老榕树盘根错节的树根卡住了。安子像多年前独眼王婆指点的那样,把秋秋背在背上颠了几圈,可她始终没有醒过来。
六指儿嚎啕大哭,安子狠狠剜了他一眼。六指儿突然抓住队长女人,说:“你害死了秋秋!你还我秋秋!”
队长女人扇了六指儿一耳光,骂:“没出息!”
秋秋死了,死在安子天天守望的河流,吞噬了秋秋生命的河流变得有些狰狞,特别是乌龙凼,更是罩上了诡秘的色彩:这段河最深的地方,淹死过洗澡的孩子,好多人下河时觉得腿被什么东西拖住……越传越邪,很少有人敢靠近乌龙凼了。只有安子,挪到乌龙凼一天一天地坐着,像沉默的守陵人。
队长女人在秋秋死后的第一个七日,开始发高烧说胡话,烧退后仍然半疯半醒,老说秋秋找她索命。稍清醒时就买许多纸到乌龙凼的老榕树下去烧,过河回来,对河边出神的安子说,秋秋不是她害死的,让安子见了秋秋,叫她别怨自己。安子不理她。队长女人走出几步又退回来:“果树是秋秋男人串通大家去挖的,我只是通知了几个人……秋秋要毒死她bduFlg5wwKTX/l+F3EIxyXArs+B7G4AbEv2krg2DWw4=男人,买了老鼠药拌在饭里,可她是傻子,要吃饭的时候,又把她男人手里的碗打掉了。我侄儿命大,噎噎……”队长女人笑一阵,偷偷瞄一眼安子,蒙住自己的嘴,一会儿又说:“我侄儿说离了算了,说不得哪天就死在她手里了。我说要不得,不能便宜了她。把她关起来,她不是喜欢男人吗,给他找几个男人,看她安逸够……”
安子霍地站起来,咬牙切齿地逼近她的脸:“你会遭报应的。”
队长女人又一笑:“我知道你,你是流氓。嘻嘻……秋秋喜欢流氓。”忽然她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我就是不让秋秋和你在一起。你是野种……哈哈,野种……”安子不知她是装疯卖傻,还是真失了心智,看着她一摇一晃地离开乌龙凼,一会儿忽见她在路中间跪下,对着空无一人的河边不断叩头。安子跑过去想问个究竟,可队长女人听见脚步声,站起来就跑。路上有人看见安子追着队长的女人,传到后来,成了安子追打队长女人。
队长女人疯了。疯了的队长女人也守在河边,唠唠叨叨对死了的秋秋说话,对安子母亲说话,对独眼王婆说话,好像她突然穿越了时间回到了从前。安子在她眼里是虚无的,她看不见他。队长每天傍晚到河边牵女人回去,原本魁梧的身形日渐佝偻。
离春节还差几天,队长女人死在了门外的一条小水沟里。沟里的水最多及脚踝,怎能淹死人?村人疑虑纷纷。可有人说,要死,一碗水也能淹死人的。队长女人死了,安子突然觉得他的恨没了根,轻飘飘的。
队长女人送到山上去埋时,安子在送葬的队伍里看见了青云——队长在外省工作的儿子。青云穿一件黑色大衣,围一根格子围巾,在母亲的葬礼上,他仍然挺直了身板,在一帮村里人面前显出他的优越来。
“如果没有我,秋秋会不会嫁给青云?青云会不会带她离开?”安子的目光粘在青云身上,少年时的一些光景跳了出来。
二
大人们在山上的红苕地里割红苕藤,安子、秋秋还有队长儿子青云和一帮小家伙在割猪草。青云虽然大两岁,却与安子一般高,这让青云很不乐意,什么事都要和安子比个高低。和安子同班的秋秋却总是站在安子一边,看他们俩为抢猪草互相抓扯,明是过去拖,却悄悄在青云手上揪了一把,疼得青云叫了起来。
队长走过来,青云越发撒泼,抢先哭着说安子抢他的东西。
队长不以为然挥了挥手,往每个小家伙的背筐里装进一把苕藤。队长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你不管,我管!”不问青红皂白就扇了安子一耳光,骂道:“娼妇养的,敢欺负我家青云?!”
安子母亲跑过来,拉了安子让他走开。
安子甩开母亲,捏紧拳头,忿忿地盯住队长女人。
队长女人跳起来,高叫:“反了反了,小杂种,你还想打我不成?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跨出来……”乡野粗鄙的骂声从她口里源源不断地倾倒出来。
有人劝:“算了算了,人家男人跑了,可怜么……”实际却把火焰扇得更高。
队长见老婆没完没了,用足了男人的声音与队长的威严,吼了一声,老婆这才收敛,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心尖尖儿疼。”
青云看安子噙着泪耷拉着脑袋,心里得意。秋秋走到安子旁边,手里的一把草丢进了安子的背筐。
其实安子早该适应这样的叫骂了,队长女人和自己母亲之间的战争,母亲总是处于劣势。母亲身子太单薄,声音也太细;队长女人身坯却像男人,骂人时,整个生产队都能听见。队长女人为何总与母亲为敌,安子不是很明白,他只知道队长每次来他家,总会带些花生、玉米之类,哄他出去玩。似懂非懂的安子很快就被队长的好处收买,再说他对父亲没有印象,母亲说父亲死了,村里人却说父亲跑了。安子恨那个没见过面的父亲,但很多时候,他都会忘掉有父亲这个人。
安子心里有事,就会呆呆的,周围的一切全都不见,心只在他想的某处。秋秋扯他衣角,他才回到眼前,俩人一起回到伙伴们中间。青云领着大大小小十多个孩子,玩占云桩的游戏,安子和青云分到一组,又成了战友,孩子之间的结还没拧紧就解了。母亲远远看着安子和青云,一不留神,镰刀割破了手指,她把手放在嘴里吸着,尝到一股甜腥味。好在苕藤已割完,母亲用衣角绕了手指坐在田里,独自流泪。
地里忽然热闹起来。因为发现红苕被人刨了很多,一串带着黄泥的脚印从地里延伸开去。队长带着一帮人沿着脚印走,安子和小家伙们也在后面跟着。近来队里能吃的东西总是被偷,这次也许能抓到小偷。脚印一直伸向坟山,那儿荒草齐腰,总带着一丝恐怖。孩子们迟疑地停住了脚步,安子退回到母亲身边。
空坟里抓住了一个人。像平静的水面突然扔进了一块巨石,地里顿时喧哗起来。队长和他的手下个个脸上被神秘与兴奋罩着,押着小偷径往村里走。过河时,有人用水洗净了小偷抹在脸上的泥巴,他们认出了他——安子的父亲。
队长和民兵连长嘀咕了一阵,把人押去了安子家,绑在柱子上。
民兵连长卖力地拿鞭子抽他,让他交待这些年去了哪里,偷了公家多少东西。
他不说话,瘦脸,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却贼亮。安子觉得他活像连环画里的特务。母亲却哭着,把别人从空坟里端回的煮红苕泼在院坝里,喊他滚。
他还是不说话。乡人被激怒了,扯下他不辨颜色的棉衣,发现了更令人惊诧的事:他的手臂上居然刺着“36”。民兵连长高喊一声:“特务!”队长本来只在一边指挥,这时也抡起鞭子狠劲儿抽,让他交待是不是特务。
除了否认,他依然没有别的话。队长打累了,和民兵队长去了公社,时代已经教会他们保持警惕。大人们打完,轮到小孩子们拿鞭子抽打,谁打得欢,谁就赢得大人们的夸奖。安子躲在堂屋门后露出惊恐的表情,青云说:“安子,你不是想加入红小兵吗?你出来打。”安子慢慢移了出来,拿起地下的扫帚往称为父亲的人身上猛拍。母亲咆哮着拉开安子:“离坏人远点!”
队长女人走到安子母亲面前,说:“你要和他划清界线,今天的苕藤就不分给你了。”母亲张了张嘴,哀哀地进了灶房。
乡亲们走了,小孩也都散去,安子母亲只是捡起棉袄披在男人身上,他才抬起头望她一眼,说:“我对不起你……”然后看了看安子,又把头埋下了。
安子跨出家门,青云他们在马路上坐了一排,见他走出来,便一齐喊:“打倒特务!”安子低头本能地一直往前走,直到河边。独眼王婆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放鹅,鹅看见安子过来,撺着脑壳去嘬他。
王婆喊:“娃呀,过来。”
安子走到她面前,她的一只瞎眼在已近黄昏的河边,闪着死鱼一样的光。以往,安子总是避免与她对视,但今天,他在那只独眼里看到了慈爱。
王婆说:“娃呀,可别想不开,路还长着呢。”
安子不说话。
王婆又说:“娃呀,没事你就看看河吧。鹅儿把水搅浑了,一泡尿的工夫,水又清了。”
安子觉得王婆这话没意思,但还是在河边坐下来,眯着眼看眼前淌过的熟悉的河流。深秋,河床已露出很多,河水分成无数支流,沿着夏天冲刷的深沟哗啦啦地流过。水流的声音被安子无限放大,在这声音里,安子看见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光滑的、粗陋的、上了苔藓的……一个个都在黄昏里静默着。河水是清亮的,回旋的地方有小鱼在石缝中钻进钻出。乌龙凼岸边的榕树倒映在水里,水面上下连成一片。乡村的各种声响渐渐沉寂,只有水声浩荡。
“安子……安子……”母亲的声音在大路上响起,像喊魂。母子俩回家相对闷坐,谁也没提吃饭的事。
安子问:“‘36’呢?”
母亲怔忡片刻,才明白安子问的是谁,叹了口气说:“押到公社去了。”
“妈,他真是我爸?”
“……”
“他真是特务?”
“……”
安子否认也好,拒绝也好,“36”作为父亲就这么进入了他的生活。安子拒绝叫他父亲, “36”,他给了他这个含义模糊的数字。乡亲们也带着一丝新奇又一些轻蔑地叫他“36”。“36”从公社押回来后很少说话,总在做事,好像赎罪。
对“36”的调查没个结果,安子一家的生活却罩在特务的阴影下。“36”四十多了,长得瘦精精的,身体灵巧而有力,斗争的次数多了,也就当成家常饭,不需要民兵来抓,自己就去了会场。青云是学校红卫兵大队长,心血来潮时也要带了“36”去学校,让这个成年男人在一帮少年面前低头,义正词严的发言之后,是谩骂与口水。这种场面对少年们而言永远刺激。安子这时候总是低着头,胆怯地站在一边。他最怕青云让他上台揭发,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证明“36”是在搞特务活动。
“36”揪去各处批斗的时候,队长就去安子家,去一次就有一些稀罕东西留下。批斗越来越频繁,安子的头越垂越低了,他被同学孤立,被大人孤立,只有河流接纳他。
冬天,河流是清冷的,如独眼的王婆,总是显得孤单。安子坐在河边,像一块石头投在没完没了的荒滩。岸边枯黄的草,被越来越饿的牛反复啃过,只剩一层薄薄的草皮。河水越来越瘦,河床更多地裸露出来,但在河中央,水一直向前流着,用它细弱却又坚韧的声音,证明河流活着。安子也活着。
翻过年,岸边的草皮慢慢润了,雨也多了,河流在安子的注视下渐渐丰满。安子躺在河流的怀里,安稳中又有几分欣喜。青云和伙伴们开始下河了,他们捡块石头跟着鱼儿跑,待它们钻进石头下面,就用手里的石头去打有鱼的石头,鱼儿被震晕了,昏昏然进了青云们的网兜。秋秋也在那伙人里,捂了一个冬天的双腿白白的像从泥里刨出的藕,晃得安子不敢盯久了。秋秋晃着白腿到了安子眼前说,安子下河啊。安子怯懦地笑,只坐在河边看。青云捉的鱼总是最多,送给秋秋,秋秋就悄悄放几条在安子旁边。
安子不说谢,心里如石头被河水抚摸般浸润。可他是多么丑陋的一块石头啊,想到“36”,想到将来,他的心又关上了。他在河边刨了个小水凼,把鱼放进去,鱼儿慢慢活过来,惊慌失措地在小水凼里冲撞。安子觉得那些鱼儿像自己,也像秋秋,他放了它们,让它们回到河流。鱼儿在河里,他相信它们不会离开,那样他又有了朋友。
夏天,河流开始涨落不定。安子的心躁动如河流,只有秋秋像一缕风,能让他在某种烦闷中安定下来。秋秋更像是河流的影子,不分白天黑夜晃动在安子脑中。坐在河边的安子明明看见秋秋在河边割草,却不敢上去说一句话,只远远地望,看她在水里的影子。风吹过水面,那影子就歪歪斜斜到了安子面前,安子低低地喊:“秋秋……”有时被自己的声音吓着了,就在沙地上写秋秋的名字。独眼王婆不知道安子在地上写的什么,但她知道他的心思:“娃呀,想得多了,苦。该是你的,命里写着呐。”
安子不明白独眼王婆为什么总能猜到他心里的东西。独眼王婆,一年四季都在河边放鹅,眼瞎了一只,年龄也大,可心里明镜似的。
“娃呀,要涨水了……”坐在地上的独眼王婆忽然说。
安子不信。天很蓝,太阳也明亮。可一会儿,河水真从上游像浪潮般掀过来,河那边的秋秋刚到河中央,就被掀倒,背筐冲走了,人也在河里挣扎。安子跳下河,救回秋秋时,她的脸白得像纸。独眼王婆要安子反背秋秋,让她把水吐出来。折腾了一阵,秋秋才醒过来。独眼王婆说:“秋秋,娃救的你。”
秋秋看看安子,安子却扭过脸,不敢对视。
秋秋说:“水咋个说涨就涨了。”
独眼王婆指指天边,河流来的地方,黑得像夜。安子说:“那地方雨大……”
多次的涨涨落落,安子知道了河的禀性。有时明明是晴朗的天,突然间就电闪雷鸣,大风刮倒河边的树,乌沉沉的黑云从上游滚滚而来,随之而来的是像涨潮一样汹涌的洪水。上山劳动的乡亲下工时,只能望河兴叹,看河水淹没河滩上那一小方自留地,看自家的亲人在河对岸伸长了脖子远望。有水性好的胆大男人就游过河,“36”常是其中之一。安子不会为他担心,他总觉得“36”身上有他不知道的强大的东西,而这种强大对安子是一种压迫。安子只念母亲,母亲的弱小,让他想到秋秋。母亲这种时候会沿河走,一直到上游有桥的地方,几分钟可回家的路,因为洪水要走两个多小时。母亲在河那边走,安子就在河这边走,到有桥的地方会合了,安子甚至不会叫声妈,又转身往回走。
安子喜欢看涨水。可有一年洪水大得超过了安子的想像,尽管他也十八岁了,身子还高过“36”,却一点也不像“36”。他长得魁梧,性格却懦弱得多。洪水满了河床,漫了公路,翻滚着冲来上游人家的草房,冲来喊救命的人。河流在安子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极有破坏力的男人,令人敬畏。
独眼王婆在一次洪水来时,连同她的几只鹅一起被冲走,鹅到了下游成了别人的,王婆的尸体因为发臭被当地人多次交涉,队长才派了人去弄回。当然这个人只能是“36”——没有人愿意做的事,自然该是坏分子去做。安子和“36”一起草草掩埋了独眼王婆。“36”回家了,安子还在坟前坐了一阵,没有眼泪,他蓦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秋秋也长大了,原先男孩子一样的性格,突然间变得羞涩了。齐肩的辫子像两把小刷子,衬着一张瓜子脸,小眼小鼻的样子,不算出众,但是拿青云的话说别有一番妩媚。青云读高中,能说出很多安子没有听过的话。春末的秋秋穿一件粉色衬衣,安子觉得像熟了的桃子,想吃,可他只是在看到秋秋的时候,把头低到了地面。秋秋端了衣服在河边洗,总洗不完似的,偶尔衣服顺水漂下来,安子捡到送过去,秋秋就问:“你天天坐在河边看啥?”
安子说:“独眼王婆说,河流不会欺人。”
秋秋不满地说:“我问你看见了啥?”
安子看秋秋一脸不乐,心中一急说话就结巴:“河……流……”
秋秋噗地一声笑了,反安慰说:“算了,我也看见了河……流……”
安子眼光蒙蒙像有水雾,秋秋紧巴巴盯着他的眼,像是看不够。安子初中时成绩优异,虽然因成分问题不能读高中,但在秋秋眼里,他始终是个好学生。安子在秋秋注视下不敢抬头,他就对着河流说话,他眼中的河流心中的河流在那一刻像水一样漫起。秋秋第一次听安子用语言说起眼前的河流,他的声音就像水流,让她着迷。
回过神来的秋秋说:“……看你衣服好脏,脱下来帮你洗了。”
安子扯着自己皱巴巴看不出颜色的衣服,难为情地说:“我自己洗。”
秋秋不理他,端着衣服走了。
安子脱下衣服,用母亲舍不得用的肥皂把衣服洗出颜色来。第二天,安子穿了洗净的衣服去河边,望穿双眼终于盼来秋秋,秋秋却沉着脸。秋秋父母是本分人,凡事都由着她,可今天父母却没有和她商量,就让媒人带了个小伙子来看房子。秋秋是独生女,父母自然不愿女儿远嫁,能招个上门女婿是不错的选择,可秋秋对那小伙子左看右看不顺眼,为这事和父母拧着。
安子瞄一眼秋秋,秋秋锁住双眉,也正看他。安子不知所措,只得把眼光丢给河流,又想起什么似的脱下那件洗干净的衣服丢在地上,露出背心衬着的发达的肌肉。秋秋红了脸,心怦怦直跳,低头看着安子的脚。
托媒婆找了几个人,秋秋都不满意,母亲天天数落她,秋秋好似没听见一般,只是认认真真做鞋。黑色灯芯绒的鞋面,上底的时候,周边压了白色的棉线。母亲问她为谁做的,秋秋说,谁穿合适给谁。队长女人介绍了她侄儿,说是兄弟多了,愿意上门。那个侄儿身体还算结实,只是一只手有六根指头。秋秋死活不同意,说她心里有人了。
青云在城里读高中,心自比别人高了一点,加上父亲到处托人给他在城里找工作,他理所当然认定自己不属于乡村。他喜欢东一句西一句说些高深莫测的话,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藉此吸引秋秋的目光。做农活的时候,他总有各种理由呆在秋秋身边,为了不至让别人说闲话,他会拉上安子。安子是安静可靠的,不会把他说的话传给别人,更主要的是他没人可传。可有一天他发现,安子梦一样的眼睛总是落在秋秋身上,秋秋看安子的神情也像书里读到的某些片段。青云突然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愤怒。
夜色中的河边,青云质问安子:“你是不是喜欢秋秋?”
安子不敢接他的话,好在有夜色掩护,看不见青云咄咄逼人的目光。青云踢了他一脚说:“你识相点,秋秋是我的。”
青云走后,安子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很久。除了流水的声音,他的头脑一片空白。河流没有带走他的忧愁只是增加了他的悲伤,突然间他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细小的水流只能沿着已有的河床前行,不像大水有重新冲出一条水道的能力。他有什么力量和青云抗衡呢?秋秋也是一股细水,如果另辟蹊径,只会消失了自己,或变成一潭死水。
安子的孱弱,让“36”从心底看不起。“36”还在挨批斗,可时间长了,人们只是为了一种游戏,让无波无浪的乡村生活多一点兴奋。大胆的女人喜欢和他开开玩笑,他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总让那些不甘寂寞的女人联想到发情的公牛。“36”在外还收敛着,可到了家,除了折腾那些石头柴火,就是折腾母亲。母亲的呻吟像锥子,一下一下刺激着安子的神经。
一个烦躁的夏日午后,母亲哀求的声音让安子血直往脑门上冲,他冲到灶房拿了菜刀,站在母亲那扇已经腐朽的木门前。“36”突然打开门,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盯住安子。安子在他的逼视下侧过头,张了张口,怒吼变成了嗫嚅。“36”鼻子里哼一声,骂一句:“龟儿子。”安子鼻子发酸,一口气跑到河边,扎进水里。
他从水里冒出头来,正见秋秋扛了一把锄头从老榕树那边过来。他突然想哭,泪流进河里。秋秋过河时,他站起来呆呆地看她,秋秋看了一眼他几乎全裸的身体,赶紧低下头说:“穿上衣服,我有东西给你。”
安子忐忑不安地跟在她后边,刻意拉开一段距离。他不敢进屋,站在竹林的阴影里等。秋秋拿了一个装过磷肥的纸袋给他,说:“回家再看。”安子转身就要走,秋秋说:“他们走亲戚了。”
安子低声说:“知道了。”
秋秋又说:“他们走亲戚了,明天才回。”
安子不解地说:“知道了。”手指使劲捏捏怀里的东西,想快点知道答案,就说:“我走了。”
秋秋骂了一句:“死脑壳。”
安子钻进自己的屋子,拉上窗帘,打开纸袋,一双漂亮的鞋,往脚上一套,正好合适。他高叫了一声妈。母亲进了他屋子,拿起鞋子凑到窗前,把窗帘拉开打量。“36”正站在窗子外,开了一句玩笑:“小子有女人了。”母亲脸色大变,拉上窗帘对安子说:“没到时候,有些事可不能做啊。”
家里安静了,安子的心却狂躁地想要破坏什么。晚上更觉燥热,身体里像有火,发不出来。电闪雷鸣,雨却不下来。安子赤裸地躺在黑暗中,听到一壁之隔传来“36”粗重的喘息,逐渐加快加深,如惊雷敲醒他身上沉睡的野性。闪电割裂天空,也撕破了他埋藏本能的伪装,原始的力的冲撞,让他在床上辗转难眠。
风嘶叫着,盼雨到来。安子潜到秋秋窗下,固执地敲她的窗子。秋秋把他让进屋的刹那,血涌上了他的脸。黑暗中,雷声与闪电像天际的奏乐,令他亢奋。他发狠地揉她捏她揪她,秋秋喊痛的声音被倾盆而下的雨声淹没了。
天空变高了,河流也变野了。那个雨夜过后,秋秋的心也野了,总是寻找机会与安子缠绵。秋秋说出她要嫁给安子,生产队就如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秋秋居然要嫁给安子!反应最强烈的是青云,暴怒的结果是找人把安子打了一顿,可安子表现出的淡漠让青云心里不是滋味,他对母亲说:“秋秋不能嫁给安子。”队长女人正为秋秋拒绝她的侄儿窝心,想了想说,她有办法。
外边开始风传秋秋订婚了,对象是队长儿子青云。青云其时正借到公社当广播员,听到这传言,又是疑惑又是欣喜,去问母亲,母亲却只是莫测高深地笑笑。至少安子没戏了,这让青云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他要安子知道他的厉害,自己娶不娶秋秋倒在其次。一个特务的儿子,怎么能和他青云决高下呢?
傍晚,青云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神气活现地在河边堵住了安子的路:“秋秋要嫁给我了。”
安子闷了半晌,冒出一句“我睡过了”,扭头就走。
青云追上去狠狠踢了他一脚,骂:“流氓!”
青云将这话告诉秋秋,以为她也会像自己一样愤怒,没想到秋秋只是低头一笑,像是默认。屋漏偏逢连夜雨,广播员的差事又被公社妇女主任的儿子顶替,青云一下子病倒了,队长女人天天在安子家门口指桑骂槐,一边又忙着给儿子找对象。青云却统统不见,他已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好躲起来复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青云在河边找到安子:“我不要了,秋秋送给你。”
青云退婚的传闻让秋秋父母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便把一切怒火都归到安子身上。秋秋父亲说,决不允许一个特务的儿子进入自己的家庭。他们把秋秋关在一间小屋里,队长女人还是把六根指头的侄子介绍给了秋秋,不到一个月,秋秋家就开始张罗婚事。
秋秋绑在家里与六指儿成婚那天,安子在河边坐了一夜,迷漫在河上的雾像看不见的将来,他没有明确的敌人,可敌人却又强大得让他无所适从,无所躲藏。河流还像昨天一样若无其事地流着,安子的心却丢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再也回不来。
婚后的秋秋再次见到安子的时候,他正在棉花地里摘棉桃。饱满的棉桃像成熟的女人,打开的声音让男人们浮想联翩。他碰到秋秋摘花的手,所有的棉桃仿佛刹那间绽开,满世界都是晃动的棉花。“今晚,乌龙凼。”安子猛然看着秋秋,她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安子重新活了,他在河边躺下,伸展开手脚,摊成一个大大的“人”字,睡意蒙蒙中也见他笑。他的世界是秋秋构成的。有了秋秋,所有的轻视如同风过水面,水不会因此而改变方向。
因为秋秋,安子的生命力恣意张扬,让好事者猜测不断。猎人布了陷阱,当安子和秋秋在棉地里缠绕时,被队长女人带着一帮人抓了正着。安子反剪了双手跪在地里,他没有低头,用眼光寻找着秋秋。看队长女人打秋秋的耳光,他骂了句粗话,队长女人打得越发狠了。安子低声下气地求他们:“你们放了秋秋,放了秋秋……”
队长女人打一下骂一句:“流氓……淫 妇……一窝淫妇……”骂着骂着就扯到安子母亲的头上。
安子说:“不准骂我妈。”
队长女人狞笑:“做得还怕别人骂不得?”
安子猛地唾了队长女人一口痰。队长女人手一抹,对其他人说:“灌他的尿。”
村人将惩办流氓当作一种乐趣,个个群情激愤。
秋秋哀求道:“让我们死吧……”
队长附在她耳边说:“说是他勾引你,他出身不好。”
秋秋固执地说:“是我愿意的。”
队长女人往地下“呸”地唾了一口:“不要脸!不看你是我侄儿媳妇,就让你挂只破鞋游街去。”
安子终究咽不下这口气,用药毒死了队长家的牛。牛是集体的,不过是队长家暂时照看。队长女人愤然告到公社,安子以流氓加蓄意破坏集体财产罪判了刑。
安子服刑之后,母亲垮了,心慌,失眠,一天不如一天。队里对“36”的斗争少了,“36”却越来越沉默,每天喝大量的劣质烧酒,终于因为酗酒而倒在河边,河流接纳了他。
秋秋父母因为女儿的丑事,愁病交加,不到一年就相继过世。秋秋与六个指头的丈夫在一个屋檐下过起了日子。她从心眼儿里看不起他,和其他人一样叫他六指儿。六指儿在秋秋面前,总是带点怯懦而讨好的神情,他知道秋秋心里只有安子,尽管不甘,但自己裤腰里那物件总不争气,自知在秋秋面前扛不起一个男人的称呼,日子久了,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秋秋在安子走后接替了他的使命,时常守着河流不言不语。河滩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秋秋就捶石头卖,碎了的石子拉到远处修路,她为自己凑足了去安子服刑地方的路费。在那个荒远的监狱,安子见到秋秋,以为是梦。他说:“好久没见过河流了。”
秋秋说:“河流还那样。”
会面始终在狱警的监视之下,她只能揪住他的手,指甲掐进他的肉里,相顾无言。疼痛夹杂着甜蜜的感觉,一直陪伴着安子度过了十年的日日夜夜。
三
安子看看自己的手,仿佛还有微微的疼痛。安子对着乌龙凼喊一声:“秋秋——”乌龙凼镜面一样平滑的水突然起了一圈涟漪。秋秋活着,世界的某个地方就有温暖,日子就有盼头;可她死了,安子还得活着。他不知道除了守着乌龙凼,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更接近秋秋。
青云迎面走来,安子抬头向这个一起长大的伙伴表示友好。青云冷冷地站定,目光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像打量一头牲口。安子说:“你回来了……”
青云点燃一支烟,烟雾把他的脸罩住了。昨晚他一直守在母亲的长明灯前,父亲坐在黑暗的角落,抽着烟,平静地述说着。青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疑惑,惊异,怨愤,连带小时候的种种,都在夜的深处显现出来。晨光微曦,青云仿佛突然发现,父亲的腰已经那么弯了……
抽完一支烟,青云像是下定了决心,在安子身边坐下。两个人默默地看着河流,好一阵,青云才说:“他们都走了……”
安子怅然:“如果秋秋跟了你,可能就不会死了。”
青云说:“没有可能。除非是小说,她可以再活一种人生。”说着他站起来,把沾在围巾上的一根野草丢进河里:“我明天就走了,爸一个人在家,让他去我那儿,他不去。人老了,不放心,你替我照顾他吧。”
安子不解地张张嘴,青云却不容分说,拍拍大衣上的尘土,走了。
队长其实并不要安子照顾,倒是常劝安子别一天到晚在河边呆坐,正常人也会坐出毛病来。安子只是淡淡的,越来越懒散,冷眼看村里人各行其道。他只侍弄一亩地,勉强过日子,剩下的时间都给了河流。秋秋走后,河流不知为什么更瘦弱了,到了冬天,河水细细的几近断流。村人在乌龙凼之前截断水源,抽干了乌龙凼的水,从没见过天的河床裸露出来,河床的岩石高低错落,老榕树根伸入岩石的缝隙间。吞噬了多条生命、村里人谈之色变的乌龙凼不过如此,人们的恐惧没了,再没有人敬畏河流。
村里人找到了一条致富的捷径:淘河里的沙石卖。一时间河滩上又热闹起来,家家老少都出动了,曾经顺畅的河床千疮百孔,乡亲们却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河流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安子不动,袖手看别人淘。安子说他听到了河流的哭声,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队长也只能袖手旁观——他喝酒喝出了脑溢血,只能坐在椅子上,说话也含糊了。安子默默担起了照顾队长的事,青云临行时的话,如今一语成谶。
河流又开始吞噬生命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有了敬畏之心。只是河流的声音每天被汽车的声音湮没了。一条新修的公路要穿过村子,掘起的泥土源源不断地往宽阔的河谷里倾倒。泥土填补了河谷的深坑,慢慢地在河谷重新堆造了一道宽阔的坝子,河流被挤到了山脚。发大水的时候,冲垮了一些泥土,河道淤积不再像河流的样子。奇的是水更细了,安子想不通水去了哪儿,常常担心河流会断。坝子上的荒草倒是浩浩荡荡,人们经过时,偶尔会被蹿出的蛇咬伤,还有人为此锯了半条腿。
安子在秋天放火烧掉了荒草,春天来时,他把队长背到河边,说:“没事你就看看河流吧。”安子开始在坝子上挖坑,没有秩序,疏密不匀。队长的表情中有一丝欣悦,好像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玩玩具。安子买回桉树苗子,一根一根地栽下去。当坝子上的桉树都长到碗口粗时,河谷又一次美丽起来,绿色屏障似的树林隔开了河流,关于鬼魂的阴影退到远处。
安子把队长推到河边,点燃一支劣质烟,在树林边坐下来看河流。或许因为有了树林,河水清了一些,潺潺地流过,仿佛是秋秋的低语,安子的心又充满了温情。他总在看着河流时想到秋秋,那一刻对于物质的要求变得很低,守着河流成为他远离喧嚣的最好借口。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的队长只能陪着他看河流。队长的心里也有一些缤纷的往事吧,安子在队长的眼角看到浑浊的泪水。安子推着队长往回走,为了方便照顾,他已把队长安排到自己家里。他想不通队长为什么不去青云那儿,青云回来接他走,他急得直摇手,青云只好按月给他寄钱回来。和队长呆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安子倒慢慢生出一些依恋来——队长解了他的寂寞。
安子的树疯长,风吹时树林哗哗的声音盖过了村子里的一切声响。鸟儿也多了,偶有白鹭来停歇。从乡村出去的年轻人回家来,也总喜欢到树林里走走。可是有一天,新队长告诉安子,为了给村民创收,要砍了树,修建一个大型造纸厂。安子不同意,说会污染河流。村里人却欣喜村子里要建厂了,他们好心地对安子说,这些树可以卖到纸厂。安子和队长每天守在河边看着树林,推土机开进树林的那一天,队长忽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死死地抱着一棵树,闭了眼。
安子给青云打电话,说:“你父亲死了。”
青云在那头说:“也是你父亲。”
安子愕然。
安子老了,头发白了许多。他还坐在河边,生长树林的河坝,现在正大兴土建。再没有人从河那边过来,但安子看到了更多的人:独眼的王婆,“36”,母亲,队长以及队长女人,还有永远年轻的秋秋,他们在那边活着,只隔了一条不宽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