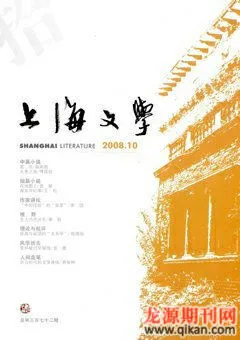花环被过早摧残——想起闻捷,总是欲哭无泪
2008-12-29袁鹰
上海文学 2008年10期
……
故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 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 路远不可测
……
水深波浪阔 无使蛟龙得
杜甫《梦李白》节选
一
这些年去上海,如果有机会路过南京西路,最怕走成都路口往西那一段,到那幢坐南朝北的公寓门口,必定快步离开,似乎闻到浓浓的煤气味扑面而来,明知这是幻觉,煤气是无色无味的,若是吞噬了活生生的生命也若无其事,一切都无异样。那年闻捷不就是在这幢楼上静悄悄地,其实是愤愤地离开人世的吗?!这么多年来,我总不愿去想他的悲剧,一想起他,就禁不住满腔悲愤,欲哭无泪。却又不能不想,倏然间,生命之火被无情浇灭,绚丽的花环被凶恶摧残,竟已过去三十七年的岁月了。
1971年春节前,我请了几天假去上海看望“文革”动乱中寄居外婆家治病的女儿,那时热闹的马路上满街大字报,据说正开展全市性的大批判高潮。有一天路过圆明园路《文汇报》馆,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上楼试探着能不能找到熟人,竟然意外地遇到老友徐开垒,动乱中相逢,十分高兴。我问起巴金、柯灵一些前辈和文学界许多同行朋友的近况,听说他们在前几年的疯狂动乱中都受到迫害和摧残,非常惦念现在境遇如何,不知能不能见到一两位。开垒兄说大多数都在奉贤“五七干校”,想见也见不着。我又问:“闻捷也在干校吗?”他忽然停住口,警觉地朝办公室门口瞥一眼,凑过身子低声说:“闻捷去世了。”我不觉一怔:“什么时候?”开垒说:“就在前几天。”接着几乎是耳语地说了两个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一个性格开朗、遇事乐观的人,会走这条绝路?开垒说不出更多详情,只能默然相对。告别他下楼慢慢走回住处,我仍是不相信这是事实。几个月前,我还偶然听说他被吸收进“样板戏”《海港》剧组去修改唱词,正庆幸他也许有机会摆脱厄运,处境会转好些,若不是到万般无奈,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决不会出此下策的。几年前,恶风初起之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夫人——一位忠贞贤淑的好党员、好干部、好妻子、好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诬陷凌辱,愤然离开人间,难道闻捷竟追随地下?怎么可能呢?两天后,老友赵自到我住处相晤,我问起闻捷的事,总算略知原委,也只能相对唏嘘。十年后读到戴厚英女士的《诗人之死》,才知道前后详情,稍微解除京中许多闻捷的友人心中疑团,却怎么也抚平不了心头的伤痛。不料几年后,《诗人之死》作者竟遭暴徒凶杀,同样使人感到惊愕,又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惨剧!
建国初期,就听说诗人闻捷的名字,知道他虽然远在西北,却是我们江苏的同乡。虽在北京文学界会上见过几次,却并不熟悉。他的名作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倒是早就读过了。1961年我去新疆路过兰州,他已经离开西北到上海定居,失之交臂,没有见到,不免憾然。
直到1963年初秋,由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我随他访问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两个月朝夕相处,才感受到闻捷不仅是位热情豪爽、开朗豁达、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深深地感染到他那宽阔的胸膛里,蕴积着那么多那么深沉的爱。旅途尽乘飞机,长途短途,频繁转换,而那一阵国际航线上经常传来飞机失事的消息。每次到达目的地走下舷梯时,我们总要互相轻松地说一句:“又把生命从驾驶员手里领回来一次。”8月下旬,由阿尔及尔去日内瓦,从机窗俯瞰,下面是碧波浩瀚的地中海。我说:“这回要是出事,可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闻捷微笑一下,神色转为严肃地回答:“不会‘皆不见’的。我的魂魄,是一定要飞回国,飞到北京,飞到上海去的。”在万里以外的异乡,他常常想念祖国,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同志,想念在上海的挚爱的夫人和三个女儿;回国以后,他又常常想念阿尔及利亚的牧民和孤儿,巴基斯坦山区的农民,孟加拉湾的船工和乞丐,也想念着出访期间结识的异国友人。他到处都无保留地显露出那颗真诚坦荡的拳拳赤子之心。
二
阿尔及利亚的8月,虽不像西非那般燠热,也还是热得可以,从早到晚,常常是汗流浃背。但是,闻捷仍然再三提议走出阿尔及尔到外地去,到山区去,去看望刚刚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普通人,去听听挣脱殖民主义锁链的奴隶的心声。在奥雷斯山区,在巴特纳和君士坦丁,我们遇到不少民族解放军的军官和战士——阿尔及利亚人称其为“圣战者”,在这种时刻,他总是问得特别周详,记得特别仔细。奥雷斯山头怎样一次次燃烧起武装反抗殖民军队的火炬,一次次伏击战怎样地进行,一些山河村落和一些勇士的名字,他都反复核对清楚,一丝不苟地记在笔记本上,也许是战争年代记者生涯中养成的好习惯吧。我也分明听到他那颗火热的心在剧烈跳动,仿佛回到十多年前某一次战役胜利休整时去采访一个英雄连队的日子。有一次告别时,他严肃地对主人说:
“亲爱的兄弟,我曾经穿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我完全能理解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士心情。这地球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没有消灭,我们还要一起战斗!”
那位民族解放军军官听了,突然双脚立正,举手行了一个军礼。好像站在他面前说这一番话的,并不是一位来访的中国诗人,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使者。
另一次,在奥兰西部,我们来到边境一个小县。阿尔及利亚朋友陪同我们参观边境一个哨卡。从哨卡附近一个洋溢着欢笑的牧民帐篷中出来几位老者,快步走到我们面前,邀请我们去参加正在进行的婚礼。陪同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朋友还在犹豫时,我看到闻捷的眼睛里已经流动着喜悦的神采。进入帐篷,他热情地向主人致贺,席地坐下。在那些还有点拘谨的牧民中间,谈笑风生,好像又坐在陕北高原上牧羊老汉或是天山脚下哈萨克男女青年们当中了。主人端来一盆“库斯库斯”——用羊肉拌杂粮的民族食物,油腻先不说,单是停留在上面的许多苍蝇,连我们的司机赛义德都忍不住要皱眉头。但是,主人刚说声“请”,闻捷就第一个举起羹匙。那几位老者眯起眼睛微笑着望着我们,等待客人们的反应,没等他们开口,闻捷就大声赞美起好味道来。如果有时间,我想,他也许会为主人朗诵几节他的《天山牧歌》的。
在阿尔及尔郊区伊特拉山上,我们访问了一所烈士子女学校,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战斗中牺牲了。走进校门,我们的心就不平静。在校长介绍学校概况和孩子们遭遇的时候,在参观学生学习成绩和宿舍的时候,特别是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闻捷的眼睛里总是噙着泪水。访问中,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将几个年龄最小的孤儿紧紧地搂在怀里。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很可能又一次想到远在上海的三个女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不行了。昨天晚上简直睡不着,两片‘眠尔通’没有一点用。”
9月,我们回到亚洲,在酷暑中踏上巴基斯坦干燥的土地。卡拉奇和达卡(那时候,孟加拉还没有独立,称为“东巴”)的街头,人声嘈杂,车马喧哗。由于访问日程的关系,我们未能同街上那些面孔黧黑、身体瘦弱的贫民进行攀谈,问一问他们的光景;也不可能直接去采访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和种黄麻的农民辛酸的生活。我们只是走马看花参观名胜古迹、大学校园和民间艺术展览,几天后便匆匆回国。路过仰光,住在大使馆等候民航班机时,开始合写一册短诗集。当我们商定将这册小诗取名为《花环》的时候,闻捷感慨万分地说:“花环花环,这算真正的花环吗?要按我们的心意,真想写写工人和渔民。我总忘不了达卡乞丐的那双手。”在达卡,有一次汽车遇到红灯,停在街心,突然从车窗外伸进一双手。车旁站着一个老年乞丐,满头干草似的乱发,同花白胡子几乎连在一起,瘦弱憔悴,显然好几天都处在极度饥饿中。一阵强烈的同情和怜悯涌上我们心头。我望望闻捷,用眼睛询问,怎么办?他紧锁双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老乞丐和他那双不住颤抖着的枯树枝似的手。在这种场合我们自然不便给他钱,而且我们袋里也没有当地的货币。很快,绿灯亮了,汽车继续奔驶。一直到回旅馆,他没有再说一句话。
如果要为所谓“诗人气质”作点注脚,人们可以找出一堆形容词,从最崇高纯洁的直到最乖僻怪异的。但我以为,对闻捷来说,最突出的就是那颗真诚的赤子之心,那颗中国革命诗人的心,而它是同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紧紧连在一起的,回想上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作家、诗人都有这样的胸怀。闻捷说过:“我们将来再一起到日本去,到拉丁美洲去,还有黑非洲许多国家,我都想去!”可惜,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以后一些年,我倒是去过日本、菲律宾、缅甸,也去过美国和苏联,却再也听不到闻捷的朗朗笑声了。
三
1988年,我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巴基斯坦,再一次踏上闻捷和我钟情的土地。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夜晚,会晤巴基斯坦文学界同行。老作家贾米鲁丁·阿里先生娓娓叙谈二十五年前相见的往事,并且说那时我们两人都还年轻,如今却已见老了。他又说到巴基斯坦作家们这些年比过去更加了解中国。记得上次闻捷曾向几位急切希望知道中国的巴基斯坦朋友介绍中国汉字的特点和结构,费了很大劲,也不知他们听懂了没有。此番我们这个代表团没有再遇到这类询问。多年来,中巴两国睦邻友好,交往频繁,如同酿酒,随着时光流转,一天天浓化友谊和了解。而闻捷和我两人作为最早接受巴基斯坦朋友们花环的中国作家,自然更感到幸运和自豪。这回在几次聚会上,我朗读我们二十五年前的诗,朋友们的掌声,使我欣然,也使我恻然。因为有的诗是闻捷的作品,掌声是给他的。空暇时候、会后,我和代表团的同伴自然地要谈起闻捷。来自天山下的诗人博格达·阿卜都拉必定要赞美《复仇的火焰》和《吐鲁番情歌》,他说闻捷那么深情地眷恋新疆,使他这个天山之子都十分感动。来自云南的作家张昆华说不久前还遇到闻捷的小女儿赵咏梅,同咏梅多次谈到她的父亲。二十五年以后,我感到闻捷依然同我们一起漫步在巴基斯坦的山山水水间。
在卡拉奇,二十五年前一路陪伴我们的小说家肖格特先生,他高兴地回忆起当年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也一再问起闻捷,问起他本人以后来中国访问时遇到过的巴金、老舍、杨朔、韩北屏……我不得不告诉他闻捷的噩耗,他沉默地对我凝视好久。我明白,那些好心的朋友们知道接触过而且尊敬的中国作家们都遭遇到不幸命运时都很纳闷,他们直率地问:为什么这些很好的人,不是遭到打击、投入监狱,就是非正常死亡?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中国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只能坦白地回答:我们那些年确实做了许多错事。可是,几句话能说清楚吗?他们很不理解,我们自己当时又何尝理解!
巴基斯坦朋友们盛情地赠送了一个又一个花环,代表团的同伴们都很喜爱那些用金线精巧编成的工艺品,我却一次次痛苦地想起闻捷这个最早被无情摧残的花环!1971年初上海那个严寒之夜,闻捷躺在自己扭开的煤气管边,让它冷酷地吞噬才华横溢的大脑和热情如火的心脏。闻捷,我不相信那个夜里你会像人们后来向我描述那样的平静安详,那不是你的性格。你是个铁铮铮的汉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你曾在沙场战火中出生入死,你曾在天山风雪里跋涉奔波,你曾为祖国母亲的今天和明天纵情讴歌,如若不是人的尊严、生的自由、爱的权利都被那伙奸贼们残暴地剥夺殆尽,蹀躞在漫长的隧道中看不到一丝亮光,听不到一点人声,你会像你的夫人那样,毅然决然地举步跨过那最后的一道门槛吗?!
想起闻捷的时候,我常常哀伤地吟诵杜甫《梦李白》的诗,一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写出了后代多少人的心情:“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凶恶残暴的蛟龙恶煞,那十年中残酷地毁灭了多少人的生命啊!闻捷,我的好友、我的兄长,你在哪里呢?你满怀豪情讴歌过的祖国,你为之流血流汗、献出满腔忠诚的党和人民,在经历了最严峻的血火炼狱,赢得了最辉煌的胜利之后,迈开了步伐,正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和光彩,走上民族复兴之路。1978年你的诗选重新出版时,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季写过一篇《清凉山的怀念》,以这样的句子结束:“……多少回,多少个同志曾经同我一起,深深地怀念他;假若闻捷还在,假若七年前他不曾在‘四人帮’的迫害下过早地离开我们,他将……”我深有同感。他特地用了“过早”二字,是的,你离开我们那年,才四十八岁的盛年啊!假若你还健在,假若你来北京,去广州、海南,假若你漫步上海浦东和一片又一片新区,漫步在今天的南京路、淮海路和崇明岛、长兴岛感受一下四十年前根本无法想像的巨变,假若你沿河西走廊再出阳关,走遍天山南北,或者去松辽原野、闽赣山区,假若你回到你长江之滨已经改天换地的家乡,再一次参加丹徒县党代会,多少新的业绩、新的风光、新的英雄儿女会融进你泉涌的诗情,而你那清新激越的诗句,又会飞到多少读者的心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