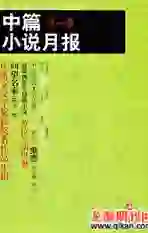二爷
2008-09-03石舒清
获奖评语:石舒清的创作多以西海固为生活背景,以短篇小说为主,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精神和艺术思维特色,他的作品沉静,深邃,从容,神秘,语言精雕细刻,富于张力,他以“对平凡事物的惊异”,表现西部农民的纯朴和善良,顽强和宽厚,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精神信仰的执著。
二爷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其实这个能说明个什么呢?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在里面呢?但虚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实起来,需要打你成右派时,这又成了一个很结实很堂皇的理由。果然把二爷一下子就弄成了右派,而且使二爷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好讲。
对于整个一个时代的迫害和诬陷,人往往是容易接受和顺从的,看到大批与自己一样甚至优越于自己的人,都一一从高处掉了下来,有些不知什么原因掉得比自己还要低,人心由于平衡会安宁下来,甚至看到那些摔得更惨掉得更低的人,会因此觉到奇异的安慰和运气。
二爷是兰州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在固原地区法院工作。一打成右派,法院是不让工作了,让去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和社员们一同参加劳动。二爷就去了。照父亲他们的话讲,二爷是太爷和二太太惯下的,袜子都没有自己洗过;去理发,太爷或二太太都要陪着的。祖太爷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盘下的一点家业不但没能使自己得益,反而把他的儿子造就成了一个有些纨绔之气的人,别的且不说,仅老婆,太爷便有着两个的,一个是我的太太,一个就是二太太。二太太是太爷从大教里娶过来的,我们这里的人把汉族人叫大教里的人,大教里的女人似乎与我们回族的女人有着某种不同,从太爷对待两个老婆的不同态度上,也可看出这一点来。太爷对我太太简直是有些毒辣无情,对二太太却是用情备至,言听计从,使得惯于享受的二太太连烟也抽起来了,这在回民人家真是很罕见的。太爷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太爷过世后,又把所余的细软尽数留给了二太太,二太太除了抽烟一时不能舍得外,别的享受都统统戒掉,一门心思培养起二爷来,培养得二爷像一个少爷。说来太爷的眼力还是不差,比较于太太,二太太果然总是棋高一着,就拿培养儿子来讲,二太太就把二爷供养成了一个大学生,这在那个时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可惜在二爷上学期间,二太太就去世了。二爷也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二太太有一个很名贵的玉石烟嘴,二爷就用这个烟嘴抽烟。像二爷那样的身份,对象是很容易谈的。二爷后来找了一个当妇联主任的女干部,两个人分居两地,大多数时候,都在各自单位上灶,很少一起吃顿饭的。说来他们小两口即使住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会做饭的人。二爷自然是不会做饭的,但他费心娶到的二奶奶也只会工作,只会当妇联主任,只会对着群众讲话,针线茶饭却不能做要求的。
二爷下放到村子里和社员们一同劳动时,他所遭的罪便可想而知。别的且不说,劳动他就不能的。农村的活儿,他几乎什么也不会干。转粪的时候,他不会用铁锨;便让他背,但是粪背斗却会拖得他坐下来;拔麦子的时候,和别人的蹲了拔不同,他是跪在地上拔,嘴上也将力用着,但是麦子像是瓷实得很,不给他轻易拔下来。他像拔树那样拔麦子。拔下来的麦子抽在他的脸上,麦芒刺到眼睛上,痛得他缩成一团,将衣袖挽起来,用胳膊揉眼睛;便让他去放羊,这个连小孩子都能的,但在二爷,又成了一桩不可收拾的事,他总是太过小心,太怕羊一下子跑散掉,总是跑来跑去咋咋呼呼地吆喝,倒把个羊群弄得七零八落。他下放劳动的那个村子叫慢坡村,二爷在慢坡村劳动了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又被弄回到了县招待所,让他当厨师。二爷哪里会当厨师,他连一顿粥也不会做的,让他去当教师教书倒可以的,但是已经被弄进了招待所当厨师,他就当厨师。这样过了几年,二爷就算是过得去的一个厨师了。二爷这个人,由于被过于娇惯的缘故,由于是一个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的缘故,心眼儿是不多的,甚至是有些天真和呆气,在一个复杂的境遇里,这一点倒好像是保护了他,使他很少卷入什么是非里去,也极少惹人揣测和疑心,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二爷凭着他的天性却可以轻易地做到。唯一让人感到不快的是他总是有些淡漠,像是和任何人都只愿意保持一个同样的关系,像是和任何人也不可能熟络亲热得起来,这一点人们似乎是接受不了的。人们似乎能接受别人对他的亲热甚至仇恨,却受不了人对他的淡漠。里面有一个胖厨师,他的包子做得远近闻名,又是一个极热闹的人,就忍不住常常对着二爷的无表情少反应做些嘲讽奚落,一次他竟冲上去捏住二爷的脸,摇晃着说,唉呀呀急死我了急死个我了,但除了胖师傅的嘲讽和偶尔一个过激的行为外,二爷在招待所的日子大体说来还是不错的。他那时候已经是离了婚,在招待所的一所单身宿舍里住着,比较于在慢坡村所过的日子,招待所自然是好了许多。二爷是一个不容易显胖的人,但脸色还是不错的。有些人的面包使人觉得他就不能做厨子。与那个善做包子的胖厨子相比,二爷倒使人觉到一种特别的清爽和干净,清爽干净于一个厨师而言,有时甚至比他的手段还要重要。并且二爷的手段也是不差的,二爷的拿手好戏是做鱼和熬鱼汤。这又比不得做包子,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少海鲜的地方,鱼都是从远地运来,一桌菜里,鱼自然要算大菜了。要是换一个人把鱼做成二爷那样子,把鱼汤熬成二爷那样子,不知会怎样地跋扈一场了。即使一个厨师,只要他想跋扈,只要他自认为有资格跋扈,也总是有着其跋扈的地方的,但二爷却不居功不显摆地做着这些,就像是自己的呼吸那样自然和简单。
后来招待所忽然要改革,要裁减冗员,真是没有料到,竟把二爷给精简下来了。二爷就搬了铺盖卷回家去。自从离婚后,家门上常就被锁子把着。院子还是很大的。树上的叶子厚厚地落了一层。风蚀雨淋之故,屋瓦业已暗黑,瓦楞间也长出草来。二爷也懒怠收拾这院子。从院子里走过,会像走过雪地上那样,久积的浮土会落下脚印来。
那时候二爷分到了二亩自留地。开春的时候,二爷也会花钱雇两头牲口,肩了犁走出城去,在自己的那块自留地里犁耕上一番。再没有像二爷那样漫不尽心犁地的人了,他一边犁着地一边抽着烟,犁把总像把不牢似的,一会儿歪向这边来,一会儿倒向那边去,有时候犁把还会脱手,犁就趁机从深土里上来,平躺着让牲口拖了走,这样牲口走起来会是很便当的,牲口也明白了什么似的就走得快些。二爷像是惊醒了似的赶上去扶犁,这样子被拖在地上的犁是不容易扶它起来的。等二爷的犁扶起时,牲口已轻轻松松走过一大截了。二爷一边假意地喝斥着它们,一边频频回头看着没有犁过的地方,连他自己也觉得这像是一个胡闹和玩笑。这样子犁地,其实牲口不但不得轻松,反而会是很吃力的,从表情也可见得它们的疲累和沮丧。后来牲口也得了计,一旦警觉到犁把从二爷手里脱开,它们几乎同时就拖着犁铧跑起来,不让二爷轻易地追上它们。有时竟一鼓作气跑出自留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等二爷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它们已沿着沟畔吃进不少草了,而且闲闲地摇着尾巴,喷着响鼻,对二爷有着某种嘲弄和轻蔑似的。畜牲们也是有眼力的,它们清楚它们即使不务正业,由着性子撒了泼地跑,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它们已经算是见识了那个人,它们清楚他不过是个追它们而已,只要它们真的要跑,那他是怎么也追不上它们的,即使追到了又怎么样呢?他又不会拿鞭子打它们,地里到处是硬土块,很容易捡起来砸到它们身上的,它们也不是没有挨过,但在他这里,却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就使得它们清楚他是不会这样干的。那它们就乐得跑,乐得让他追,乐得让他追不上,乐得让他追上了再把它们给吆回去。有时候要是它们吃草正到兴头上,就不愿一下子被他吆了回去,它们直着脖子吃草,听任他在后面拖拽着犁铧吆喝个不已,听任他的鞭子在半空里徒然地绕来绕去。它们微眯着眼吃草,像使自己在一种笃定或幻觉中似的。它们也会斜了眼角看看那个在一旁忙乱个不已的人,它们看得出他和它们所见的犁地者有着许多不同,凡犁地者大多是不穿鞋的,大多赤脚走在犁沟里,它们看到他不但是穿着鞋,袜子也穿着的,这就使得它们不愿意在他跟前安分地做牲口。而且事实证明它们是对的,当他实在吆喝不动它们时,就丢开犁铧任它们吃草,他自己也在一边蹲了,掏出那个玉石烟嘴抽烟。风吹得他的脸像干土块一样。烟从他嘴里冒出来,很快就会被风带得不见了影踪。一边抽烟,他会一边出神地看它们吃草,或者眯缝着眼看向远处去,像是一时节忘记了有犁地这回事。
这样子的犁地,庄稼自然是不可能长得好。二爷的自留地里种的多是小麦或扁豆,等它们长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苗垄的断断续续和歪歪扭扭,就像一个盲人缝的衣裳,针脚粗大别扭不说,还不断地离开针线,冲突到不该有针脚的地方去。这样的庄稼实在是没有个什么收头。每年收庄稼的时候,二爷总是来我家把小叔叫去帮他。有时候把我也一并叫了。二爷螃蟹那样支楞着手脚在地里拔粮食,拔几拔就像受惊的黄鼠那样,直起身子来向四下里看着,也不知他在看什么。一会儿就见他已经蹲在了地埂儿上,一边抽烟,一边很有些认真地捉取着沾在裤腿上的一种叫冉冉子的草,那草球状,上面长满了小刺,很容易就会沾你一身。二爷抽着烟,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捉取着裤腿和鞋袜上的冉冉子,许多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日头慢慢地高起来,而且不断地加强着它的热力,使得二爷身上的冉冉子也干硬起来,它们沾得那么紧,一个个多足的小虫子似的,不让二爷轻易就把它们从身上取下来。
等收完粮食,二爷总是要给叔叔扯片布做件衬衣。带叔叔到裁缝铺去,等衣服做好,叔叔穿上了,才打发他回来。我正是看到叔叔有新衬衣穿,才乐意去给二爷拔粮食。但二爷没有做衬衣给我,记得他给我买了一双球鞋。鞋显得大,叔叔穿来却有些小。但叔叔却总是趁我不备就悄悄穿去了,直到把他的两只大拇指从鞋尖上穿出来。
到碾场的时候,二爷又会叫叔叔去帮着他碾场。往往一个春夏下来,所谓春种夏收,辛苦一场,但二爷收获的粮食往往还不足两麻袋,要是早年,就连一麻袋也不能满。二爷自己没牲口,一年耕播拉碾,都免不得花钱的,还要给叔叔做衬衣,也是一分花销,算下来头比身子大,那么,二爷何必要种这几亩自留地呢?倒不如让它荒着去省心。
但是父亲说,他不种人骂呢。然而把好好的几亩地种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怕人骂么?
说来二爷的生计倒是不靠这几亩地,要靠这几亩地,就那点收成,他也是一饿死,从招待所精简回来后,二爷又学了一门手艺,给人糊顶棚。二爷个头高,踩一张桌子就能够着任何一个顶棚的。不清楚糊一个顶棚多少钱。记得二爷那时候几乎是天天有顶棚可糊,私人而外,也给公家糊。父亲和叔叔都被二爷叫去帮他抹糨子。我后来到城里上中学时就住在二爷家里,整整住了八年。星期天,二爷总是带我去糊顶棚,帮他抹糨子。我记得给县革委会都糊过顶棚的,那顶棚很高,二爷踩在桌子上,踮起脚尖,将裤腰带都全部地露出来,还不容易够得上。但二爷的手段是高明的,那些实在够不到的地方,他就把纸张顶在长刷子上,轻轻地顶上去让纸张先贴住顶棚架,然后再调整位置和方向,等一一调整好,二爷就用大刷子左左右右地刷几刷,使垂下来的边边角角都得到某种命令似的收紧上去,那么地熨帖而又吻合,真使人暗生佩服。而且二爷的最后那几刷,漫不经心,又痛快淋漓,每每那个时候,轻车熟路似的,二爷在那种大笔挥洒里似乎在信手展示着一种什么,又像在尽情地宣泄着一种什么。我觉得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二爷的精力才得到了蓄积和恢复,不然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仰脖伸臂在高桌子上那样劳碌一天,不要说他,年轻人也受不了的。
二爷的话极少,常常用嗯啊的方式指挥着我,和我交流着。往纸上抹糨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有时候一不小心,某一个地方就漏了抹或是抹得不够,这样子到了顶棚架上立马会显现出来,二爷驾轻就熟地挥着刷子,但是有那么一角总像是折断的鸟翼那样软软地垂下来,像一段探出的舌头在戏弄和嘲弄你,这就说明那里的糨子不足或竟没有,这时候二爷的情绪总是不好的,他够住那段舌头,将纸张整片地撕下来,任由它飘落到地上来,然后他也不说什么,举头看顶棚或看着别处,脸上身上的糨子也懒怠擦一下。我忙忙拾起来重新抹糨子。将纸张侧着看过去,看哪里不发亮,就说明哪里可能没抹到糨子。
我个头矮,把抹好糨子的纸张给二爷递去时,二爷就得俯下身来接,二爷是个头很高的人,这就使他的弯腰多时候显出一种危险来,但熟能生巧,后来二爷就探下刷子来捞我的纸张,一捞就捞去了。这个实际上是不好捞的,功夫不好的人,即使一时捞到,也容易在半途或即将送到手里的一刻使纸张滑飘出去。这些不足挂齿的劳动实际上也是很有些让人惊讶和佩服的地方。但时间久了,也使人觉得厌倦,我只是坐在地上抹糨子罢了,有时候也觉得烦,觉得疲累,觉到某种深陷其中与难以挣脱,不知站在高桌上踮了脚尖伸长着脖子刷来刷去的二爷又是怎么想的。他是极少说话,好像说话会是一种多余甚至麻烦,有时候糊整整一天顶棚,他也说不了一句话,他只是偶尔地清清喉咙,咳嗽几声而已。当他踮着脚尖,伸直着脖子往顶棚架上小心地送纸张时,我看见他的脖子一时绷得那么紧,喉结也承受着某种压迫那样,艰涩地一动一动,似乎只要拿个刀子临近着比划比划,那不安的喉结就会破皮而出。这时候,真是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和焦虑的,但也总是有惊无险。劳作之余,二爷会带着我去看一场电影或篮球赛。比较来说,二爷似乎更喜欢看篮球赛,那时候,我们的县体育馆也还活跃着的,常常会有一些赛事。二爷的习惯是早早地将票买好,装在钱夹里,然后就一心一意地糊顶棚。但他的心里明显是惦记着赛事的。二爷的胳膊上有一块老旧的手表,当窗外有了暗影,屋子里需要开灯时,二爷就会频频地看表,忽然将刷子丢下来,抬头看着还没有糊完的地方,像是有某种茫然和遗憾似的。这时候我就知道二爷是要去看篮球赛了。果然他有些僵直地蹲下来,双手按住桌脚,我忙忙将一把椅子搬到桌子跟前,看着二爷的一只脚像病人那样小心地试探着向椅子上落去。
有时候糊毕顶棚,要是没有篮球赛,要是县剧团正好演一场戏,二爷也会买了戏票去看戏。篮球赛尤可,电影自然更好,但老戏,我是不怎么爱看的,然而怎么办呢,二爷他已经把票买好了,总不能让作废掉吧,只好同着去看。有时看着看着,我就睡过去了,觉得二爷推我时,戏已经完了。我牵着他的手,懵懵懂懂地回去。对于二爷的看篮球看老戏等等,父亲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有些不屑的,啊,辛辛苦苦挣下的几个钱,脏不拉叽累死累活给人糊顶棚挣下的几个钱,倒拿去看那个,看了能顶个啥用呢?不看又是个啥损失呢?还不如买上几斤米,要么买上几两茶叶喝喝,解解乏气,也是可以的嘛。这是父亲他们的意思,父亲他们即使有一张电影票戏票,也会想办法换成钱,拿这钱来再干点别的。
我上初二的时候,53岁的二爷忽然获得了平反,又可以到地区法院去工作了。那时候私人不算,就是县上大大小小几十个机关的顶棚,也几乎被二爷都糊过了。
二爷原本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学得最精的却是熬鱼汤和糊顶棚,不知道平反后,他积数十年之功学得的这两门手艺还用得上不。
原载《青年文学家》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石舒清,本名田裕民,男,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