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仲联先生
2008-07-10陈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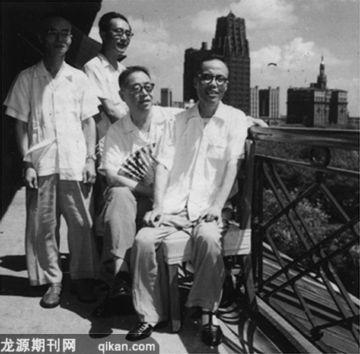
钱仲联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笔者有幸自1958年夏起与之共事6年,1964年春调回南京后,与之再聚已是30年后的1994年夏,此后未曾有缘再见。如今钱先生已归道山数年,近年有弟子、友人先后送来钱先生两封信的复印件,半个世纪前与先生交往的情景又涌上心头,悠悠往事并未如烟如云。
苏州相识
1958年,江苏师范学院(今之苏州大学)要恢复于1955年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今之南京师范大学)的文科,而南京师院同样要重办同时并入江苏师院的理科。两校抽调相关教师互相支援,以中文系而言,南京师范学院派出以刘开荣为首包括钱仲联、耿某、孙某、翁某、应某几位先生去苏州。笔者当年正在南京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的工作,原拟在文学所成立后去所里从事研究工作,而国务院新任命的江苏师范学院院长刘烈人在去苏州履新之前,也在南京罗致人员去苏州工作,笔者便被动员去该校任职。
暑假期间我即被催去报到,到达苏州站时居然有人事处某处长来接。报到后某一日,新被任命为系副主任(正职缺)的刘开荣先生特请耿某一起陪同我游览苏州园林。饮茶之际,刘先生含笑对我说:“我们有不少课程尚未有教师担任。听刘院长说,他从科学院要来一位先生,我们的期望很大呢,不曾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听了这番话语,我方明白何以有人事处长接站之举,如今见到人后,怕是既感意外,也有几分失望。不过,话说回来,院、系对我这样一个1953年大学毕业(毕业时21岁)的青年教师还是信任的,当时院方任命钱仲联先生为古典文学教研组组长,我为副组长,系里又任命我兼系资料室主任。当时古典文学教研组仅三名教师,钱先生与笔者之外还有一位当年从华东师大研究生班毕业分来的助教。教研组后来不断充实,人员渐多,乃升格为教研室,钱先生与笔者继续任正副主任。
当年我知道钱先生曾对黄遵宪、韩愈的诗作进行笺注、系年、集释,很有成就,但他的职衔却是未曾定级的教员,虽不知就里,也不便询问。任命后不久,总支书记把我叫了去,说:“你虽是副的,有事可要找你。”我有些不解,他接着说:“你知道钱仲联的历史么?”我说不明白,他也只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让人感到是在民族气节方面有些问题。接着又问我:“你知道金某某是什么人?”我自然不明白,他便明确地说:“他是教授,但是个右派,派在资料室做资料员,你要好好督促。”经他这样“提醒”,我虽凡事要向钱先生汇报、请示,对他的学问也很钦佩,但在日常相处时不免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民族气节问题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相信,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情景都能理解。我们之间这种不亲不疏的状态一直保持到1964年春我离开苏州为止,而钱先生的“教员”则一直做到“文革”后的1979年,恢复教授职称后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会朱季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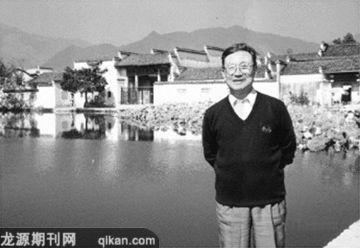
1958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在办公室内遇见钱先生,他说起在南京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有唐圭璋、段熙仲、徐复等先生可以交往谈学,如今调来苏州,已无人可以共同探讨学问了。他说,北京友人建议他可以找章太炎弟子朱季海交往,但经友人联系,朱季海先生既不愿来江苏师院拜访钱先生,又不愿意在家中接待钱先生前去拜访,而是建议星期日在怡园见面。钱先生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两个不曾见过面的人,在公共园林中如何碰头呢?”当年没有可以随时联络的手机一类的工具,这的确是个难题。我立即自告奋勇地对钱先生说:“不要紧,我认识朱季海先生,可以陪你去。”钱先生大喜过望,就问我是如何认识这位“怪人”的,我便一五一十地讲给钱先生听。
1956年暑期,我应大学时代外文系一位同学之邀去苏州游玩。她的家住在山塘街,前临街,后背水,房舍逼仄,不便接待,就把我安排到她的同学沈某家。据说沈某是《浮生六记》作者沈复(三白)的后人,家在学士街天官坊,所居宅第据说是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的一处房产,出借或让与沈三白后人居住的。前面是几进高堂大屋,后面有玲珑精致的花园,园中有一座二层的读书楼,我独自住在这座楼的二层上,早晚对着房内悬挂的联对:“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名句。推开窗扉,满园青翠,夹杂着红红白白的花卉,墙外不时飘进一两句吴侬软语的市井叫卖声,让人真不知身在杭州(临安)还是苏州。正当遐想时,我的同学在沈某陪同下叫我去客厅早餐、会客,原来她们请来曾经在桃坞中学任教的朱季海先生一同早餐。餐后闲谈,朱先生便向我发问,有关中外古今的文史问题,他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面对长者不断地考问,我真有些惶惶然,难以招架。午餐后继续,直到傍晚方止,因此与朱季海先生仅此一会,已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事后,我有些嗔怪,但同学说:“朱先生对你印象不错呢。”时过境迁,事后也就没有任何联系,想不到两年后却对钱先生与之相会起了作用。我在约定的周日早晨陪同钱先生去怡园,两人终于见面。
此际,朱先生赋闲在家,我们曾向领导汇报,建议请他来校任教。但他提出的几项条件之一,在当时形势下任谁做领导也不能同意,此事遂作罢。
常熟购书
资料室初建,藏书极少,除从院图书馆选调部分图书外,还需多方采购。有一天钱先生找我,说常熟县图书馆有不少《燕京学报》待售,可以去购来。经领导同意后,我便与钱先生去常熟。
常熟乃人文之乡,藏书楼甚多,有名者如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赵宗建的旧山楼等,其中特别以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声名最著,与聊城杨氏的海源阁、归安陆氏的皕宋楼、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并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去常熟购书,我们自是抱着很大期望,可是此行却空手而归,不知是早已脱手还是另有安排。
购书不成,钱先生便领我去王四酒家午餐。钱先生点了常熟名菜如该店的油鸡、黄笋豆腐之类,并向我作了介绍。餐后又去附近的兴福寺游览,钱先生介绍此寺为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舍斋兴建,最早名叫大慈寺,梁时改名兴福寺,因位于破龙涧附近,所以又叫破山寺,有石幢、破龙桥、空心潭、日照亭等胜迹。

听了钱先生对常熟饮食、名胜的介绍,又听到钱先生地地道道的常熟话,我不免随口而出:“钱先生是回家乡来了。”钱先生听了此话,颇有些激动,立即声明:“我虽然生在常熟,但原籍却不是常熟,是浙江湖州。我的书室名叫梦苕庵,苕就是指吴兴的苕溪。”
于是,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家世:他原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本是务农人家,曾祖开始读书,成为秀才,直到祖父钱振伦高中进士,家世才渐渐显赫起来。钱振伦曾任四川乡试主考,主试完毕后返京,升任国子司业,其岳父翁心存曾任国子祭酒。祖父因母病辞官返乡,以教书、著书为生,有《鲍参军诗注》等著述。祖母为常熟翁氏,其弟翁同龢为咸丰六年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为同、光两朝帝师,死后追谥“文恭”。翁氏在其夫振伦死后,生活无着,乃携子回到常熟母家,依弟同龢为生,未再返回吴兴。因此,仲联先生出生在虞山之畔,却常想望先世故土吴兴,用“梦苕”命名书室乃是不忘先祖乡土之情的表现。
常熟之行,虽未能购得一卷书籍,却了解到钱仲联先生的家世大略,对后来的一些传言也就能加以辨别。
推荐撰稿
建系之初,我除了担任一年级的教学外,还要准备新生升入四年级时的元明清文学的讲授工作。由于钱先生声言不治小说、戏曲,这一段古典文学的教学任务便由我承担。在新生升入三年级时,也就是1961年秋季应该讲授唐宋文学时,钱先生却于该年5月底被借调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留下的课程便由我和另一位先生承担。这一经历,笔者在《学林寻步》一文中有所交代,兹不赘叙。
当年可以见到的文学史著作很少,连许多古典戏曲作品也不易借到。为了讲好课,必须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讲义,我除了上好一年级的文选、习作课外,到1962年该讲授戏曲、小说内容时还完成了百万字的编写任务。大约在1960年底,学校办了个自编教材展览会,我编写的部分教材经教研室推荐被系里选报上去公开展出。1961年3月22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江苏师院积极培养红专师资队伍》,其中还提到我所编写的教材。这些讲义讲稿,钱先生不可能全部看过,但起初要抽一些看看——也就是审查。大约我所编写的教材讲义,他还比较满意,后来也就不再看了。
1960年初,钱先生在教研组开会之后对我说:“中华书局有约稿,你写我也写。”选题便是《李玉和〈清忠谱〉》。我在2006年五六月间接受《文艺研究》访谈时说起此事,还以为是中华书局有人来苏州约稿的,直到是年8月,我的一位已取得博士学位六七年的弟子孔庆茂君送来钱先生给中华书局的信以及中华书局复信的复印件,方知是钱先生写信推荐的。2008年元旦前夕,《藏书》杂志主人金小明、徐雷两位先生又送来钱先生给中华书局的第二封推荐信的复印件。第一封信是1960年1月16日写的,第二封信是同年2月8日写的,先生不足一月连续两次写信推荐,令人既感激又难忘。特将两信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封信:
我院讲师陈美林同志,擅长古典戏曲,文笔生动流利,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较深,可以参加编写一些这方面的读物。特为介绍,请示复为悉。
第二封信:
介绍陈美林同志参加编选杂剧传奇一节,未蒙赐复。陈同志青壮年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定修养,文笔流利,专攻古代戏曲,用力至劬。联意在这方面有兼擅新旧之长之陈君,如果从事编选,必能做出出色成绩。
《藏书》在刊出第二封信的同时,还介绍了此信的拍卖情况,说是“钢笔书写,一通一页”,“起拍价60元”,“浏览次数239”,“最高出价410元”。还有点评说:“钱先生是著名诗人、词人、国学大师,这件手札既是一件珍贵的墨宝,也是一件重要的史料……钱先生连续两次推荐了青年学者陈美林参加编选杂剧传奇的工作,信中对陈美林先生在古典戏曲研究方面的能力充分肯定。如今陈美林先生以古稀之年依旧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确为钱仲联先生所言‘做出出色成绩了。”钱先生所推荐、中华书局所约定的《李玉和〈清忠谱〉》一稿,我在与友人合作下于1961年6月交稿,1963年发排,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80年12月才根据1963年校样印了出来。从约稿到见书整整二十年!这正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色。往事已矣,但钱仲联先生不足一月的两次推荐,可谓不遗余力,是不能忘却的。
信函墨宝
仲联先生已于2003年12月仙逝,我检点书柜,有先生手札一通,著作一部,墨宝三件。
1981年夏,我将钱先生推荐之《李玉和〈清忠谱〉》以及新出的《杜甫诗选析》寄给钱先生。他于7月5日复信云:“惠赐杜诗选析、李玉和清忠谱二册,拜领谢谢。”信中只说杜诗“解释得十分好”,而于他所推荐的李玉戏曲却未置一词,这可能是其时我在《光明日报·文学》、《社会科学战线·形象思维论丛》上发表了几篇论杜诗的文章予钱先生以一定印象,而钱先生又不研治戏曲、小说所致。
钱先生赠我的墨宝有三幅,其一为横幅,写的是两首《买陂塘》词,并有题记云:“光绪戊戌冬,文恭舅祖西山墓庐落成,有《买陂塘》词二首”,其后人“笃念世德,绘图嘱题”,钱先生便“用文恭词韵”写了这两首词。后题“己未冬至录奉美林同志两正”,落款为“虞山钱梦苕”。“光绪戊戌”为1898年,文恭指翁同龢,“己未”为1979年,落款又强调“虞山”、“苕”溪,仔细揣想,不无深意。因为当年有人误认为钱先生与由明入清之钱谦益有“远亲关系”,钱先生在访谈录中也明说见于日人所著《金陵学记》。该书作者坂田新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我国活动,虽然笔者与之毫无接触,也未见过《金陵学记》一书,但知其曾在南师大访学。钱先生当年赠我这一横幅,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1984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吴敬梓研究》,收到样书后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不久收到他所题赠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和一幅条幅,写的是钱先生“甲子秋游嵩山中岳庙诗”,“录似美林道兄两正”,落款为“钱仲联”,未再有“梦苕”字样。
1994年孟夏,我应王钟陵教授之邀前往苏州大学,为其研究生主持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秘书为周秦,我从与他的谈话中知道钱先生仍住在原处,便去螺丝滨10号拜望。敲门后,是先生亲自开的门。此际我与钱先生分别后已整整三十年未曾见面,所以我第一句话就是:“钱先生,我是陈美林,还记得么?”钱先生仍然一口地道的常熟话:“记得咯,记得咯。”一边谈话一边让进后房,我们谈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往事,既感到亲切,也难免有些神伤。返宁不久,便收到他寄赠的条幅,内容为“己未滇游诗”,“录似美林方家两正”,落款为“甲戌孟夏八十七叟钱仲联”,同样未再用“梦苕”。己未为1979年,甲戌是1994年,“孟夏”正是我去拜望他的时日,可见在我走后他就写了这一条幅。此后,我未曾与先生再有谋面机缘,连他的仙逝,由于没有及时收到讣告,也是事后方知,自然不能有所表示。近年接连读到钱先生当年所写的两封推荐信,虽已过了近半个世纪,但感念之情并未稍减,乃为此文,以为追忆与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