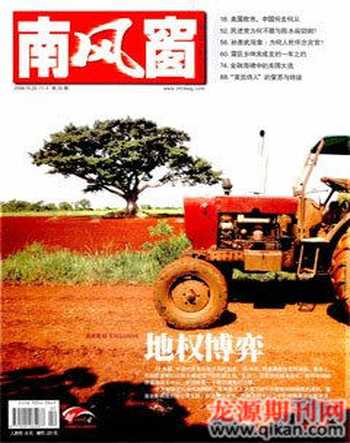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官员诗人”的复苏与终结
2008-05-30曾念长
曾念长
近年以来,在经历“打工诗人”、“老板诗人”等一系列概念炒作之后,与诗人有关的第三个概念——“官员诗人”于2008年成功面世。先是坊间流传安徽天长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叶世斌被国内某民间组织推荐为“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后是广东省中山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丘树宏获得由《诗选刊》颁发的“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项。
“官员诗人”的高调亮相得到了当代诗坛知名诗人的捧场。著名诗人多多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颁奖仪式宣读了颁奖词,而在当代诗歌史上被公认为先驱人物之一的食指则当场表示:官员写诗是一种时代进步。食指的话是“金玉良言”。他不仅为“官员诗人”的出场说了好话,而且为“官员诗人”从现实存在转化为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概念提供了“理论铺垫”。
按照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人类精神生活史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它们可以分别表述为结构、情势和事件。通过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
官员诗人的历史检索
那么,中国“官员诗人”的“长时段史”是什么呢?
丘树宏获得“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之后曾经感言:中国本来就有“官文一体”的传统。中国“官员诗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雅言”(也就是后来的“官话”)在权势阶层的逐步推广,训练有素的官员在诗歌写作中获得了文字传播上的优势。
从唐朝科举制开始,诗歌则作为官场的一种实用文体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中,赋诗作文逐渐内化为官员的基本技能。到此为止,“官员诗人”已成为一种稳定性的身份,而且规定着中国诗歌写作的主流传统。两宋时期,中国的“官员诗人”在身份构建上一度达到了巅峰,再加上当时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话”,“官话写作”已牢牢占据了中国诗歌的主流。从“长时段”来看,“官员诗人”与“官话写作”在自先秦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史中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存在。
但是,这种持续性的结构从历史某个时期来看,却常常出现“中时段”的破坏。这是因为,自秦以降,中国政权的更替大体上是通过农民起义来完成的,新政权的不少官员往往出身贫农,一开始并没有掌握“官话写作”的语言技能。即使如此,“官员诗人”的身份依然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得以修复。新政权官员往往先是以“民歌写作”代替“官话写作”,而后通过科举制度实现新生代官员向“官话写作”的回归。这正是“官员诗人”传统的自我修复机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刘邦、朱元璋这些贫农出身的开国皇帝虽然未受过正规的诗词训练,却留下比一般诗人更多的、广为流传的诗作。这是以“官本位”为最大传统的中国诗歌写作史赋予他们的一份额外奖励。

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权之下的官员大多出身贫寒,“官员诗人”由于话语资源的极度匮乏再度陷入了“身份危机”。相比之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身份危机”,新中国的“官员诗人”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科举制已经废除40多年,大大削弱了“官员诗人”的身份修复机能;第二,新体诗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写作形式,探索性的写作令“官员诗人”无所适从;第三,近代中国以来专业化诗人群体的形成,分割了“官员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的话语权。第四,工业化建设导致“技术官僚”群体的崛起,从而致使“官员诗人”群体的进一步萎缩。
但是,这种“中时段”的历史情势阻挡不了“官员诗人”向“长时段”结构回归的步伐。1958年,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其初衷是解决当时的“诗歌创作形式”的问题。他在当年3月22日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道:“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毛泽东是新中国政权中最高级别的“官员诗人”,由他发动的这场“新民歌运动”在郭沫若、周扬等“官员诗(文)人”的大力贯彻之下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张开来。以“中时段”视角来看,它正是在新政权的历史情势之下,“官员诗人”试图从民间歌谣中吸收话语资源以修复自身身份的一场政治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干部带头、任务下达、人人创作、日日高产。这场运动实际上只坚持了一年就偃旗息鼓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建设和制度化的保障,它并没有对新中国“官员诗人”的“身份修复”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紧随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则一步摧毁了这种修复能力。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诗歌运动。但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不同的是,这场运动的主导者并非来自高层官员,而是来自民间的文学社团,并且运动主体大多是获得学校教育机会的青年学生。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场运动大约持续了10年,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一批又一批诗人成长起来,成为影响90年代及以后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势力;二是为“官员诗人”传统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特别是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人人接受了那场诗歌运动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中高层干部。
本文开头提到的叶世斌和丘树宏就是在8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官员诗人”。
诗人传统的异化
自70年代末的“朦胧诗”运动以来,10年一次的诗歌运动似乎成了又一个“中时段”的历史规律,从而为“官员诗人”传统的延续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前面说过,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古代“官员诗人”传统的关键力量。1905年,科举制戛然而止,但“官员诗人”的传统不会止步。已经运作了1000多年的传统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存在,足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自我更新的生存能力。
事实上,当代官员写诗相当普遍,构成了当下极富中国特色的几种“诗歌文本”的重要来源:
第一,酒桌段子诗(打油诗):酒酣耳热之后产生的各种“红段子”、“黄段子”及其混合体是当代最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这些杰出文本的主要创作者是官员。在酒桌上,段子诗的生产往往遵循着一种“官序原则”,即酒桌上的最高长官是段子诗的主要发表者(但未必是原创者),下级官员则充当聆听者和喝彩者的角色(相当于读者和品评者),这种“官序原则”同样适用于职称论文署名的潜规则。必须补充一点,酒桌段子诗是当代“口语写作”的一个重要支流。也就是说,当代官员虽然还是“高产诗人”,但在许多场合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八股式的“官话写作”,这是科举制被废除的一个重要
后果。
第二,官场应景诗:应景诗是中国传统官场的一种重要润滑剂,也是中国官员的必备修养和技能。这种传统的坚固性即使在技术官僚迅猛崛起的今天,依然得到有效的继承。通过对汗牛充栋的各种人物叙事文本的解读,我们发现,多数以自然科学技术起家的中国官员依然保持着对古诗词阅读和创作的日常坚持,还有一批技术官员在年轻时代写了大量的现代诗,并将这种癖好带到官场中去。从常理上讲,公务繁忙的官员不可能沉心到诗歌的世界中去,但是,这种叙事路径的一致性反复告诉我们:当代官员依然普遍重视自己的诗文修养。
“官员诗人”的应景诗广泛地消融在以下三种文本载体中:一是汗牛充栋的官员人物叙事文本,叙事作者在介绍官员的时候往往会渲染官员的文学素养并引用官员创作的诗句;二是各种公开场合的官员题词,它是一种集成了中国诗词和中国书法的代言艺术,成为官员展现其社交素养的一种基本技能。三是官员出版的诗集。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官员出版诗集的情况,但是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多数官员都会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自己多年来的应景文字出版成书。这种时尚甚至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优雅式腐败”——据2008年9月8日出版的《瞭望》周刊透露,近年来内地大大小小官员已出书成风。仅以湖南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短短几年出版一本书法作品集和一本诗集,并以摊派发行的方式创收3000多万元。
第三,官刊体制诗:“官刊”指由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审批、由国家文艺单位主办的文艺报刊。“体制诗”指以官刊为主要传播载体并接受“体制美学”检验的诗歌作品。中国所有官办文艺刊物的宗旨可以归结为:培养社会主义文艺接班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种功能定位隐秘地引导着中国的官刊不断对其作者进行身份检查,将那些具有明确体制身份的写作者圈定为官刊的有效作者,从而降低办刊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一来,中国的官刊成为从高层到基层的大大小小官员的发表园地。这是身份检查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美学身份”的检查。文艺官刊的编辑实际上是国家的“美学警察”,通过发表/不发表、创作培训等方式来不断规训出合格的国家文艺工作者。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官员诗人”显然是最容易通过双重“身份检查”的合格创作者,也是“官刊体制诗”的主要创作群体。
以上三种诗歌文本基本上构成了“官员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全貌。随着科层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加剧,“官员诗人”在内部也逐步分化为专业和非专业两种。前者是指在国家文艺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诗人”,后者是在其它国家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诗人”。此二者虽然出现了官僚部门的分化,但在作协等半官方化的群团组织中又实现了横向的联系,从而共同构建起“国家文艺工作者”的人力资源体系。
在纸质出版物占绝对优势的19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经由国家文艺刊物和出版社正规出版的诗歌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大大小小的“官员诗人”手中。但是,由于“官员诗人”已从科举时代的“显身份”退出,进入“隐身份”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官员诗人”这个群体的存在。
终结的传统
正如前面对“官员诗人”的三种文本的分析,官员写诗在当代中国官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这种官场惯习是一份来自传统的文化遗产,它将继续支配着中国官员的日常趣味。此外,由于当代诗歌写作承载着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官方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注意引导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官员诗人”的主流传统。很难说,这种意图是否可以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诗人”这个具有历史传承的群体并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会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继续丰富和延伸。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官员诗人”虽然继续与诗歌这种文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专业的分化,他们已经退出了“艺术引领者”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极少数的专业诗人。就整体而言,当代“官员诗人”已不可能像古代的“官员诗人”一样创作出他们所在时代的最杰出的诗歌作品。因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官员已不可能投入到当代诗歌的先锋性探索中去。这个问题也反向说明了当代诗歌创作与传统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并不是在否定当代“官员诗人”的存在价值。作为一个有着千年传统延续的存在主体,“官员诗人”依然在当代极富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体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他们的“酒桌段子诗”,虽然在文学这个价值向度内毫无意义,但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大量在文化观察上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文本。
“官员诗人”的复苏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喧哗。但是,将2008年的“官员诗人”现象仅仅视为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新闻泡沫,却是一种肤浅的失察。即使是从“短时段”来看,“官员诗人”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果把观察的时间尺度稍微拉长一点,将“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官员诗人”这些哗然一时的热点现象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的现实背景。
留意官方媒体文献,我们会发现,“官员诗人”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各种主流的新闻叙事中。但是直到2008年,这种日常关注才转化为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热新闻”。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官员诗人”这一话题的传播在广东地区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动。除了广东地区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2000年以来,来自广东的诗人和媒体人自发推进了一场持续性的“诗歌大省”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已被官方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宏大叙事中去,而“官员诗人”的话题恰巧构成了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从“老板诗人”到“打工诗人”再到“官员诗人”,这一系列概念的策源地均在广东。它展示了一个南方经济大省对当下文化进行干预的特有模式。“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和“官员诗人”并非广东独有,但活跃在广东地区的这些主体最早以“概念炒作”的方式将自己推到时代的前台。
“概念炒作”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技法,它往往发生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地区:第一,工业经济发达;第二,商业意识形态相对成熟。以上两个条件在21世纪的广东地区最先发展到了完备形态。前者是“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官员诗人”跃上历史舞台的经济基础,后者为这些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态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但是,相比之“老板诗人”和“打工诗人”,“官员诗人”显然要特殊得多。因为“官员诗人”并不是“新新人类”,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恒常存在。新经济形态只不过是刺激了“官员诗人”在身份意识层面的复苏。这种复苏同时也预示着“官员诗人”传统的某种终结。因为,新经济形态及商业意识形态的崛起必然会进一步瓦解“官员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商业话语的介入,“官员诗人”甚至无力在这个时代为自己举行这么声势浩大的“复名仪式”,然而反向观之,这又是一次“合谋”。这是“官员诗人”在新经济崛起的年代继续延伸其历史存在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