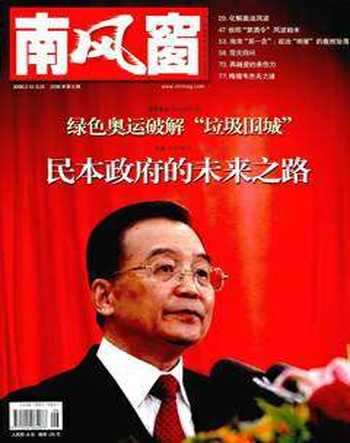“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2008-05-30熊培云
熊培云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国家伦理的革新怎样进行,决定了朴素无华的“五有之乡”(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的理想,是否会沦为“乌有之乡”。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正式提出:全国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邢普委员建议政府“还钱”,难免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
尽管提案看似异想天开,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其结果如何,“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经是一次观念的胜出。而写,在这个建议背后的更是沉重的时代之间,即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国家伦理的革新。
社会分红:阿拉斯加的光荣与梦想
许多中国人在年底都希望能够在雇主那里领到红包,或者自食其力在股市(市场)捡到一个红包,直接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个红包,几乎闻所未闻。有些情景却是时常可见的。比如有些困难户会有机会紧捧有摄像机尾随的领导的“红包”,但那些“红包”更像是救济,显然与真正的社会分红大异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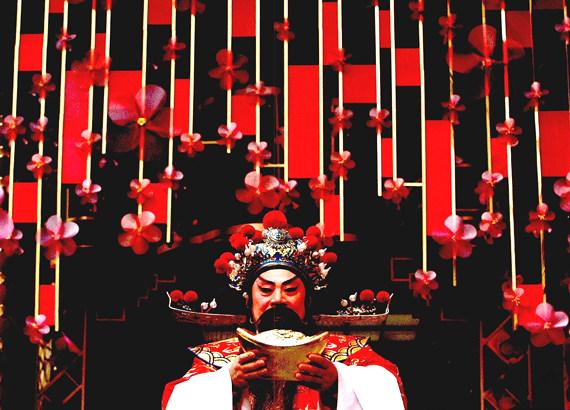
今日世界,与其说“找政府分红”是天方夜谭,不如说是国际惯例。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此前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社会分红”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首先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在米德看来:“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两年后,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的作用。
这方面,人们耳熟能详最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个案莫过于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实践。1968年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普拉德霍湾的土地属于阿拉斯加州州政府所有,次年9月州政府通过油田的租赁获得9亿美元的收入。为了避免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被花光,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提出用这笔钱建立永久基金以造福阿拉斯加的后人。这就是后来由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的缘起。由于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设立,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红。
如今,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等学者在学理层面倡导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外,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相关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会分红”,拥有美国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荣与梦想。
从政府分红到社会分红
2007年8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长达13年之久的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此前一年的2月10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人,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若干年里,国家不仅承担了一些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原属国企的社会职能,而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相关的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与此过去穷困潦倒、无红可分的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财政部数据,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达7700亿元。据财政部研究机构估算,2007年中央企业的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7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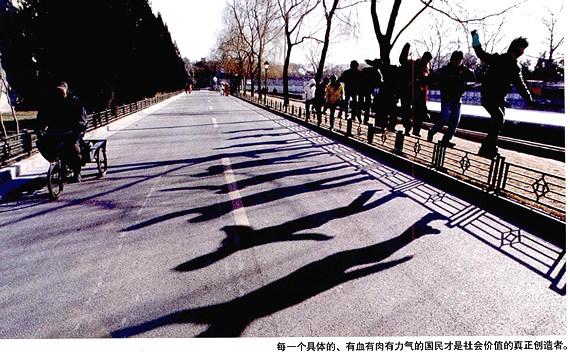
谈到国企为什么向政府分红,世行报告认为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也有利于改善教育和医疗等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另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而言,过度利用留存利润进行产业扩张构成了不利因素。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而缺乏审核可能导致顺周期投资,使经济更易出现大起大落。这方面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三九集团。由于医药、汽车、食品等八大产业盲目扩张,该集团银行欠款已经从2003年底的98亿元增至2005年的约107亿元。
显而易见,这里的政府分红的最后归宿依旧是社会分红,因为国企的出资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担负者既不是通过观念缔结的国家,也不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体的国民、劳动者。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追逐分红而不将这些红利以各种形式归还社会,那么这种分红便可能失去意义。
令人回味的是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府?当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聚敛超量的社会财富,它是否会累积同样深不可测的风险,甚至使国家“三九化”?
倘使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就不难发现,藏富于民或还富于民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于政治层面,即财富的分散效应将大大降低了政府在财富与权力高位中的运行风险。事实上,“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追逐的目标。遗憾的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再度急剧膨胀。
“三九化”:中国政府有多大?
著名学者陈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这样写道: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对中美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进行了对比:在美国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即使土地也只是少量。与此相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1/4的资产。“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政府为什么“越做越大”?政府权力未受到有效约束无疑是主因。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观念上的误区。其一是“国富先于民强”。由于事事“以国家为重”,而政府又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政府与民争利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某种正当性。显然,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国家对某些领域的垄断,同样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上。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许多调控政策,不乐见的是,许多政策收效不尽人意之余,却让政府机构尽得好处。比如几年间名义上为了控制房价而对5年内二手房收取的5%的营业税,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房价突飞猛进地上升,反而因为这一进一出的税收使房价变相上涨一成。同样,“为股市降温”而上调印花税使2007年印花税超过2000亿元,较2006年增长了10倍。从成交额和税率算更超过了过去16年的总和。“管理就是收费”如今变成了“调控就是增加社会成本”。这种既能“偷懒”又能尽得好处的调控,其所损害的必然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这种暧昧同样体现于“监护人政府”这一角色上。和“守夜人政府”不同的是,“监护人政府”在保卫和协调社会的同时,更认为自己较社会更会花钱,有耳光远大。在这样的“大政府,小社会”时代,社会就像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必须将自己尽可能多的劳动所得或者财富压岁钱般通过各种渠道上交给国家(政府),由国家(政府)统一保管和支配。显然,在这里,政府多多益善地掌管钱财并非只是因为“贪婪”,同样源于某种“监护逻辑”,即政府自信能够代替民众花钱,而且花得更好。然而,人性的常识却告诉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才更注重收益,更精打细算。当然,这里所谓的“钱”,并不只是货币,同样包括土地、审美以及公民应有的其他权益。
“发放1000元钱”式的社会分红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内涵?不难发现,这里的“发放”实为“返还”,因为相较于国家或者政府而言,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力气的国民才是社会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回顾30年的改革沉浮,中国改革的一个大脉络就在于将原本属于民众的还给民众。这是一个未竟的价值回归之旅,是在政治上还权于民和经济上还利于民的风雨历程。而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最终仍在于社会是否获得这一关键性成长。有鉴于此,这“1000元”更像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代表了国企的部分红利、属于农民的土地、适时返还的税费,更代表了一种迟到却不失朴素的公正以及一种全新的国家伦理。
“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没有面向社会的分红,不将国民视为股东,国企只能说是浪得虚名。任何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同样不能相信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越多越光荣。
相信许多人都看过一则比较中美两国市长的故事:中国市长敢请美国市长来中国,为其报销来去一切费用;而美国市长说他没有钱请中国市长去美国,因为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同样是嫖娼,有些中国官员会“开发票”,而不久前陷入嫖娼丑闻的德国市长,却因为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妓女那里抵押自己的电脑。
每年两会召开之际,网上网下,都会有许多期许。和往年一样,有关教育、医疗、社保,房價、物价等民生问题在2008年继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们期待有更多民生利好从两会中传出。殷殷希望,诚所谓“民生尚未成功,两会仍须努力。”没有人奢望所有问题都会在两会上彻底解决,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一份份热忱的期许编织的民意,成为两会向上的力量之源。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如既往强调民生政治。就在此前一天,《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民生政治与现代行政之所以相继被着重提出,并且一起指向2020年,正是因为民生与现代行政密不可分。
应该看到,尽管在谈到民生问题时人们多寄望于政府有所担当,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事事都要仰仗政府的亲力亲为,因为社会更应有大作为,更应成为推动时代变迁的主角。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社会里政府当追求“责大权小”。所谓“责大”,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必须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让那些生活于底层者不因时代迁延而被抛弃,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够享受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所谓“权小”,就是政府应该谦卑地使用手中的权力,而且充分放权,使社会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去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让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独立或者合群的奋斗直接改善自己的民生状况,并间接从整体上促进全社会民生的改善。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在30年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成长已是明证。
上世纪80年代,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从整体上告别了贫穷,而社会也在不断的分化与裂变中重组意义。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后,十七大报告将“民生”具体概括为让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而这五个“有所”因被概括为“五有之乡”而为人们寄以厚望。
无疑,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重建国家伦理的30年。走过风雨征程,人们渐渐达成的共识是,为建立一个公正、开放、文明、富庶的社会,必须在政治建设方面还权于民,使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富于民,政府不再身兼“二员”(运动员,裁判员)、与民争利;在社会建设方面允许社会成员充分自治和自组织,视社会组织为政府组织的必要救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赋予社会充分的创造自由。唯其如此,今世纪朴素无华的“五有之乡”的理想才不至于沦为“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