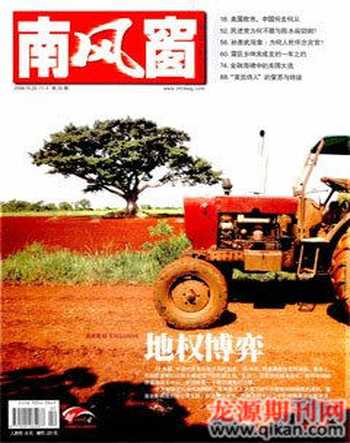土地集中的湖南样本
2008-05-30郭凯
郭 凯
在中央政府土地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原则,预留空间内,地方结合实际自我创新、自我探索,现有矛盾有望得到更快、更平稳的化解。
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载录的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场景,到最近的湖南吉首民众集体抗议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化和非暴力化,其中历经的种种社会变迁,或多或少,大概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注释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既存说法——“如果中国湖南的农村问题搞不好,就不能妄言搞好了中国的农村问题。”
回望过去,变革、回转、再变革甚至再回转,对于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农村,都是十分熟悉的字眼。而30年的改革进程,且不论主管愿望如何,客观结果上,正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并且由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身份等级秩序的30年。
面对这种现实,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希望扭转局面、反哺农村的政策探索多年前已经开始。然而,以中国之大,中国各地农村局势之多元,都对政策之手提出了高于传统中央集权式政府所习惯的套路要求。
而对于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据记者的了解,相当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全会对今后农村政策给出的最珍贵的指导思路,在于它给各地留下了在中央大政方针之下的自主创新空间。
土地与土地上的人
湖南益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业依然为这个地级市的多数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
随着近年来依照中央政府政策推进土地承包权自由流转、农业产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益阳市逐渐涌现了各个数量级的农业大户。然而,在既有的控制粮食价格以及各种相关经济和政策条件下j即便是集中种植、规模经营,粮食种植仍然只是一个“饱肚子的活计”。
刘进良是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利兴村的农民。他参过军,当过村干部。2004年,乡里基本完成完善第二轮土地延包、给农民承包地发放确权证后,他开始了大规模转包土地、集中粮食种植的尝试。
刘进良说,他主要集中的是需要土地开发投入、转包成本较低的低产出田,因为这样农民愿意长期转包给他。历经数年,他投入了200多万元资金,第一年贷款加个人借钱100多万全部投进去,第二年的收入平衡投入,不计刘个人薪酬,大约有5万结余,那时他已经转包了1000亩土地。2007年,以将近3000亩的集中经营规模,选种湖南农科院袁隆平教授研发的一种最优良种,全年也才有二三十万的收益,摊到每亩地,平均盈利几十块钱。

刘说,所有成本都在涨,尤其是化肥,但粮价怎么也上不去,今后再单纯扩大种植面积肯定不行了。他现在正和乡里协调,希望能够承包(并购)原来的乡粮站,把它改建成晒谷场和稻米加工厂,生产自有品牌的大米。
这个粮站在几年前改制时,已经承包给了别人。牌口乡乡长汤建翔说,乡里会尽全力帮忙,协调关系,尽快让刘拿到牌照,并希望刘将来建设的米加工企业能给乡里的百姓带来就业和致富机会。刘已经注册了一个“益阳市兴农粮食产销合作社”,刘是社长,并购原乡粮站时,他会以这个合作社为依托。他还准备好了注册商标——“进良米”和“兴百姓米”。
刘说,如果不是这几年的连续投入和乡县市的帮扶,他未必能够坚持下来。他的感觉更像是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当他发现继续扩大种粮仍然赚不了钱,就只能往产业加工的路子上走。他也遇到返乡农民或者又想自己种地的农民要田的情况,但整块田不可能再分出去,他往往就是给农民加地租(转包费)了事,大概这一支出每年在几万元左右。
有村干部和村民说,刘已经是个超级大户,种粮还赚不到钱,其他种小块田的种粮村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农民不愿意种粮,但在外面打工缺乏保障,而且也留不下多少钱,所以大家还很看重自己的承包地。
益阳市市委办副主任王锡良说,作为地方基层政府,他们感受到中央要稳定粮价的政策取向,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做“大农业”、发展农业加工业、做强产业链上寻找致富机会。“用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也许会是我们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道路。”
像目前已经颇具规模的全国十大米市之一的益阳兰溪米市(兰溪大米加工市场),日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消化粮食130万吨,年创产值21.8亿元,年创收入近2亿元。因该市场的存在,地区全年转移富余农业劳动力2000多人,为周围的村民提供年就业收入3000多万元。此外,为该市场提供运输服务的车辆总计年收入大约为4500万元。
然而,农业种植业是高风险产业,与之相关联的农产品加工业也同样面临各种风险,由此致富之路,行之不易。位于兰溪米市的湖南佳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达明说,不少没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以为米商赚了大头,事实上不是。虽然说谷子涨价有限,但还是涨了-一点,但米商还要面对其他更多的成本上涨,但大米价格是受到控制的,近来的收入不但上涨乏力,考虑各种成本的上涨势头,还可能有下滑的趋势。
位于益阳的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李副总经理说,农产品加工业很多和食品有关,由于食品与健康的关系,对行业企业的要求很高。李说,虽然中国很多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企业都是规范企业,但经过三鹿奶粉事件的冲击,对整个中国食品加工制造业和自有品牌都是打击。辣妹子在数年前花了不少钱,申办了一个“QS”(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标志,现在一下子被取消了,大概不取消也没意义了,“我们会想办法寻求其他的认证”。
然而,就这样一个食品加工厂,每年因向农民收购辣椒而惠及3000家农户,还有柑橘罐头等各种辣妹子产品加起来,每年有5000多家农户得以依托这一农产品加工企业而增收。
一县与一国
如果说农业就地产业化意味着农村就地城市化,那么与农民流动到城市、在城市实现城市化两个加在一起,是否就能结合共举、实现城乡统筹呢?湖南长沙市郊区的长沙县,它的统筹经历,似乎已经告白了一个国家有可能实现的城乡统筹机会。
长沙县的地理分布以及县内的不平衡发展情况,让它几乎成为了一个缩小版的“小中国”。长沙县一部分区域紧贴长沙市,受长沙城市经济和城市化扩张的辐射,经济和社会福利水平发展很快,在这些地方,几乎难以体察市县之分。但是长沙县还有广大的偏远区域和相对落后地区,农民生活和福利水平严重不足。如何让已经发展的地区继续发展、让仍然落后的偏远地区分享县里的发展果实、实现全县内相对均衡的福利,就是摆在长沙县政府面前的大问题。
长沙县副县长常利民说,改革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资金、人才和技术等优势资源不断集中城市、城市不断从农村抽血的局面。现在,需要从各个层面综合改革来扭转这种状况。
对于农业产业化,在长沙县重点推进
了现代农庄和农业投资博览会的发展。而对于耕地和地权这一农村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处理,长沙县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自发的实践,则对很多农村工作者和农村问题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
长沙县农办主任周锦程说,在完善第二轮延包时,虽然中央政策规定了确认土地权证时不能调田,但是地方上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村子多年来基本上没调,有的村子则作了调整。于是,在完善二轮延包时,既遵守中央规定的不许村集体(小组)留下任何机动田(公田)的政策,又根据现在的农村家庭人口变化还有未来15年可能出现的人口变化,长沙县的各处乡村事实上分配机动土地(公田)时,都是按照15年后的预计家庭人口数分的。
所以,现在以及未来15年,长沙县由于土地承包无限顺延与人口变化导致的农村人地不均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不会出现。而且在紧邻长沙市城市化扩张的地区和县内农村基建加快的地区,随着土地价值上升,这直接关系到农民征地之后的补偿公平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避免了将来会出现的补偿分配难题,这是社保等配套制度所无法替代的。
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现代化农庄和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长沙县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开始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准备尝试以地权入股现代大农庄的耕地土地股份制,以求获得更好的收益和更现代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由于工业的发展,现在长沙县一个县的经济产值,在湖南省甚至是几个市的产值的总和。但是面对县内很多仍然落后的地区,统筹协调发展的道路仍然挑战很多。长沙县县长杨懿文说,县政府考虑过很多平衡县内福利的问题,发现了很多困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落后地区的教育条件问题,很多好的老师不愿意去,因为条件差距大,但是不是可以给他们高工资、甚至双倍工资,再给一些更好的发展机会呢,比如学习中央援疆、援藏的政策。
杨说,为了长期保有良好的环境,长沙县有计划对每一个农村提供垃圾清理和废品回收公共服务,但是担心周边县市的农村废品都卖到长沙县来,长期支撑不起。所以这要求县政府人员的智慧,怎么样把价格定在让本县农民愿意把废品垃圾卖到收购点、但是对于其他县的农民,则交通成本都偿付不起,大概就可以解决问题。杨说现在他们还在研究。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长,长沙县先行一步,计划在县内探索建立城乡统筹社保、医保基金和个人账户。常利民副县长说,他们算过两笔账,一是如果要给县内60岁以上的老人买足15年基本养老保险,需要1.2亿元财政开支,二是如果从现在开始给县内农民建立养老保险账户,15年大概需要15亿元的财政投入。具体怎么操作,长沙县还需要详细认证和规划。杨说,只要中央不把政策框住,长沙县的发展有望能够从事这样的试验。
而对于目前各界都有很大意见的农民工社保转移问题,杨说,如有政策自由度的话,在长沙县给县内农民建立统一社保账户之前,长沙县可以在县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农民工社保转移托管账户,让农民工把自己的养命钱有渠道转回来,而不是被迫退保或者不参保。
呼吸空间与政策框界
对于化解三农问题,农村就地城市化和农民到城市实现城市化,都遭遇着重大的政策瓶颈。

一方面,在农村就地城市化道路上,是保护耕地与农村城市化发展需要大量工业用地的矛盾。如果农业产业化、更多资本进入农村,带动工业化,没有土地的供给是难以实现的。目前,在东部地区、先发展地区已经逐步实现工业化,农民摆脱农地种植的束缚之后,中央政府以保护耕地为宗旨,对工业用地实行总量控制,指标层层落实到地方。那么对于需要就地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后发农业地区,这一政策就变成以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大约束。
长沙市望城县格塘乡是较早实行农民工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地方,受惠于专业劳动力的供给,引来了不少的外来投资。但用地问题却一直是个大难题。最近一家珠海的公司想在格塘乡投资开发观光休闲农庄,涉地千亩,但是作为传统农业区,根本没有用地指标。乡长吕凯兴说,如果今年没有指标,项目就要拖一年,县里如果能给调剂到用地指标,办手续下来也需要半年。
但是望城县和长沙市的政府人员告诉记者,不是各级政府不愿意给乡里指标,实在是整体指标都不够用,他们只能“排排队”。
而这一问题,在湖南益阳,甚至在记者之前调查过的江苏省的许多地区,也是一样的。这就对中央政府政策提出了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要保稳定、保粮食生产,某些农业地区必须剔除在工业化之外、或者不能进行就地城市化的话,中央财政是否能够承诺对这些后发受限地区提供与先工业化地区同样的公共福利呢?
另一方面,在未来更大规模的农民土地流转后进城的道路上,户口制度尤其是户口与公共福利相挂钩的制度,依然是最大障碍。
但是,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据长沙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肖柏平介绍,长沙市政府正在计划新一轮户口改革,有可能推行有固定工作、参加社保3年的外地人即可转为长沙户口的政策。
而这种跨越“居住证”(取消暂住证之后,这是在很多发达地区实行的户口改革的过渡阶段身份证明)、3年到位“户口”的改革方式,对于长沙市未来的最大挑战,是目前户口政策中的“三投靠”政策,尤其是老人投靠,有可能将给城市财政保障和社会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在其他与户口相挂钩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对这项改革的未来普遍不持乐观态度。
事实上中国还有一种思路可以参考。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教授认为,对于纳税人国家,比如美国,纳税凭证是与福利挂钩的基本依据。在中国,目前已经从财政国家转向了税收国家,但是远远不是纳税人福利国家。以纳税人要获得福利的基本社会正义标准,结合人口流动的需要改革户口制度,不仅对农村人口流动,对整个国家的人口流动、福利对接和身份公平,都有渐进的可行性。
总体而言,从湖南的情况看,在中央政府土改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原则,预留的空间内,地方政府结合实际自我创新、自我探索,现有的矛盾的化解,有望更快、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