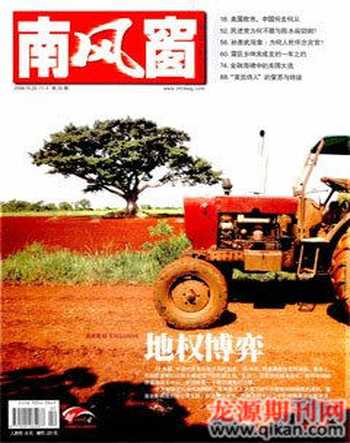南海“土改”14年波折
2008-05-30邢少文
邢少文
历经14年,由于各种原因,南海农村土地入股试验从原来的村集体股份制转变为村民小组股份制。但因为与现时法律、政策的抵触之处颇多,隐患已经开始显现。
一个牌坊、一座祠堂、一小块菜地,这是现时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办街边村北边村民小组作为“村庄”最后遗留的景象。这个户籍人口不足两百的小村庄,东临桂城工业大道,西临佛山机场,北临广茂铁路,前后左右包围着的,则是鳞次栉比的工厂厂房。
距北边村不过10公里的桂城街道办,便是南海区政府所在地,那里新楼盘林立,俨然一派CBD(中央商务区)景象。
10月12日,在已成楼群的村庄旁边,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给菜地浇水施肥,“给自己吃的,不卖。”老人说。
这是庞大的珠三角工业重镇中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村庄缩影。自从1994年南海全面推行被称之为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南海模式”之后,村庄和农民,便逐渐消失了。
明涧暗涌,历经14年,南海土改曾曲折迂回,至今也并未完全明朗化。
新时期的农民
在27岁的叶铭恩印象里,小时候上学,是踩着田埂去的。那个时候,每户家里要向上缴纳两担稻谷的公粮。但自打他上了初中之后,农田就消失了。
1994年,南海全面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即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集体财产及集体土地折成股份集中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组织,然后由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租,村里的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作为出资入股,凭股权每年享受分红,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
南海土改的背景,是珠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制造工厂”之后所面临的工业用地紧张问题,向农村要地,向农民要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围之举。
1995年3月,南海1574个农村股份合作组织成立,拉开了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大幕。
叶铭恩所在的北边村亦将全村70多亩的耕地归由原街边乡(后改街边村)经济联合社进行出租和发包,按照以年龄划分股份的方法,叶铭恩家一共4口人,共分得37股。
自此之后,北边村的村民就告别了种田的日子,仅留了10亩菜地种菜自供。土改之后,免交公粮。
北边村的土地出租价格从1994年的每亩2000元左右,到2002年涨到6000元/亩,由于村里的土地太少,村民每年分得的股红并不算丰厚,仅为几百块钱。但叶铭恩的父亲叶炳红告诉本刊记者,总比以前种田要好,以前村里每人5分地不到,“种的都不够吃”。
没了地之后,叶炳红用初期入股分红的钱买了一个小货车专门帮别人拉货,他妻子则在租用村里土地的一家电器设备厂的食堂打工。虽说生活并不算富裕,但也比以前好了许多。后来,村里又对预留的宅基地进行划分,叶一家在新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两层小楼。老房子他则粉饰一番租给附近工厂的外来打工者,这亦是一笔收入。

日转星移,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南海又被并入佛山市,皮革和灯饰成为罗村的支柱产业,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土地也在不断增值,2008年北边的土地出租价格,已升至1.5万元/亩。
2006年,村民小组从街边村要回了原由街边村经济联合社拥有的集体土地出租权,重新调整价格发包。北边村民的土地出租分红也从原来每人每年几百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每人一年接近2000元。
去年,叶铭恩用他家分得的股红买了一台电脑。技校毕业之后,他成了家里的打工一员,先后干过超市打单员,推销员等。2007年,他娶了一个湛江媳妇,经过艰苦的努力,将媳妇的户口转到了北边村民小组,进了村旁一家卫浴用具厂打工,另外还花了1000多块钱,购买了村民小组的8股股权,这样一来,媳妇也能够参与土地出租的分红。
对于叶炳红而言,虽说日子比过去好了许多,但由于今年以来,拉货的生意越来越淡,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闲着,有些落寞。今年经济萧条,工厂的效益也不好,有一些厂倒闭搬走,有些拖着租金迟迟未交。年底的分红看来并不很乐观。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一样有天灾人祸,没有什么是旱涝保收的。
在罗村,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一个人一年能分到1万多块钱。特别是今年年初,他听说邻近的芦塘村旁边村民小组因为把一块撂荒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每个人一次性分得了近30万元红利,他更觉得落差很大。“只怪我们村的土地太少了。”他闲坐在家门口,抱着一条大黄狗,有些愁眉不展地说。
股份公司的名存实亡
土地的多寡、位置的好坏,成了当地村民小组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指标,不是属于村民小组,而是属于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组织。
在街边村委会办公楼的门口,仍然挂着街边村经济联合社的牌子,吕耀波仍然挂着经济联合社社长的职务,但这仅仅是一个空壳,经济联合社已无人员。
联合村与街边村毗邻,与街边村相比,拥有5000多人、3000多亩土地的联合村村委会办公楼要气派得多,办公楼的顶上架着巨大的招牌:联合股份集团公司。
在1994年那一轮风生水起的改革中,在把土地股份制之后,各村都建立了股份合作组织,虽然土地的承包权转化为股权后仍然属于村民,但土地的经营权已被划入股份合作组织。这些股份合作组织大一点叫股份集团公司,小A的叫经济联合社。
实际上,这些股份合作组织与村委会是两块牌子,同一班人马,同一个办公楼。这也意味着,股份合作组织实际上是入股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这样的权属,导致后来发生了矛盾。
“股份集团公司早已名存实亡了。”10月14日,现任联合村村委会副主任吴均南对本刊记者说,“股份公司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大锅饭,利益均沾,股份公司集中对外出租土地,然后利益再大家分配,但村民小组对分红不满意。”吴均南解释,不满意的焦点在于,村民觉得分红太少了,而大部分的收入被提留为公益金和公积金。“村里要搞三通一平,要建医院、建学校、建幼儿园,要买医疗保险,要发老人金,要维修旧厂房,当然需要截留土地出租的利润。但这样一来村民手里拿不到现钱,就不高兴了。”
同属罗村辖下的芦塘股份集团公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由于芦塘村在划分股份的时候是以土地推平后再以平均每人1股的方式进行股权化分配,而在出租的时候,有些地方租金高,有些地方租金低,有些是作为商业用地出租,有些是作为工业用地出租,结果在分红的时候,位处租金高地段的村民便为拿到的股红与位处租金低地段村民的股红相等而忿忿不平。“大家对出租价格的意见也不统一,利益没有办法平衡,麻烦的事情一大堆。”现任芦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均帮对记者说。
在此之外,吴均南和张均帮没有挑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一些腐败现象
的出现,村民不信任股份公司,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理事、监事基本由村委会干部兼任,村民认为土地出租的财务不够公开,监督不到位,村民没有话语权,土地在升值,而出租价格却低廉,公益金和公积金的提取与村民感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
联合村后来发生的一起腐败案件最终导致了股份集团公司的解散,一个村委主任将土地违规卖给开发商后,卷款逃到了国外。为此,村民们拉着横幅在桂城工业大道上游行示威。
“上级要来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把财务报表在公告栏里张贴一下,平时见不到。”一位村民说。
类似的矛盾并非联合村独有,甚至有一些村民小组和村民提出来分田退股。当村民们对股份公司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之后,冲突此起彼伏,股份公司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2000年之后,在村民的要求之下,村一级的股份公司将原先人股的集体土地退回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向外出租,仍然保留股份制。
在现时由村民小组负责出租的运作过程中,成立了村民理财民主小组、财务监督小组以及引进第三方审计单位,每个月公布一次账务。在北边村,这样的监督工作看起来似乎简单一些,村民小组有一位村长,两位副村长,而村民们对这三位村长的信任更多的来自于其族群关系,叶炳红的大哥就是副村长,“村里人口少,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有什么事一说就知道了”。
土地重新发回村民小组之后,原先的股份集团公司的干部不无失落感。“原来出租前的三通一平费用、办土地证的费用都由股份集团公司垫资,把土地退回给村民小组,这些钱都拿不回来了。”张均帮说。而这部分费用,实际已变成股份公司的债务。但是,随着股份公司的解散,“所有的账本都没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就在各村纷纷解散股份公司之后,联合村则采取了另一种运作方式:村民小组仍将集体用地交由村委会去出租,只不过,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签订固定收益的合同,即无论最终的出租收益如何,每年村委会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村民小组。
“村民小组是旱涝保收,村委会如果收益不好,就是贷款也要把分红的钱给到村民小组。”吴均南说。当然,实际上事不至此,“最多是租金少的时候把公益金和公积金等公共开支压缩一下。”
吴认为,由村民小组自己出租不但因为三通一平等配套措施不齐全而导致租金低,而且厂房乱盖,不利于整体统一规划。
更有利的是,村委会可以通过地租的级差收益获得公共资金,比如与村民小组签订的租金为1万元/亩,而村委会出租的时候则可以将租金提高到1.5万元/亩,中间差价5000元作为村委会的公共资金。同时,村委会还可以收取工厂管理费。此外,村委会还收回了30%的土地作为村集体机动用地,这部分土地的租金也作为村公共基金。
吕耀波则对联合村的做法羡慕不已,因为整个罗村街道办,只有联合村这么做。村委会少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处置权,“现在搞‘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改造阻碍重重,搞不动。”他对记者说。
而张均帮则表示,当初将土地重新发回给村民小组的时候,芦塘村委并没有留机动地,现在只能根据上级要求靠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规划的方式,获取公共资金。模糊地带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南海摸索的这一套农村集体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模式对缓解工业用地紧张,推进城镇化进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宏观政策迟迟没有出台,这一模式与现时政策的抵触之处也颇多,这都为南海的土改未来走向添加了一份不明朗的色彩。
在整个南海区所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改革之中,模式虽然都类似,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在改革之初,名义上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但实际上,在这些使用权流转的土地中,不仅仅是山岗地、撂荒地,还有大量的土地属于农用耕地。以北边村和联合村为例,便是100%的属于农耕地。
而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要用于非农建设,都必须先征为国有。而在有关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之中,农用地的使用权流转更是被严格禁止转为非农用地。
“我们这种做法其实严格起来也不能叫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流转是指承租方可以利用土地进行抵押贷款,但我们村的地现在都没有办理土地证。”吴均南说,联合村的耕地性质,更是敏感之处。“没有人去管这个,反正耕地、山岗地、荒地,混在一块弄。”张均帮则说。
这也为南海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埋下了隐患,而且,这种隐患已经开始显现。2001年,南海市共同集团有限公司孔村北社公司曾诉南海市共同五金塑料厂违约,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双方当初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给付1998年到2001年租金276012元,同时终止合同,收回土地。但被告反称,原告将其集体所有的土地租给自己建厂房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土地法》第63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明确规定,集体土地不能出租、转让或出让。最终判决结果为原告与被告于1994年6月3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原告返还被告以前收的租金。
根据南海相关方面的统计,类似案件正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由于大量的土地都没有办理农转非的手续,一旦依照现行法律,受损的极有可能是农民。
2005年,广东省曾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该《办法》草案提出,农民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将以国有土地同样的身份——同地、同价、同权,进入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份对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入市具有实操性的文件。
据悉,广东省有关部门也在探索和研究给农民发土地产权使用证的试点,有了产权使用证,便可以进行土地确权,然后依法在产权期限内进行土地流转。但这一试点目前仅在个别地区展开,而且,对于已经城镇化的珠三角地区,农用耕地的非农流转,更是一个没有触及的问题。
与此同时,虽然集体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从原来的村集体股份制转变为村民小组股份制,但土地出租收益的分配合理性仍是一大问题。根据南海区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区农村经济总收入比最早开始试点改革时的1992年增长了26.7倍,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增长4.17倍,股红分配额也仅增长9.91倍。
如何遏制村委会级差收益和开支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性?将集体用地重新发回村民小组后,虽然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但道德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人口和土地众多的村小组更为复杂,财务运作的监督机制如何来改进和加强?
这或许已经不是土地制度的改变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