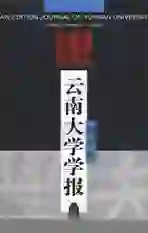德雷德·斯科特案及其背景述论
2008-04-21张锡盛
张锡盛
摘要: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关于宪政和种族平等的众多案件之一,从初审到终审历时10年有余,对美国内战产生了诱导性的作用;它以“1850年妥协案”,1854年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和1856年的大选为背景,且共同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当时美国多数人统治的一些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多元社会中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相互关系的某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德雷德·斯科特,案件,背景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识码:A
一
当托克维尔于1830年代对美国进行考察并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时,他对美国的民主与多数人的统治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下面的这段引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人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的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告发的事情如何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托克维尔在注释中,引证了1812年美英战争中发生在巴尔的摩的暴民案说明多数人是如何抗拒行政执法官,无视少数人言论自由、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对持异议者和监狱设施进行破坏以实现多数人专治目的的过程。
然而,关于少数与多数的划分有时是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的。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少数与多数是随着情势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转变而相互转化的。
就在托克维尔发表该书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令人震惊的,体现少数人与多数人相互关系最为淋漓尽致的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法庭拉开了序幕。这一案件是在英美宣布禁止国际奴隶贸易,并在废奴运动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奴隶主义者由羞羞答答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转而公开赞扬并为扩张奴隶制鸣锣开道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内外多数与少数在观点上的划分泾渭分明,而在人数和力量对比上又扑朔迷离的案件。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政治家和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他们的决策对于少数与多数的转化,对于政治力量的对比都将是举足轻重的,而对历史的进程也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仔细考察历史转折的关头这一案件的过程及其相关背景,政治家和法官们处理此案的方式,对于理解托克维尔所揭示的当时美国社会状况,少数与多数的关系、法律效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对比的转化应该是有益的。
二
德雷德·斯科特案自始至终经历了州和联邦的四级法院,历时约十年的漫长过程,可谓旷日持久,惊心动魄,其当事人的律师和审理此案的法官中有数位在这一过程中逝世而未能见证这一案件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然而他们所留下的司法印记,即使在今天也是意味深长的。他们的思想观点和与之相关的情感,均凝结于当时处理此案的美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践当中,至今仍为人们所关注。原告德雷德·斯科特则在诉讼期间被当作此案初审被告的财产在上诉审期间转移到的另一名诉讼当事人的名下;因此,此案与德雷德·斯科特对垒的另一方当事人也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初审为德雷德·斯科特诉爱仑·爱默生(Irene Emerson)。
黑人德雷德·斯科特的双亲居住于福吉尼亚(Virginia),均为奴隶。他大约生于19世纪之交。据法庭的证词,他是被其主人彼特·泰勒(Peter Taylor)作为奴隶出卖给军医约翰·爱默森(Dr.John Emer-son)的。这个军医于1833年11月19日携带他到自由州伊利诺斯州报到,他在那里的差事持续了近三年。在此期间德雷德·斯科特被赋予了自由,因为依1787年《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 of 1787),除被作为犯罪惩罚之外,在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大湖区(Great Lakes)之间的地区禁止奴隶制。而且,伊利诺斯州就是根据1787年《西北法令》的部分内容建立的,该州的宪法亦禁止奴隶制。然而在此期间,德雷德·斯科特未主张他依法获得的自由。其后他一家随约翰·爱默森回到了密苏里州。
依密苏里的法律规定,任何被不正当奴役的奴隶均可为其获得自由而提出诉讼,包括黑人和白人。密苏里州处理自由诉讼的司法实践还表明,此类诉讼奉行“一旦自由,永远自由”的司法准则,并且长期被坚持下来。鉴于这些有利的条件,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和他的妻子哈丽特·斯科特(HerrietScott)于1846年4月6日,分别向圣路易斯巡回法庭(st.Louis Circuit Court,密苏里州的法院)起诉爱仑·爱默生(Irene Emerson)以摆脱他们的奴隶身份而获得自由。自此,开始了此案的初审。由于初审期间发生了法庭所在地火灾和霍乱疫情,以及法官选举等情况,此案的初审耗时经年,直至1850年1月12日,才由法官亚里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持了这次审判,并裁决原告胜诉。
被告爱仑·爱默生(Irene Emerson)的律师立即将此案上诉到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法庭于1850年2月12日与当事各方商定只有德雷德·斯科特诉爱仑·爱默生(Irene Emerson)一案可以得以继续审理,其审理结果也适用于初审时哈丽特·斯科特(HerrietScott)一案。由于过多的案件积压,此案未能在1850年的三月审理,而是拖延到了1850年的lO月才开庭。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是威廉姆·那普顿(Wil—liam Napton),詹姆斯·H·伯吉(James H,Birch),和约翰·F·李兰德(John F.Ryland)。此三个法官在1850年10月开庭期审理了此案,但未宣布他们的审理意见,而是延迟到1851年8月密苏里州选举法官之后。而在这次选举之中,威廉姆·那普顿(Wil—liam Napton)和詹姆斯·H·伯吉(James H.Birch)未能当选。因此,这个案子又组成了一个新法庭。除原来的约翰·F·李兰德(John F.Ryland)法官外,新当选的汉米尔顿·格博(Hamilton Gamble)和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代替了落选的两人。新法庭于1851年10月在圣路易斯开庭,但中止于1851年12月24日,而后于1852年3月15日,重新开庭。法庭以2:1作出决定,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决定。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撰写了由约翰·F·李兰德
(John F.Ryland)附议的法庭意见,汉米尔顿·格博(Hamilton Gamble)对此持有异议。
1853年11月2日德雷德·斯科特的朋友帮助他将此案上诉到密苏里地区的美国巡回法院。此为该案的第三审。在此期间,作为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发生了变化。前述被告爱仑·爱默生(Irene Emerson)的弟弟桑弗德(John Sandford)宣称他对德雷德·斯科特一家拥有所有权。因此,在这一审级的官司中,桑弗德代替爱仑·爱默生成为与德雷德·斯科特对垒的一方当事人。法官罗伯特·w威尔士(Robertw.Wells)主审了案件。1854年5月,该法院宣判:支持桑弗德(Sandford),维持德雷德·斯科特及其家庭的奴隶地位。1854年12月,德雷德·斯科特的律师菲尔德(Field)将此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直到1956年2月最高法院才审理案件。1956年5月法官们决定于该年12月再行辩论此案。1957年3月6日,法院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在最高法院,对垒双方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德雷德·斯科特的律师蒙格墨利·布莱尔(Montgomery Blair)认为,基于居住于一个自由州或者領地而获得的自由,是永久性的,回到一个蓄奴州奴役不应该再行施予。这是密苏里州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原则,直到州最高法院于1852年引入了当下的多数意见的政治观点,才改变了这一情况。他还宣称,一个非洲血统的黑人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他和另外一个律师罗斯威尔·M·菲尔德(Roswell M.Field)希望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密苏里长期以来的法律先例,以及关于奴隶自由和公民身份的法律。桑弗德的律师拉吾迪·琼森(Reverdy John—son)和亨利·S·盖伊(Henry s.Geyer)则挑战国会1820年所制定的密苏里妥协的权威性;并因此否定德雷德·斯科特的自由权利。他们不曾提出德雷德·斯科特因在自由领地内居住而获得的自由是否得而复失,但却首先质疑他是否曾经拥有自由,因为他们的法律解释不承认1787年西北法令和1820年密苏里妥协的约束力。
在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中,以7:2的多数支持桑弗德及其律师的观点。
在谈尼(有的译为唐尼)法官所代表的法院多数看来,黑人不属于美国的人民或公民:“法院认为,无论是立法和历史的记载,还是《独立宣言》中的文字,都表明被运往美国的黑奴和他们的后代,无论他们是否得到自由,都不能被视为那些州的公民的一部分,宪法这个伟大的文献也没有意图将他们纳入‘公民这个词的含义之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认为是低等的种族无论在社会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中都不能与白人相提并论。他们的低劣,使得他们不享有任何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黑人生活在奴隶制中是公平的,也是合法的。只要能产生利益,他就会被当作贸易和运输中的一件普通商品买卖。这是在当时白人的文明世界盛行的持久的观点。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这都被认为是一个‘公理,没有人会辩驳,也没有人想去辩驳。所有等级和立场的人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都习惯地遵守着它,无论是出于私利还是公共利益。他们从未怀疑这个意见的正确性。”虽然谈尼法官所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内的同事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即“根据合众国宪法,每一个出生在一州并根据其宪法或法律的效力而成为其公民的自由人,也是合众国的公民”,但因其只是少数而未能成为法院的生效意见。
德雷德·斯科特一案被认为是继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又一个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此案所进行的司法解释,宣布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是违宪的;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是奴隶、下等人,因而他们是其主人的财产。
三
历经十年有余的德雷德·斯科特诉讼案,以赞成并支持和反对奴隶制为分水岭,将法院和社会分成两大阵营,而两个阵营当中多数与少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法院内的法官及律师的数量是确定的,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上的民众的数量确是难以料定的。如果将支持和反对奴隶制作为分水岭,则在此案的整个诉讼期间所表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况,很难说哪一方占多数,或哪一方的力量更为强大。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此案三级上诉审中,支持奴隶制的法官占多数的情况,并且试图通过此案否定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而将奴隶制推向整个美国。其理由则是此时非彼时,情移势易,1787年制定“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eeof 1787),以及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所审判过的许多有利于:逐步消除奴隶制的先例不再具有拘束力。
实际上,此案发生之时,奴隶制是既成事实,只不过,以此案为分水岭,此前的立法和密苏里州的司法实践,是通过与它们相关的过程逐步地限制和缩小奴隶制的范围。而当此案发生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并未将此案当成事关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大问题来考量,而是将德雷德·斯科特及其家人的自由作为诉讼的目的。当诉讼进入到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之后,这一讼案不再仅仅是原告个人的事务,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些重大的价值取向:奴隶制是否合理,是逐步地限制它,还是使之向全国扩张,黑人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是否应该享有公民权,是维持议会中多数制定的既有法律,还是由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经由司法审查的程序来挑战作为多数的国会的立法,宣布其违宪而加以废除。
如果将1787西北法令和1820年密苏里妥协作为国会的立法,则它们可被看作是经由立法者代表社会上民众的多数,表达了将奴隶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通过一些特定的程序逐步地缩小这一范围。而自1803年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v,Madison)一案所建立的司法审查制度,使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行使司法权以对国会的多数立法进行制约和平衡为社会所接受。因此,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及其所行使的职权,相对于国会和总统代表的行政分支而言,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权力上均处于“少数”和弱势的地位。当他们的意见与国会的立法或者与行政分支的意见相悖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处于名符其实的“少数”。
由于最高法院内部也采取多数决定的方式,因此在其法官当中,也根据其在所审理的案件的意见和态度分成多数和少数。他们针对案件审理所体现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在哲学上的态度可能导致他们对案件一作出意见分歧或者观点截然相反的裁决。在斯科特一案中,上述国会的立法,美国的社会情势,以及原告被告的权利主张,9名法官以7:2的多数通过了对斯科特不利的司法判决,并宣布国会有关限制奴隶制的立法违宪。法院的这一多数裁决被认为是继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司法审查判例。
最高法院内法官多数与少数的分野,似乎也在民
众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首先是斯科特及其一家,他们是黑人,而黑人在当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人口数量上相对于白人也是少数。在白人当中,根据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似乎可以说,反对奴隶制度的人数要比赞成奴隶制的人数多,因为经由国会中多数通过的1787年北方法令和1820年密苏里妥协的精神是逐步限制奴隶制。而当时只有白人才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代表选举权人行使立法权而制定的法律反映白人当中的多数人意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问题是:最高法院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为什么要在斯科特一案中与国会中的多数和白人民众中的多数“作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1820年制定密苏里妥协案时的多数,到了斯科特一案时(1846年4月6日-1957年3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最后的决定),是否还是多数?即彼时之多数是否此时的多数?
实际上,当此案正在进行时,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告诉世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多数与少数的对比在国家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中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会在此期间的立法活动和总统的选举过程之中。
其一是国会于1850年9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总称为《1850年妥协案》,其中包括《逃亡奴隶法》。其背景是南部奴隶主企图将奴隶制扩大到美国通过战争从墨西哥得到的土地上,以及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然而这种意图受到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民众的激烈反对。对此,南方奴隶主以退出联邦相威胁。为了调停双方的争执,国会于1850年根据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和达尼尔·韦伯斯特的建议,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总称为《1850年妥协案》。这一妥协案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在上述两个地区,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而新墨西哥的奴隶制的存废,依据“居民主权原则”解决,即由当地居民投票表决;其二,禁止哥伦比亚特区实行国内奴隶贸易,但特区内的奴隶制却不能触动;其三,规定全国所有的法院执行官都有责任捕捉逃亡奴隶,并且在必要时可以动员地方部队及一切力量协助。《1850年妥协案》的通过,虽然起因于妥协的意图,但其内容中明显的偏向南方奴隶主利益的规定,则表明赞成法案的国会议员成为国会内的多数。换言之,制定《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时国会中原来支持抑制奴隶制的多数,到1850年时,已经变为少数;反之,支持奴隶制扩张的少数此时则变成了多数。
其二是国会于1854年上半年通过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地区均处于《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根据密苏里妥协案,应该禁止奴隶制。然而,《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作废,并规定该领地上及领地形成的新州内的一切有关奴隶制的问题,应留给住在那里的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解决,即上述1850年妥协案的“居民主权原则”。如果说,1850年妥协案对密苏里妥协还留有尊重的话,那么到《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则由国会本身废除了它原先制定的抑制奴隶制扩张的立法,而代之以后果不甚确定的“居民主权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因当时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而造成了堪萨斯选举的混乱和随之而来的1856年5月至11月的堪萨斯内战。
其三是1856年即当斯科特案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期间的大选。这次大选的争战主要在赞成奴隶制的民主党和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之间展开。前者的候选人布坎南在大选中共得票一百八十三万张;而后者候选人约翰·弗里蒙特(废奴派)共得票一百三十四万张,选举的情况说明,选民当中以对奴隶制的态度看,赞成者的数量超过了反对者的数量。支持奴隶制的布坎南当选为总统。
上述的三件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审理期间,构成了映衬该案的一幅纷繁复杂的背景。
四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德雷德·斯科特案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由地方基层法院受理,继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件。法院外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法官们裁判案件的态度。然而,从判决的结果与上述背景所体现的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强势力量看,说法院的司法解释顺从了该历史时段上多数人及其代表机关的意志似乎是成立的。所不同的是,这一判决比国会于1854年上半年通过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走的更远。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界限,一八五四年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一八五七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壁障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从这些情况看,最高法、院内的多数派法官,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比当时国会内的那些多数派更为倾向于废除对奴隶制的限制。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一案件的审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显得特别地“另类”。通常认为,“在程序所规定的界限和对符合宪法的立法设想加以尊重的范围之内,最高法院就成了我们进行‘冷静的再思考的场所,成了美国社会内个人与弱小群体的天然论坛——这正是人权法案之父麦迪逊强烈地希望它能永远保持不变的地方。比之于更易受压力、更冲动、更易动感情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来说,最高法院更具备保护少数者权利的资格。”。这是由于其法官是终身任职,一旦获得任命就不受选民和委任他们的行政权力和议会权力的干扰,因此他们要更为超脱而更显独立,更能平衡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为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法治提供更为理性,更能洞察历史趋势和把握社会发展脉络,引导民众选择正确的治国方略,也更能提供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政治智慧。然而,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审理和判决却与这些分析相反,成为顺从“暂时多数”的一个反面典型,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
虽然如此,当时的美国仍不失为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同利益的诉求,包括黑人在内的利益诉求依然能够得到倾听,如德雷德·斯科特及其家人为获得自由的诉讼,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从初审到终审,不断有律师、法官和许多民众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捐资出力,使这一案件从开始时的个人诉讼最终成为事关种族平等和个人自由这样一些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宪法之诉。原告虽未赢得诉讼,但代表少数和弱势的德雷德·斯科特一家的律师和法官们的行为,却在改变着当时和未来的少数和多数的状况,从而使当时处于多数的奴隶制扩张者只是一种“暂时的强势力量”,对处于少数地位的限制扩张者和废奴者不致失去胜利的希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開头引用的托克维尔关于多数人统治的描述,似乎过于悲观。因为,虽然在民主社会中由多数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只要允许多元利益的存在,只要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得到容忍和保障,则少数和多数之分就始终是一种暂时的和可能被改变的状况。这是个人和少数人在民主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他们遵纪守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多数人(强者)应该保持警惕,使自己不致失去自我约束的社会运作机制得以建立的基础所在。
责任编辑姜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