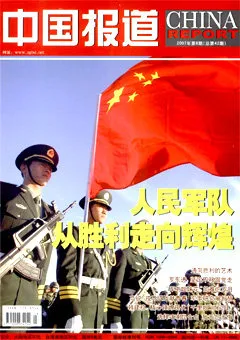“军中姐妹花”的难忘岁月
2007-12-29游艳玲李强
中国报道 2007年8期
她,范景新,开国上将王平的妻子,17岁参加革命,现年88岁;
她,范景明,开国中将王宗槐的妻子,15岁参加革命,现年86岁;
她和她,是姐妹、是战友,又同是开国将军的妻子。
战争年代,她们互相帮扶、并肩作战;和平年代,他们共享阳光、不忘进取。
和我们采访的其他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一样,在范氏姐妹家的像册里,各个时期头戴军帽、身着军服的军人唱着主角。看着像册,老人也因自己的“军人之家”的身份而自豪——两位老人的丈夫分别是开国上将王平和中将王宗槐,他们自己也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子女也全都入伍参军,其中景新老人的儿子范小光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因为景新老人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于是我们和景明老人一起来到姐姐景新家中进行采访。
刚进门厅,就看到景新老人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并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可坐下后,我们都发现景新老人的座儿比我们坐的沙发要高出一大截。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她已经很少坐起了,特殊的椅子,是为了减轻身体的疼痛。但是,妹妹景明还是故意抗议说,姐姐的座儿怎么比我们的都要高呢?这样不平等嘛!逗得我们大笑。我们的采访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一起参加革命
范氏姐妹出生于河北阜平县。1937年,姐妹俩还在阜平师范就读。因为抗战的爆发,学校停课,他俩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县城中参加当地的抗联宣传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老人说,他们一家姐弟三人,都是在那年先后入伍的,年龄最大的姐姐范景新那时17岁,范景明15岁,而最小的弟弟范景阳才13岁。他们那时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武装、动员参军。
由于姐姐范景明接受的文化教育略多些,很快被调到专区工作;妹妹景明聪明好学,很快成为当地人武会(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笔杆子。
对于参加革命的初衷,老人回答得特干脆:“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我们来说,横竖是个死,不如拿起武器参加革命。”老人说,那时候的革命青年没有什么苦恼,虽然每天和日本人周旋,天天跑、天天打,但是大家整天都是快快乐乐的,笑声不断、歌声不断,就是那种革命乐观主义。就这样过了几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讲述共同的经历
革命工作充满欢歌笑语,但是反“扫荡”的险情也时有发生。在姐妹俩的共同记忆中,就有这么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1年9月,在专区工作的姐姐来到妹妹工作的分区河北完县(现在的顺平县)传达上级精神、指导工作。由于那天正值农历八月十五,姐姐决定留下,和妹妹一起过完中秋团圆节,第二天再走。可是没想到,还未睡到拂晓,就从远处传来敌人的枪声。凭经验,大家知道,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开始了。包括姐妹俩在内的七八个女兵赶紧起身,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物件,招集附近村民一起向后山没人的地方转移。
因为大家知道,敌人的“扫荡”会持续3个多月,这段时k4YPNIHVY8MHQYtOyNYlwb515aVYB4jvGhrL770GUTM=间,敌人可能会在当地驻扎。所以,一旦转移,每个人都必须做好露宿山野的准备,所有个人物品都必须背在身上,包括粮食、衣被、洗漱用品、文件资料等和每人仅有的一颗手榴弹。
当时,姐姐景新生完孩子刚三个月,红肿的双腿完全支撑不住瘦弱的身体,可还要背上沉重的行囊,就决定扔掉随身的毛巾、口杯等物,以减轻负担。可是,这些生活必需品是转移中不可缺少的,于是,妹妹就将姐姐的东西抢过来背到自己身上继续跑。
从拂晓时分到中午,姐妹俩带着村民转移到附近的甲各庄时,已和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决定原地休息。这时,姐姐告诉大家,她身上带有重要文件,现在必须烧毁,不然这些文件落到敌人手上,就会给党组织造成极大危害。可是,这样做,无异于向敌人暴露他们的行踪。虽然这项决定遭到在场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但姐姐还是坚持让同伴们和乡亲们手背相连,身首合围了个圈以遮挡火光,自己把身上的文件拿出来全部烧掉了。
烧掉文件的她们如释重负,带着众人继续向后山转移。当来到八大岭时,有人说往山顶跑,有人说往山沟跑,可是姐姐景新决定跑到半山腰后蹲下,躲在深草丛里。当他们刚跑到山腰蹲下,后面紧追的敌人便跟了过来,有一队人马向下面的山沟跑去,还有一队往山顶上跑去,并时不时从山顶往下打枪,子弹从姐妹俩的头顶飞啸而过。就这样,机警的姐姐带着众人躲过了一场劫难。
妹妹的婚事
范氏姐妹感情深厚,从他们交谈时的默契和眼神交流中就可窥见一斑。同胞姐妹加亲密战友,姐姐景新给妹妹做媒,并成就了一对军中爱侣也是圈中佳话。这段故事,在《王宗槐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1941年冬,我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王平同志见我26岁了,尚未婚配,就对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爱人范景新有个妹妹,叫范景明,是个党员,19岁,人聪明,长得也好,原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医去了,你们抽空认识认识吧!”后来,学校放假,范景明来到她姐姐家,我们俩就见了面。她,中等个儿,举止端庄,面目俊俏,身段匀称,加上那两只水灵灵的人眼睛,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后经几次接触和交谈,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42年夏,我离开了三分区,调到四分区任副政委。白求恩医科学校也从唐县葛公村迁到了树沟大台村。两地隔山隔水,相距远了,见面很不容易,我们只有靠书信往来交流思想感情。
1944年2月,她从学校毕业了,婚事摆到眼前。巧遇邓华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西调,王平同志就托教二旅的同志让范景明一同西行。这天上午,当教二旅旅部进入河谷时,敌人的两辆铁甲车向正在渡河的部队拼命扫射。范景明刚走进河谷的泥沼地段,一粒子弹打飞了戴在头上的那顶肥大的帽子。她周围的几个战士倒下去了,鲜血洒在河滩上。凭着多次反“扫荡”的经验,她没有直接涉水过河,而是招呼护送她的那名警卫战士同她一块向右前方的小桥奔跑。从桥下过了河,到了对岸。
景明这次西行延安,历时3个多月,真可谓千里迢迢来完婚。尽管我们穷得叮当响,还是狠狠心,花钱在延安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这是我俩首次合影。
俗话说,患难夫妻情真挚。这一点不错。我和范景明结婚50余年了,虽然难免口角,但她没让我“背板凳”,我也没对她红过脸,一直和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