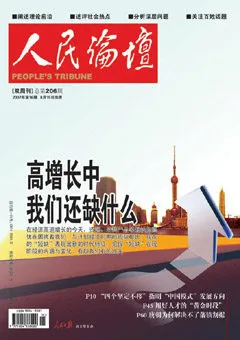警惕“人为制造”的短缺
2007-12-29叶檀
人民论坛 2007年16期
以往的短缺由商品供应不足而来,而目前我国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不足,既有历史的原因,有需求扩大、提升的原因,也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存在角色错位以及利益同盟的干扰所形成
面对日益攀升的房价,住房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回归运动,宗旨是市场的回归市场、保障的回归保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住房保障体制的缺失是正在急剧燃烧的中国房价的助燃剂。
所谓住房保障,即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满足低收入阶层基本住房保障需求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合在一起,构筑起全体国民的基本生存底线。这些公共产品能使他们的生活得以维系,也使他们的纳税价值得到体现。
住房保障的缺失缘于牢固的利益链条
我国的住房保障起自住房商品化之后,此前均由政府配给无产权只有使用权的住房。但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住房成为一种交换商品,由交易双方定价,房地产的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再分配能力显露无遗。
这就产生了如下几个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住房市场化在短期内使得我国的内需得到极大的提高,没有比以房地产拉动GDP更立竿见影的了。加快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与稳定人民币币值等叠加在一起,使中国经济不仅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疾风暴雨,还成为东亚经济的避风港,最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财富得到极大的提高,家庭储蓄从几百元上千元一下子增加了上万元的固定资产。由于城镇居民家庭60%左右通过房改房增加了财富改善了居住条件,负面效应并未显露。因此,当时的住房制度改革不仅没有遭到抵制,反而受到享受到房改房政策的城镇居民的欢迎。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是房改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这些人占据了城镇居民的大多数。当一项政策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并且拥有显而易见的短期好处时,得到拥戴十分正常。
住宅商品化的过程并没有与住宅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从一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商品化就欠缺了保障这条腿,显示出先天不足的一面。之后随着商品化过程的异化,这一隐形疾患终于显现。
中国住房商品化的异化起始于2003年,当年8月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18号文,彻底改变了1998年18号文在整个住房供应体系中使绝大多数居民住房应用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法,这一转变,加上近几年高达45%的城市化率新增的城市居民人口,加上每年从海外以及从大学毕业的上千万人,汇聚成一股购房洪流,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了世界最大的购买群体。
不仅于此,由世界最大的购买群体还刺激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容易的生财之路,那就是土地财政,在2007年以前一直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的这笔谁也搞不清楚确切数字却庞大无比的收入,成为城市基本建设、国企转型成本、政府财政收入等最为便捷的来源。个别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无论是出于追逐政绩还是追逐资产价格最大化等目标,都成为地价的哄抬者。无怪乎高房价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这样的怪论层出不穷。
1988年之前,我国土地交易以行政划拨为主;1991年之后开始出台土地出让的政策,到1995年的时候,转变为招标与协议出让两种形式;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签发11号令叫停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而代之招、拍、挂方式;这一次土地革命留下的协议出让的小口子在2004年8月31日被彻底堵死,所有的土地出让都必须以“招、拍、挂”的形式出让。
此后,频频传出天价地王的报道,近日长沙城北新河三角洲地块,被北京城开和北辰置业以92亿元的天价中标,成为“中国地王”。这一经济并不算发达的二线城市将此视为招商大事,政府北上南下,招徕各路开发商共襄盛举。该地块楼面成交价已与目前长沙平均房价持平,达到3500—3600元/平方米,预计项目成本价将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开发商,要使土地资产价格最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当地房价。
当然,获利的不只是某些地方政府,还有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据贷款额度60%到70%,利差高达3%以上,开发商土地竞标时压在银行手中的动辄几千万元的无息保证金,都使银行食髓知味,难以戒除房地产之大瘾;当然,捆绑在这根链条上的还有房地产开发商、中介机构,以及投资客。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以市场化的名义在垄断之下获取高额收益,虽然所获之利各不相同,互相时时发生冲撞,却又牢不可破。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是没有公共产品的立足之地的,虽然政府本应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却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既得利益者。
在“人为制造”的短缺经济的背后
在多数商品供过于求四处求售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面临着新型短缺经济,这一短缺既由现阶段中国的人地矛盾尖锐这一现实而来,也由某些层面的人为制造而成。实际上,不仅住房领域如此,在教育、医疗等领域无不如此,一方面强调市场化,另一方面却是资源的集中,人为制造供求紧张,导致消费者不得不以大价钱买到一般水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完全与公共产品的本义背道而驰。
可见,我国目前的住房市场短缺与以往的制造力不足所形成的商品短缺性质截然不同。以往的短缺由商品供应不足而来,而目前我国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不足,既有历史的原因,有需求扩大、提升的原因,也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存在角色错位以及利益同盟的干扰所形成。
中国房地产所面临的问题不容乐观,不仅商品住宅与保障型住宅极端失衡,甚至在商品住宅中,用于自住与投资的比例也严重失衡,在人民币升值、经济过热、投资品种匮乏的背景下,商品房已经成为少数能够买得起商品房的保值增值手段。当商品房的效用与艺术品投资、黄金投资等量齐观时,商品房价格的居高不下找到了另一种金融解读视野。
在主要是由人为制造的短缺经济背后,反应的是公共产品的缺失状态,已经造成越来越不容回避的社会矛盾:在土地一级市场,由于征地部门垄断性压价,形成被征地农民与基层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在终端消费市场,形成大多数自住型消费者与高房价之间的冲突;而在投资市场,由于政府为了稳定房价采取的各种行政手段与市场预期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一次次的冲突中,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政府信用的下降,公众的满意度下降,这对政府而言是无形的却又是最大的损失,因为民众将以房地产、教育等领域为标志,来判断政府行为的逻辑动机,使得政令与政策执行遭到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抵制。
负面影响还包括,由于在公共产品领域市场化边界不清,真正符合市场准则的商人无法生存,形成市场的逆淘汰机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对于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一再无法得到满足,同样形成逆反心理,对市场二字畏之如虎,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极端不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正因为无法区分市场与公共产品,而政府又屡屡承诺降价,或者将保障责任落实在限价房这样的非驴非马非市场非保障的产品上,普通民众只能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住房、教育等问题,一概视之为公共产品的缺失问题,从而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保障要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已经在纠偏,在预算中明确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严厉惩处在医疗、房地产等领域的腐败现象,以呼应民众对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强烈诉求。这固然令人欣慰,但比加大预算投入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必须从市场深度参与者的身份摆脱出来,回到通过合法征税提供公共产品的定位,这样才能从激励机制上改变目前政府的行为方式。
国民需要保障,正如渔民需要灯塔,如残疾人士需要扶持,政府的作用是从企业、个人收税之后建造灯塔,给予残障人士最低生活保障(作者系资深财经学者,《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