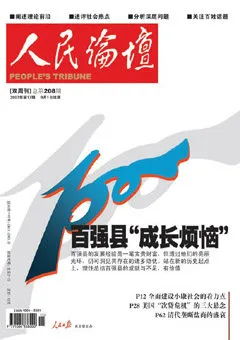“刑罚崇拜”思维值得警惕
2007-12-29张智新
人民论坛 2007年17期
近日,有两则领导干部挥霍国家资财的报道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率团公款出国旅游,结果因为邀请函系伪造而被芬兰遣返,最终受到严肃查处;二是今年以来,监察部牵头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案件,上半年共有4866名党政干部因此类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公款挥霍作为一种久已存在的腐败现象,当然不是新闻,不过这两则报道之所以引起舆论强烈反响,却缘于如何遏制公款挥霍的见解差异:就安徽省副检察长被查的消息,某报纸发表《公费旅游能否以贪污罪论处》的社论,随之该报又发表对著名刑法专家陈兴良以及一位知名律师的访谈,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公款旅游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结果这一消息很快招来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甚至围攻。
反驳者均认为公款挥霍之所以屡禁不止,就因为对这一腐败现象仅认定为违纪,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不是将其列入刑法罪名或者视同贪污等罪名,课之以严厉刑罚,因而没有对挥霍公款的腐败分子形成严厉的打击和强大的威慑。甚至有论者因情绪驱使,将两位专家定性为同腐败官员、行贿商人一起构成外电所谓“贪腐铁三角”的“无良学者”。
其实,媒体舆论一致炮轰两位专家的意见,乃在于双方所占据的立场角度迥异:陈兴良等纯粹从刑法学专业角度解释为何公款旅游等挥霍公款行为还不能以贪污罪论处,媒体评论则是站在社会学现象角度要求通过“入罪上刑”来遏制这一日趋蔓延的腐败顽疾;前者依据的是对犯罪构成的主客体、主客观方面等四大精确要件,后者依据的是腐败现象之间的粗略类比和定性。正因为双方的立论依据甚至议论焦点都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媒体对两位专家的炮轰显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都将对公款挥霍这一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一股脑儿迁延到学者的学术结论上,“无良学者”等人身攻击型语言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从刑法学角度看,一项新罪名的立法确认需要对新型违法现象进行深入论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提出、论证到立法等环节都需要以慎之又慎的态度科学研讨,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从法治的角度看,“慎刑罚”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在各项论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草率开展新罪名立法,或者在民众情绪驱使下任意地将违法行为向刑法条款挂靠,都是对“法律应有明确性、稳定性”等法治精神的背离,也有违“司法独立”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
这种民愤驱动下对挥霍公款“入罪上刑”的喧嚣声浪,实质上仍不过是“严刑峻法”、“乱世用重典”等古代法家思想的翻版,而决不是现代法治思想指引下的严谨推断,最终必将落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而这种“罪刑依赖”甚或“刑罚崇拜”观念,反映出的并非法治意识的提升,恰恰仍是法治精神的贫瘠和匮乏。
更何况,“入罪上刑”是否就能遏制公款挥霍现象呢?正如贪污受贿等刑法业已明晰的罪名无法有效阻遏贪污受贿的蔓延一样,公款旅游、吃喝等挥霍行为,也很难因为“入罪上刑”而得到根本遏制。
其实,对于包括公款旅游等在内的挥霍公款腐败,从源头上说,需要规范的公共财政预决算制度加以防范把关;从过程中说,需要新闻媒体监督,乃至包括投票、罢免等在内的公民权利直接监督;法纪惩处,虽然有力,毕竟是事后的追惩,这种监督的有限性、滞后性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源头上没有强有力的预防、阻挡,中上游没有有力的拦截、分流,那么,面对公款挥霍这股已然汹涌澎湃的恶浪,党纪政纪也好,刑罚罪名也好,任是再坚固的堤坝,又岂能抵挡得住?(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