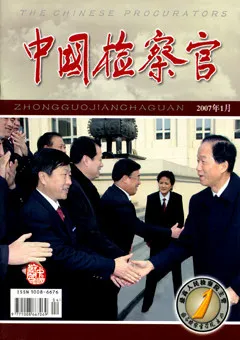政府招募的社区保安能否构成渎职罪主体
2007-12-29董月利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7年1期
[基本案情]
2005年,宁波市C镇政府通过公开招募,组建了一支社区保安大队,王某、刘某和沈某为该队保安队员。2006年4月12日晚上,保安王某从他人举报中获悉,租住在C镇某村的安徽籍许某有收购赃物的嫌疑,便联系正在巡逻的刘某和沈某,在许某租住处查获了黄铜、摩托车配件等大量赃物。三个保安以此为要挟向许某索取了8000元后,放掉了许某。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刘某和沈某身为C镇政府招募组建的社区保安大队队员,虽然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亦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其在履行维护社区治安稳定的职责时是代表国家机关,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渎职罪主体新增加的第三类人员。王某、刘某和沈某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挟私索贿,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王某、刘某和沈某应以滥用职权罪论处,但理由和上述不同。认为C镇政府与社区保安大队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保安大队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王某、刘某和沈某从事职务行为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渎职罪主体加的第二类人员而非第三类。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刘某和沈某依照职责履行公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索取贿赂行为构成受贿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政府出资聘任的保安和物业花钱雇佣(自己直接雇佣或从保安公司雇佣)的保安在工作内容上没有区别,本质上都是提供一种可供消费的公共产品——劳务,而不是公务,这种服务的提供不能仅仅因为是由政府出资就改变性质,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从公务活动运作的范围看,公权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公务活动作用的对象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私权利的勃兴也对公权力的“越位”时刻保持一份警惕。在宪政的纬度下,公权力运行轨道被分配为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社区保安所提供的社区治安防范虽然也具有生产公共产品的特点,但服务对象毕竟仅限于社区大众,社区以外的公众无法“搭便车”消费,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集体公共事务,而不是国家、社会公共事务。
其次,从公务的本质特征分析,公务是对国家、社会事务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具有“管理性”的特点。基于保证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这种管理性活动被赋予了权力性和优先性,而且这种权力只能由适格的主体享有,就行政权行使主体来说,行政权由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来行使,别的任何组织都无权行使。反观社区保安大队、中队之类组织,显然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效力层次较低的公安部规章也只是对保安的权力义务作出了概括性规定,其中带有强制色彩的扭送犯罪嫌疑人至公安机关的“扭送权”,任何公民都享有,并非专门授权。除此而外,现行法律法规很少规定保安拥有诸如调查、留置、盘问、要求出示证件、收集证据等具体强制性权力,政府组建的保安组织同样缺少法律上的授权。就行政委托来说,法律虽然规定行政权可以转授,但必须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委托就更为严格,而且委托组织是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社区保安大队不具备组织上的独立性,也不能以自己名义实施相应行为,因此,社区保安大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资格,只能协助公安机关执行。实际上,政府雇佣的社区保安和物业保安、联防队、社区巡逻队一样,都是社区自治管理的组成部分,履行的是自我管理职能,政府“埋单”组建专职保安、联防队、反扒队员只不过使得社会治理模式叠加了政府管理的强力因素,但不能从根本上颠覆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格局,逻辑的结论,社区保安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就不具备公务的特征,而是一种体力上的付出,属于劳务,只不过劳务的购买者由物业换成了政府。
最后,从公务行为运行法律后果看,行政措施在依法撤销前具有法律效力,相对方有忍耐服从的义务,否则会遭受相应法律制裁。当前,一些国家机关聘用人员如法警、书记员、协警员、安全监督员,他们虽然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他们在国家机关里工作,行使职权时代表的是国家机关,实际上也可能影响国家权力的正确运行,所以渎职罪的扩大解释把他们都规定为渎职主体。但这种扩大解释不能任意扩大,否则有违“重在治吏”的法治精神。保安队伍,作为社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外观上的一致性,公众无法区分究竟是物业保安还是政府保安,要求其忍耐服从,一方面显然会与保安受雇于物业、根本上取决于业主评价的主流价值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对社会公众来说,阻挠保安履行职责,似乎也很难有“防碍公务”的违法性认知。同时,由于政府保安的介入,使得业主权利保护更趋复杂,就目前司法实践主导性做法,保安工作失职,造成业主人身、财产损失的,物业一般须承担补充性赔偿责任;换成政府保安后,保安工作失职,造成业主人身、财产损失的,恐怕就连追究物业补充性赔偿责任也会成为问题,诉诸行政赔偿更不切实际,因此,笔者认为,政府聘任的保安所从事的工作从性质上说仅仅是提供了维护社区安全的劳务,而非公务,保安队员工作中具有案情所述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敲诈勒索罪而非滥用职权罪追究责任。
作者: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 [315016]
本栏目责任编辑:陈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