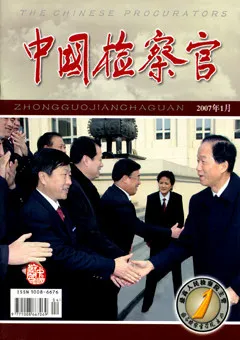从定罪与司法逻辑、共同关系与共同犯罪解析犯罪的认定
2007-12-29李洪欣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7年1期
内容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个案的争议往往隐寓着对法律问题的不同理解,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梳理和讨论,能够将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形成合情合理的法律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尤其是办案实务中的案例,不仅包括相近罪名间的混同,也包括相互不可及罪名的加入,趣味并复杂。
关键词: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 打击报复证人 犯罪构成 共同犯罪
[案情] 2002年12月,通州某小区两户居民住宅被窃,丢失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玉佩等物,该小区保安经理滕××为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积极查寻线索,买回了笔记本电脑等部分赃物,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作案人员冯××。后因证据不足,未全部认定上述两案均为冯××所为。2003年6月,法院以盗窃罪和销赃罪判处冯××有期徒刑二年。2004年年底,冯××在狱中给滕写来一封信,暗示将对滕不利(冯、滕二人案前即已相识)。
2005年1月,冯××刑满释放。2005年1月25日,冯××约集陈××、田××(在逃)、大刚(在逃),滕××也约来与冯同村居住的刘××,到聚友轩饭店“说事”。对于“说事”的内容,双方供证差异较大。
冯××供称,滕××说:“你刚回来,我肯定帮助你,我会给你补偿补偿”,并定好次日细谈。
滕××证称,冯××说:“我刚出来,衣服和鞋都是新买的,花了一万元,这些钱都是借的,你拿钱我得还人家,现在我每天吸粉也需要一千元”,“你先给我拿五万元,我先花着”,(滕××说:“现在没钱,等过段时间你再找我”),“武××我得找人干了他,因为是他找人点的我,让我进去的,我今天没有找着他,找着了就干了他”。
陈××最初供称,冯××说:“我刚出来,身上穿的衣服花了一万多元买的,我刚出来没钱,你得帮我。”滕××说:“你要不抽大烟我可以帮你”。后推翻原供,称“我只听见冯××让滕××帮他,我没听见冯××跟滕××要钱。具体怎么帮,他们没说,我就不知道了”。
刘××最初证称,冯××说:“我这身西服和鞋都是新买的,花了一万多”,“我因为给你点了,进去两年多,在里面受了挺多的苦,你得补偿”,“你就先拿五万元我花着,完了之后再说”。并证称冯、滕二人约定次日单独谈。后推翻原证,称“当时我没有听见冯××向滕××要钱。冯××只是问滕××怎么办,滕××说第二天上午我们单独聊,冯××就答应了。以后我没听见他们说这事。”特别是否认曾说过冯××向滕××要五万元的话。并称其妻能予证实,其妻确予证实,并证称刘当时还对记录提出了异议。有关民警也对其妻在询问刘时亦在场的情况予以证实。
双方分手后,滕××、刘××到京东垂钓园歌厅,滕电话约来武××,后武××又叫来山东老二(在逃)等人,与冯××等人再次会面。其间,双方发生冲突, 武××与“山东老二”等人离去,冯××亦离去。陈××、田××、大刚借口“滕××生事”对滕进行殴打,致滕轻伤。
武××证称,在歌厅,滕××说:“冯××找了三个社会上的人,跟我要补偿费”其问“要多少钱”,滕××说:“那还少的了,明天再说,冯××还找你呢”,其问“找我干什么”,滕××说:“还能干什么,要钱呗”。
本案是由证据的认定继而引发定性和处理的分歧。公安机关以冯××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数额五万元)、陈××构成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经审查,本案证据的焦点在于冯××是否提出了明确的敲诈勒索数额。审查认为,在案证据不能支持冯××敲诈勒索五万元的认定。基于此,对于定性及处理形成了以下几种意见:
1.冯××从狱中写给滕××的信及冯、滕相见时的语言,反映出其威胁系隐性存在,程度不强,且无证据显示冯索要钱财的数额,敲诈勒索罪难以成立,现有事实证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冯应作存疑不起诉。陈××构成寻衅滋事罪定罪起诉。
2.冯××的信件、语言表示及其行为,基于人们的一般理解,可以判定冯××的敲诈勒索行为,虽然五万元的数额难以认定,但几项言词证据均可以支持对其敲诈数额以下限一万元的认定,故对冯可以敲诈勒索罪(未遂)起诉,对陈以寻衅滋事罪起诉。
3.虽然几项言词证据均提到了一万元的数额,但从冯的语言环境判断,所谓一万元只是向滕实施勒索的一个示例、借口,表明其敲诈勒索的意向,而非具体的犯罪数额,故应认定冯××的行为为敲诈勒索罪(预备)起诉,认定陈××的行为为寻衅滋事罪起诉。
4.以敲诈勒索对冯××定罪处理,在证据和犯罪构成上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冯××的行为包含于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内容之内,故可以该罪对其进行处罚。同时,陈××也应以此定罪处罚。因为两起事实是有机的整体,冯××基于报复的动机纠集陈××等人共同实施的行为以及陈××等人单独实施的行为,冯××、陈××等人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若对陈××另定寻衅滋事罪,则割裂了两起事实之间的联系,也降低了冯××行为的危害程度,同时,难以解释冯××对于陈××等人殴打滕××的行为未指使、未参与的情况。
5.认同把前后两起事实作为一个整体,但认为应以涵盖于打击报复的动机之下的特征比较明显的寻衅滋事罪定性处理。
就上述意见,无论支持哪一种意见,都可以有充足的文字为文,但是,笔者认为,对本案的争议,足以引起我们对立法司法中一些基础问题的深入探讨,尽可能地统一认识,减少类似争议,这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定罪与司法逻辑
面对刑事案件,正常的司法逻辑一般是,通过犯罪概念对罪与非罪作出抽象的判断,再通过犯罪构成把犯罪的概念具体化,以确定犯罪的成立。抽象判断与具体化二者有交叉和重合。这一过程中,抽象的判断一般是隐形的,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省略的。对于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司法人员,根据其司法的先验便可以作出判断,这种先验包括法律规范、法学理论的掌握和司法经验的积累。
当对犯罪的抽象判断被忽略时,就造成了逻辑偏差,即直接以犯罪构成的条件框套案件事实以决定罪与刑,狭隘地关注先验的某个罪名(一般是司法人员知识体系中最熟悉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所需的条件是否满足,而忽略该构成之外的其他情况的综合把握(包括一些不常用的罪刑设定),难免造成司法判断的错误。
通过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的交互作用,判断该案罪在哪里,犯在何条,不会直截了当地切入某个条款加以论证,而可能会在几个条款中选择最适用的条款。所以那种直接引证某罪的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对犯罪的抽象判断。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设定,犯罪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突出表现在对《刑法》法益的侵害,本案中,冯、陈的行为侵害了多个方面的法益,包括公民的财产、健康、社会秩序、司法活动,因此,应当在较大的范围内根据具体的犯罪构成确定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说,要用事实去对应犯罪构成,而不是用犯罪构成去取裁事实。我们说某人犯某罪,并不代表其行为只侵害一种法益,究竟以何罪对其科处,还是要看其行为符合哪种罪的犯罪构成,也就是要对犯罪的刑事违法性进行衡量。
在犯罪构成的考量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影响着对一个案件的规范评价,也就是说,案件有时不以犯罪构成的规范形态呈现,当我们以最适合犯罪显性样态的犯罪构成去评价时,却往往发现它在一些要件上存在缺失。这样的情况既有立法缺陷的问题,也有应用的问题。从现行法律效力的角度,不符合犯罪构成要求的,当然就不能成立该罪,也就当然地需要考虑其他的犯罪构成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作非罪处理。我们不能以最适合犯罪显性样态的犯罪构成去评价时,可以以符合条件的犯罪构成去评价,确立该犯罪构成所成立之犯罪应施予的刑罚处罚。
对以上所述总结说明如下:
1.犯罪概念的抽象判断与犯罪构成的具体判断在司法中不可或缺;
2.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以作出多重判断,决定了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也具有多样性;
3.确立案件性质的是最符合刑法设定的构成条件的犯罪,而不是最适合犯罪显性样态的犯罪。
还需要说明的是,犯罪人的犯罪故意与刑法评价的关系。笔者认为,犯罪故意不是指犯罪人主观上犯某罪的故意,而是实施某种行为的故意,而确立该故意为犯某罪的故意,是司法机关给予的评价,这种评价从属于对最符合刑法设定条件的犯罪构成的判断。
还需要引申的是,《刑法》条文设定中的保护关系。我国以四要件构成为标准的犯罪构成模式,是一种平面整合式的一次性判断,不可能涵盖犯罪的各种复杂情态。但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有些犯罪的设定其包容量是相当大的,这种宽松式的构成(如打击报复证人罪等)与要求严格的紧缩式的构成(如敲诈勒索罪等)形成了一种保护关系,当不符合后者的条件时,应考虑前者的应用。
还需要提示的是,罪刑法定不仅是出罪所擎的大旗,也是入罪的纲鼎。我们不能以罪刑法定遮掩司法的无能,放纵犯罪将贻害无穷。司法人员应该合理运用法律技术最大限度地制裁犯罪,善于在法律的适用中发现和延伸法律的活力。
根据本案的显性特征,可以先验地判断以敲诈勒索罪的构成加以评价,但很明显,在犯罪构成上存在缺失,这种缺失决定了围绕敲诈勒索罪的努力的“完形”处理都是值得攻讦的。但当我们以打击报复证人罪加以评价时,却会发现本案未出离于该罪的构成,可以适用该罪对冯××定罪科刑。
二、犯罪的共同关系与共同犯罪的认定
认定犯罪,要综合全案事实,通过对全案事实的分析从中取裁犯罪构成所需的事实,而不是以某一犯罪构成人为地割裂事实。任何犯罪,都不是一蹴而就,在行为上都会有一个持续的过程,从行为的发生、发展、恶化到有结果的产生,也许某犯罪构成只关注恶化或结果产生那一段的行为,但并非其他行为就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在判断犯罪之成立时是不能被抛开的。特别是在有数人参与的案件中,首先要确立数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共同关系,以判断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各参与人有的可能参与全部行为,有的可能只参与部分行为,如果缺乏对全案事实的综合考量,往往会割裂事实,造成认识上的障碍和结论上的错误。前述案件分歧意见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共同犯罪意味着共犯人之间的行为相互利用相互补充而成为一体,每个人的行为都和结果之间有物理或心理的因果关系。从本案的全部过程来看,冯××因与滕××结怨,蓄意报复,并召集陈××、田××(在逃)、大刚(在逃)帮助其实施,报复的直接目的是向滕××要钱,最初是由冯××与滕××具体交涉,陈××等三人站脚助威,案件在报复的前提下呈现出敲诈勒索的面貌,但由于数额要件的缺失,以敲诈勒索罪定罪显然难以成立,因而案件继续沿着报复的走向发展。此时,冯××、陈××等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不仅有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也有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其后,滕××电话叫来武××,试图把武拉入自己一方,以对抗冯××,因“山东老二”等人的介入,冯××暂时中断了其个人行为。但是,冯××前期的行为与此后案件结果的心理关系并没有中断。陈××等人的行为自开始就是在帮助冯××实现其犯罪目标,因为滕××叫来武××并引起“山东老二”一派势力的介入,才形成了对滕××的不满,继而有殴打滕××并致轻伤的行为,是帮助冯××实施报复行为的继续,也可以说,后期陈××等人的行为仍然与冯××有着共同的报复目的。冯××虽然中断了个人行为,却对陈××等人的行为听之任之,并没有截断心理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本案应成立共同犯罪。
三、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和罪质的补充关系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对于共同犯罪有两种对立的解释: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犯罪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行一个特定的犯罪,认定共同犯罪是否成立,以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准,简单地说,共同犯罪是共犯人共同犯某一罪。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是数人由共同的行为完成各自意图的犯罪,也就是说,数人的共同行为可以跨越数个犯罪而实施,认定共同犯罪是否成立,以共同的犯罪事实为标准,共犯人可以构成不同的犯罪。行为共同说对于共同犯罪的解释更加突出了共同犯罪与单个人犯罪相较的特异性,使共同犯罪处罚原则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原生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又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并没有两大学说的明显分野,但对于共同犯罪的不同主张,仍未脱离于上述争议,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按照犯罪共同说,共犯人同犯一罪,罪名只能定一个,按照行为共同说,罪名可以不同一,然而行为共同说并不适合我国的犯罪成立模式。我国理论界还提出了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二人以上就部分犯罪具有共同的行为与共同的故意,便成立共同犯罪;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又存在分别定罪的可能性。”然而笔者认为本案还没有涉及到这个复杂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冯××与陈××等人在行为初期即达成了报复滕××的共意,此后陈××等人殴打滕××并致其轻伤的行为仍是报复行为的继续,所造成的伤害后果也并未超出打击报复证人罪的客观评价范围,从量刑上看,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打击报复证人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者也大体相当,所以,不必要进行伤害罪的独立评价,二人的行为均认定为打击报复证人罪。假如陈××等人殴打滕××致重伤,该结果已超出打击报复证人罪所能涵盖的范围,那么笔者就会赞同部分共同犯罪说,认定二人在打击报复证人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陈××以故意重伤罪定罪处罚,对冯××以打击报复证人罪(情节严重款)定罪处罚。
该案的分歧中,主张对陈××单独定寻衅滋事罪而冯××不定罪的观点是以否定共同犯罪成立为前提的,因笔者已论述过共同犯罪的成立,在此不再赘论。主张对全案以寻衅滋事定罪的观点,无法解释冯××的共同行为,难以立论。
此案法院以冯××犯打击报复证人罪、陈××犯寻衅滋事罪定罪科刑,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歧意见,且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性意见,笔者持异议。
对冯××定罪是以确立共同犯罪为前提的,而且本案的全部事实也支持对冯、陈二人行为的共同评价。法官作出如此判决只能是基于对二人行为的分别评价,那么对冯只能评价殴打滕以前的敲诈勒索行为,在法定刑相当的情况下敲诈勒索未成立犯罪而打击报复证人成立了犯罪,则是说不通的。认定冯××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加上后面的殴打致伤情节,但单独评价冯××的行为时是难以把其没有参与的行为评价进去的。以寻衅滋事罪评价陈××的行为,如果抛开了前期的行为背景,很难解释殴打他人的“随意性”,而当考量殴打他人的行为背景时,又难以作出该殴打行为就是“随意”的判断,所以,得出寻衅滋事罪的结论是武断的。
另外,寻衅滋事罪在刑法罪名体系中的定位相对于有关犯罪而言是一个堵截性或称兜底性的条款,是将客体区分上不便纳入其它类罪的,以及未达其他类罪的犯罪标准,而又需要进行刑罚处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聚合设定的,当行为符合某一具体的犯罪构成时,一般以该具体犯罪论处,除非该具体犯罪之处罚与其危害性有不相协之处,可以利用想像竞合的原理认定寻衅滋事罪以维护罚当其罪的原则。当然这是本文探讨之外的问题。
责任编辑:苗红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