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定神逸邹东涛
2007-12-29欧阳君山
中华儿女 2007年4期

2004年10月,某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老少咸集,群贤毕至。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是研讨会的重要嘉宾。
我那一次也到场。但我没想到,会议发言时,邹东涛先生“跑了题”,节外生枝,高度评论了我这个无名小辈,而我那时候还仅与他有过一面之谈。我后来才知道,邹东涛推崇创新与探险,偏爱“异端”和草根,打那以后,我与邹东涛先生便热络起来。
端庄厚重气方定
初一见邹东涛,你会明显地感觉到此公的端庄厚重,很端正地坐着,看着你,听着你,你肯定能够感觉到他的友好和善意,但他脸上的表情不会有什么变化,眼睛也没有什么转动,连坐着的姿态都不会有什么晃动。
在笔者的印象中,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嘴巴大,能悬河;耳朵小,春风不度玉门关,难以听进去别人的话,极端者甚至听不得别人的东西。这就可见邹东涛先生之难能可贵,有一只能听八方的大耳朵!尽管做过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目前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但邹东涛主要还是专家学者的身份,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涵养、政治修养的功夫,确实超越一般的专家学者。
有一个鲜明的例证,这就是他始终不用“左”和右的词。学界江湖流行各种小圈圈,划家归派,主义一大堆,“左”和右更是十分时尚的帽子,随便扣一顶,节省多少口舌,强化多少效果啊!而此公从不用“左”和右的词,难得也!
端庄厚重其实是人格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都知道清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个神态非常特别的人,《清史稿》有这么一记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曾公的特别神态其实就是端庄厚重。
所谓端庄厚重,说到底,就是一种定气的功夫。一个人必须先有气定的功夫,后才可能谈得上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否则的话,就一切都是浮的!
猴子老虎谋创新
邹东涛在理论思考中却非常有锐气,前卫,探险,突破,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表现出十足的“猴气”加“虎气”。个中道理,邹东涛总结为16个字,琅琅上口:“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早在1980年,邹东涛在家乡陕西省汉阴县作企业调查,便有感而发,提出“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并成文寄《经济研究》。编辑部复信:“该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目前不宜发表。”20多年过去,问题仍然“十分重要”,还不知道要让邹东涛先生超前多少年呢!
在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学习阶段,邹东涛更是英姿勃发,表现出非凡的思想勇气和理论魄力。1985年春,“全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邹东涛在大会上发言,掷地有声地提出:
理论再也不能跟在实践后面爬行;
对“基本理论”也要进行再认识;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
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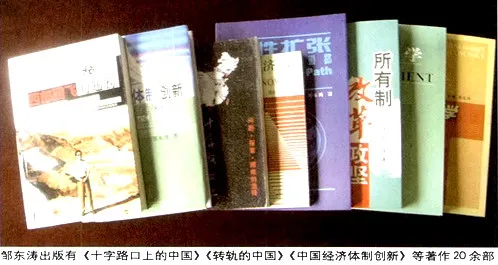
即便是今天,这种种说法也仍然是掷地作响的,锐气不减当年。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最后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百尺竿头再跃前,邹东涛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一文中更进一步,颠覆了被视为常识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说,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且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实践!这就是邹东涛,想常人之未想之不敢想,言常人之未言之不敢言。
《人民日报》2001年6月2日和《求是》杂志2001年第8期都刊发了邹东涛的文章《哲学社会科学: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邹东涛对创新的大力推崇,不但来自对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对时代的切身感受,他的全部观察和思考都紧紧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联系在一起,是一位冲锋在前的时代弄潮儿。正是时代赋予了他创新的理论锐气,给予了他创新的理论灵气。
生逢其时,躬逢其事,邹东涛对经济学的最初学习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现在虽然是经济学教授,邹东涛原本是学物理的,哲学社会科学最初是自学的,按他本人的说法,“草台班”出身。而且当时漫无所归,“万金油”式地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邹东涛才锁定经济学,高度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
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邹东涛先生《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上下册),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体制创新巨著,它记录了邹东涛从1980年初到2003年6月之间20多年的著述,全部内容都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运筹于改革年华,探索于开放时代”。
当今中国,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另一方面,社会上一旦有某个学者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往往被看作“保守”,甚至被挖苦为“时光倒流”。我查阅了邹东涛先生这位体制内学者《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感怀》《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等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章,也读了他两首《我读马列毛》和《咏社会科学创新》的诗,确实感觉到他是真正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从他的文稿中丝毫也没有发现一点“保守”的痕迹,相反,我所读到的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19世纪”、“劳动价值论:把创新写在旗帜上”、“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西方经济学要本土化”、“创新立潮头,文章忌跟风。莫拘本本言,最重实践功。理论与时进,求索永攀峰。”这些话语无不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精神。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最本质、最高明的地方都在于:它充满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邹东涛虽然主要是作为专家学者,但在看问题和想事情时特别讲务实,注重看效果,不意气风发,不天真浪漫,一切从现实出发,这最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座右铭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翻读《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让人一次次惊喜,成熟的改革理论家风范跃然纸上,全书充满“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睿智。
所谓“做‘中国猫’,抓‘中国鼠’”,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想问题,办事情,无论是国外的主义还是经验,都可以用,也应当用,但不能够盲用,特别是不能够忘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
“中国国情”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因为这是一个硬指标,不承认不行。
但“中国特色”却是另一种命运,很多人并不承认,甚至口口声声地叫道:“什么中国特色,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的人,都一样的心,有什么特色!”“即使是有所谓中国特色,也一律不管,直到抹平,全球化要的就是化!”
究竟有没有“中国特色”这么回事呢?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中国特色”是真的实的,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即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则旗帜鲜明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甚至有时候也被直接简称为“中特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十六大更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历史的经验不能代替理论的思考,因为历史的经验有时候可能是历史的特例或偶然。西方有人之所以大力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要“化”掉中国,乃至要“化”掉所有其他的国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眼中,西方式自由民主是普适的,不是“西方特色”的。
这样一来,理论上存不存在“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如果理论上没有“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那历史的经验可能也值得推敲,或许所谓经验只是个假象;如果理论上有“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那历史的经验无疑就更加稳固。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被邹东涛先生称为“颠覆之作”,它最大的颠覆其实是为“中国特色”平反!“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表明,“中国特色”不但在理论上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一席高位。回头一看,倒是西方的东西是“西方特色”,属于历史的特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中的东西。
邹东涛的座右铭事实上已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所明证。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于“苏东”,它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所谓“新体制增量推进”,有时也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中国猫”抓“中国鼠”,用经济学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成本更低的交易方式;用稍微政治化的话讲,这是和平渐进。同为社会主义大国,前苏联的改革归于失败,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这样的“中国猫”功不可没!
中国的下一步怎么走?用邹东涛的话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该“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是啃“骨头”,需要攻坚,包括行政体制改革之坚和政治文明建设之艰。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坚”与“艰”,“中国猫”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只有真正的“中国猫”,才能确实抓到“中国鼠”!所谓真正的“中国猫”,就是那种勤而不懒、廉而不贪和捕鼠有道之“猫”,而不是那种在鼠面前退避三合、任凭鼠害猖獗、甚至与鼠勾结狼狈为奸之“猫”。
邹东涛先生是一只典型的“中国猫”,一只气定神逸的“中国猫”,始终不忘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猫”,他曾草诗自励:改革开放铭心间,华夏复兴垫小砖。路漫漫兮其修远,做猫抓鼠自扬鞭。
愿邹东涛先生这只“中国猫”抓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鼠”,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