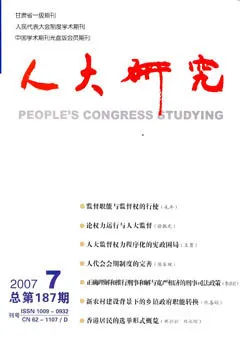从一项政府规定透视依法行政
2007-12-29李锋
人大研究 2007年7期
据媒体报道,某市政府有关部署对旧货市场的整顿行动,规定今后市民在销售、购买二手手机、电脑时必须出示身份证,并由经营者做详细记录,凡是明确有收赃嫌疑,拒不交代收购来源和身份、住址等,一律予以刑事拘留的高限处罚。看到这则报道我不由产生疑问:政府是否有权作出如此规定?该规定内容是否合法?政府作出该规定是否必要?
首先。我们看该市政府是否有权作出如此规定。仅仅因为“有收赃嫌疑,拒不交代收购来源和身份、住址等,就要一律予以刑事拘留的高限处罚”。这明显是政府越权“立法”。只要不是法盲,都知道“刑事拘留”是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一种,目的是为了查明案情、明辨是非,不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性质上,它是一种强制措施,不是一种处罚方式;地位上,它是刑事诉讼过程的一个环节,不是一个事件的“结案陈词”。更进一步而言,依《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对于涉嫌犯罪的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相关刑事法律来作出规定。任何一级政府都无权对此“下结论”,包括国务院。难道我买了二手电脑,没有向政府老老实实交代何时何地于何人购买的,我就得到公安机关去“享受免费吃喝拉撒”?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十年了,《立法法》实施也七年时间了,作为一级政府竟然“背法治而行”、“逆宪法而为”,实在令人费解和遗憾!
其次。姑且不管该市政府是否有权作出该规定,到底该规定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质?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交易的确需要“验明正身”、进行登记,如房屋等不动产交易。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不动产价值较大,如若不登记,容易引发纠纷并且取证将十分困难;二是不动产位置固定,无法自由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能通过登记等公示方式使公众明确其物权归属;三是不动产流转速度较慢,因而易于登记管理。但是手机、电脑这些物品是典型的动产,市场流通速度很快、价值不太大但数量甚多,因而对其进行逐一登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然不切合实际。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民法通则》对动产和不动产规定了不同的交易公示方式:动产以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船舶等特殊动产除外),不动产以登记为要件。该市政府的规定显然违反了《民法通则》这部民事活动的基本法,又是“下位法”(严格说该市政府的这项规定不能称之为法)违反上位法的“典型代表”。试想,如果各个政府都如该市政府这样不把民法“放在眼里”,那民法如何调整民事活动?人大立法还有何意义?那所有的民事活动、民事关系都交给政府管理好了!到时候我们的政府将难受其烦、难负其累!
再次,政府作出此项规定是否有必要呢?不能否认该市政府制定此项规定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因为近些年来,盗窃手机、电脑的行为日渐猖獗,其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赃物能顺利出手甚至还很走俏。现在很多二手市场上的确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赃物。该市意图通过此项规定切断赃物的流通渠道,从而遏制盗窃现象,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对公民的负责。但效果上却是画蛇添足。一方面,当今社会,手机、电脑这些物品随处皆有,价格不高,普及犹如衣裤鞋袜,寻常百姓举手可得。“物美价廉”的二手手机、电脑更是大行其道。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买卖个二手手机、电脑是“小菜一碟”,本是件逛街之余随意而为之事,可现在得“在公安机关发放的‘登记簿’中详细记录品牌、型号、唯一标志码、数量、价格等基本特征,详细登记出卖人、购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物品来源去向的信息……”如此郑重其事,人们在二手市场岂不惶惶——万一没操作得好。被刑事拘留可不是闹着玩的!众所周知,小额交易本应该要限制少、效率高,以提高民事流转关系,活跃市场、方便民众。打击犯罪是对的,但矫枉过正给老百姓带来生活不便,还拿刑事拘留来“吓唬”人就是大错特错了。
另一方面,如果明知是赃物仍进行买卖的确可能涉嫌犯罪,我们的司法机关完全可以依据现有的刑事法律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已经有相应的明确的法律来规范,政府又何必还参与进来搅和一番呢?似乎有点多此一举!难道没有这项规定,司法机关就无法打击盗窃违法犯罪行为了吗?表面上看来,政府是在积极作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笔者以为,该市政府的此项规定有转嫁压力、推诿义务之嫌。盗窃手机、电脑等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政府恼火难受却又没有根治之策,只好“乱世用重典”——不管好人坏人,没有登记我就抓人。于是政府的压力无形之中转到了老百姓头上,政府的义务活生生要大多数无辜的老百姓一起来承担。什么逻辑啊!
透过该市政府的这一规定,笔者所联想到的是依法行政之难:
其一,谁来推行法治?看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国家,亦或政府。目前看来,中国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由国家(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渐次推进的法治之路。但是难就难在:法治之核心正是要“治权”,而政府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行使者,谁来监督政府行为?政府不“治权”反而“以权治之”会承担什么责任?等等,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孟德斯鸠曾指出:“法治思想具体地说就是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法治从根本上说是“民治”而非“治民”!显然,通过前述分析,政府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不应是法治的主体,相反应当是法治的客体。进而,谁来推行法治?法治主体是谁?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中国法治之首要难点。
其二,如何控制行政权?行政权的膨胀与扩张是当代宪政的发展趋势,这是有其现实需要和合理性的。但如何有效地引导、控制行政权在法治的道路上进行却是令人费思的宏伟工程。就是在法治比较发达的美国,对总统权力的扩张也是头痛不已。中国历来是行政权独大,立法权、司法权虚弱。我国宪政确立的分权体制也决定了现实中很难遏制行政权的擅断、专断,这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主要难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谈到法治与行政权时,认为尽管法治意指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但其重心在于政府应该依据公知的、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规则体系办事,即要求政府的权力行为包括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自由与义务的行为都必须能证实具有法律的授权,能说明其严格的法律渊源;政府不应享有超越于普通法律的特权与豁免权,并且法治还要求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司法机关进行法律上的判断,以阻止政府滥用权力。
其三,如何培育法治文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钟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这表明,公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是法治建设最深厚的心理基础。没有民间积淀深厚的法治文化的有效支撑,法治实难深入、持续下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人们心理上默许了政府恣意法律这种状况的存在;很多人虽然痛恨权力的妄为腐败,可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引发和强化了人们心里的权力崇拜意识。由此造成既想“限权”又想“求权”,或者无权之时“日日拆庙”、有权之时“时时护庙”的“二律背反”。如此,法治大厦难以矗立于大地。另一方面西方的法治文化又与中国本土文明不能够良好兼容,难免“水土不服”。因此,如何培育本土化的法治文化,树立正确的法律与权力意识,的确有待于我们继续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