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史(连载四)
2007-11-01吴晓波
吴晓波

八十年代,新生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度过了野草般肆意疯长的阶段,在行将跨入1990年时,命运再次显示出它的波澜与跌宕。一群产权意识觉醒的企业家们,正小心翼翼的廓清资本的界线,却陡然遭遇全球的政治寒流,一切近乎停滞,甚至倒退。但资本顽强的意志不仅没有被压倒,反而在证券市场上迅速壮大,企业的资本运营和组织结构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改革重新启航……
产权意识的苏醒
1988年,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他们开始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
1988年12月6日,24岁的国务院机关某部副科长王文京和他的伙伴苏启强一起来到北京海淀区工商局领公司执照。但却被告知,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面对这一问题,有不少人为了图便利,就顺便挂靠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因此而生。
而被拒绝的王文京不甘心,他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两个小时后,他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从公务员到个体工商户,这好像有点污辱人。
王文京当时不太清楚的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私营企业那时已经开始注册,不过,政府选择了东城区作为试点。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2001年,用友上市,王文京名下的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他没有跟很多同一代企业家那样受到产权归属的困扰,其原因便在于12年前的那次企业登记,他去领了一本“身份低贱”的执照。
如果说,王文京资本意识的觉醒是天生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已经走在创业路上的企业家们则开始认识到产权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一切都不可能从头再起,但他们开始考虑采取一些隐晦或曲折的方式,为日后的产权清晰留下腾挪的空间。
1988年1月,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变压器。柳传志选中了两家合作者:一家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柳传志父亲任董事长;另一家就是吕谭平的香港导远公司。1993年,柳传志父亲退休离任,中技转公司随即退出香港联想;1996年,柳传志将吕谭平从香港联想劝退。
在中国企业史上,吕谭平式人物的出现,既不是意外,更非偶然。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很多国有企业都在悄悄尝试这样的办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的方式,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出现。
与这些幸运者相比,当时中国电子电器100强之首的万宝冰箱就倒霉透顶,企业的领导人邓韶深最终身败名裂,远走他乡。
1988年,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100万台,年总产值10多亿元,同年张瑞敏的青岛海尔才达到20万台的规模。万宝在产权上属于广州市二轻系统,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快速成长后,邓韶深希望在资本上对企业进行改造。于是,在他的四处奔波下,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将之列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试点集团之一,并开始直接参与万宝的发展战略与产权改革事宜。矛盾就在这种变革中悄然萌芽。
在万宝冰箱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广州市二轻系统先就把一大堆“烂苹果”一股脑儿地往邓韶深身上推,万宝组建集团,先后吃下24家亏损的中小工厂,这些久转不动的企业日日消耗万宝的利润和邓韶深的精力。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争斗日渐激烈,上级指派下来的党委书记与邓韶深不和,两人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各有己见,前者无条件听令于主管部门的指挥,而邓则有自己的一盘棋。这给地方政府的感觉就是邓韶深已经尾大不掉。
其后,万宝因产销失衡,在短时间内出现将近8亿元的呆坏账,万宝电器一蹶不振。
【点评】企业沉浮命系产权
万宝的陨落,看上去是经营不善所致,而其内在的矛盾纠葛无一不与体制有关。承包制所能激发的创造力在企业崛起之后就迅速地消退了,当邓韶深想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继续有所动作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动作,遭遇致命的狙击。在这一部中国企业史上,邓式命运并非孤例。十年后,如健力宝的李经纬和科龙的潘宁,都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同样的命运陷阱。
资本市场的艰难启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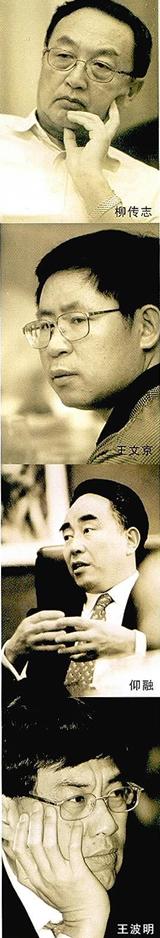
股票与债券,在最初几年无人问津,而到1992年时却席卷全国,并产生舞弊事件,引发骚乱。其中因幼稚而显得忙乱,因缺乏监管而恶意操纵,一场关于利益与野蛮的较量将贯穿整个资本市场发展史。
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全国各地像万科这样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并不在少数,但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普通的市民眼中,股票、债券也是一个完全的新玩意儿,敢于下水一试的人没有几个。1986年,上海工商银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卖出延中和飞乐股票1700股,后来每天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近乎于“死市”。
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规范化的资本市场,那些发行了股票和债券的企业无非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笔钱而已。
筹建资本市场
1988年8月,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没有人请他们回来,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是唯一的动力,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
就在北京的高西庆和王波明为资本市场的筹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卷起袖子干了起来。
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上海人民银行(后来转给上海工商银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在1988年底高西庆和王波明们就搞起了一次“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着手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事宜。但是,工作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动乱打断了。直到1989年下半年两地才重新开始。
1989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致开业词,尉文渊敲锣开市。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
上海开市的消息,在南方的深圳引起了连锁反应。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
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的大张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灏没有出现在开市仪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董国良出席。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1991年7月深交所的正式批文下达,当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
不过,无论创市的过程是怎样的幼稚忙乱,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公司将演出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戏。
股市硝烟
转眼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专门就证券业说了一段话,认为证券、股市要坚决放开,错了可以纠正,受此刺激,那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
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00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发奇想,发明出“大户室”制度。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游戏场。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发行新股只好实行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和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随后10月12日,证监会成立,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
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候,丑闻就已经如一道无法摆脱的影子随身而至了。同年,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原野公司便爆出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纵股价事件。
两年里,原野公司11次变更股权,屡屡发布诱人的投资预期,导致股价节节上升,彭建东则多次乘机抛股套现。1992年4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向公众披露原野问题。7月7日,原野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第一只被停牌的股票。
【点评】资本凶猛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股市的暴涨狂跌,乃至发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而如何驾驭这头资本的巨兽,为我所用,却至今不能游刃有余。
乍热骤冷下的“帽子”戏法
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前后,便是这种“循环交替”中一个比较敏感而动荡的一环。
“物价闯关”与“抢购风”
在很多年后,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的时候,更多的会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1988年的宏观经济再趋紧绷,三年多的高速成长使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而推行了4年的物价双轨制在此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效应——《经济日报》称之为“官倒祸国论”。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正在朝自由市场主义的方向快速转型。在这一年,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中,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的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
随后,3月份,闯关行动从最大工业城市上海开始。当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30%之间。这一调价政策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弗里德曼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
“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全国民众的改革热情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事实上,正是这次经济政策的失败,成为第二年春天爆发全国性动乱的主要诱因之一。
整顿私营企业和重戴“红帽子”
1989年,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动荡变幻的年份。横亘在东西方世界的铁幕正在倒塌中,苏联瓦解。
经济局势的动荡,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一直被压抑着的、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
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
整治首先从对私营企业的偷漏税打击开始。8月份,国家税务局下发文件,一个全国性的偷漏税打击行动开始了。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它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新兴的家电业成为整治的重点,增长最快的冰箱业则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就是对全国已经出现的数千个专业市场流通环节开始清理。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当时距离文革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王廷江是山东临沂市沈泉庄的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价值420万元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王廷江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后,那些在1989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都通过各种形式回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当时这确乎是人们恐慌心理的某种体现。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则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到1990年3月为止,全省共有222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1.8亿元。
清理帽子催生的“股份制合作企业”
1989年之后,随着宏观形势的紧张和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严厉整治,“挂户经营企业”、“红帽子企业”或“假集体企业”再次突然升温。据统计,在广东汕头地区,此类企业就有1.5万家之多,占到集体企业注册数的六成左右。1990年中期,政府及媒体突然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导下,各地开始了对“红帽子企业”的清理工作。
这个清理工作前后持续了4年,大批私营企业被迫“摘帽”,并绕道走出另一番模式——在浙南和珠三角地区开始流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是精于变通、擅长“绕着红灯走”的温州人发明出来的。据记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温州市城郊的瓯海登山鞋厂,它是1985年5月由26个农民集股7.2万元创办的,这些农民既是工厂的股东,又是员工,所以被称为“股份合作”,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不过,这种合作制一旦规模大起来,就经不起推敲了,因为不可能让后来招用的工人都一一地成为股东。到1988年,聪明的温州干部又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产权模式。这年8月,苍南县在一家名叫桥墩门啤酒厂的小企业搞试点,设计出“股份合作企业章程”,此章程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规定“企业财产中有15%是企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资金”。正是有了一部分公共积累,股份合作制企业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集体经济的范畴。
温州的这种新型企业模式很受改革派理论人士的青睐,当私营企业备受左派思潮侵扰之际,股份合作制成了一个理想的过渡模式和“避风港”。1990年2月,开明的农业部发出第十四号令,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定规定》,其附带的章程蓝本便是桥墩门啤酒厂的那个章程。这种模式的尝试削减了保守力量对私营企业的无休止的清算,也让企业部分地完成了资产所有权的清晰化。
【点评】历史的考验
1990年前后爆发的系列问题,既是来自全球的政治寒流,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真正的历史考验,当历史的矛盾累积在一起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但祸福相依,风平浪静之后,人们终究会看清改革的方向,并且更加坚定不移。
市场化改革的新起点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以及发生在1989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成为改革的底线,一切的变革都将在渐进和妥协中展开,任何有可能引发社会阶层情绪或利益激变的改革都被放置一边。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迅速地从过热中冷却了下来,各种投资全面停摆,消费的持续低迷立即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苦恼。“启动市场从何入手”又成为全国媒体热议的主题。
从1992年初开始,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这期间的讲话后来都被整理成了“南巡语录”——“三个有利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这些讲话的核心其实便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10月,中共十四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92派”新浪潮
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到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
这其中,在政府的中底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呆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天然的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国企改制的资本盛宴
早在南巡讲话之前的1991年,就有先行者从国企改制中嗅到了利润的气息,他就是仰融,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掌握了现代资本游戏规则的中国企业家。
1989年,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他深知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将带来巨大的利益空间。他看中的第一家国企就是沈阳金杯汽车,作为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沈阳金杯于1988年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有余却响应寥寥。便在此时,仰融上门洽谈,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的股份,之后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仰融还为此专门在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之后,仰融开始筹划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对纽约证交所来说,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只正式挂牌的股票。它在当年的美国股市轰动一时。
仰融在1991年前后的这一系列资本操作,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娴熟——以少量资金控股资本质量良好却暂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在免税天堂设立“壳公司”、以“中国股”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现。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将成为无数商业奇才崛起和沦陷的重地。
与仰融相比,更加财大气粗的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的次子黄鸿年,他可能是最早从南巡讲话中读出商机的外籍企业家。
为了实施他的进军中国策略,黄鸿年收购了香港股市一家日资亏损公司,将之易名为中策,自称“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然后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的大旗,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借南巡东风,用好政治牌,高举高打,以气造势。从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间,中策集团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196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100多家,短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黄鸿年在1992年的热走,彻底炒热了“资本经营”这个名词,自然引发了其他国际公司的效仿。泰国华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谢国民同时来到了杭州青春宝药业公司。青春宝当时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
【点评】改革新动力——市场经济制度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未来前行的航标开始清晰,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
[编辑 陈建光]
E-mail:chinacbr@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