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寻找文明的坐标
2007-05-30熊培云
熊培云
2007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中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显而易见,在“一切文明成果”中,除了自由、民主等价值外,分立的产权制度同样是转型期中国亟需吸收和借鉴的文明成果。尽管《物权法》曾经因为导致“建国以来第三次意识形态大讨论”而“暂时搁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从2004年“私产入宪”到《民法典》的即将出台,中国正在寻找新的坐标与起点,重新定义和丰富自己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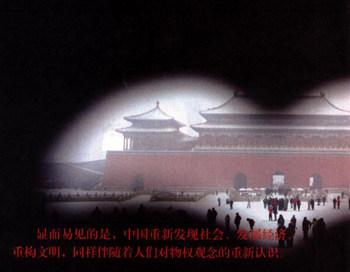
拆迁,中国文明的隐痛
近年来,面对四处风起云涌的“拆迁运动”,有中国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如此“原音重现”虽有夸张、戏谑之嫌,但它无可怀疑地触及了埋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隐痛。
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祖宗文明”雄视天下,时而扬言“祖宗之法不可变”。然而,当我们仔细检点自己的历史时,发现真正支配中国历史走向的却是“拆迁律”——这既包括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拆迁”,也包括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创造物的拆迁。前者表现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王朝建立往往伴随着对旧王朝的全盘否定,而后者更常见于日常生活中的拆房毁屋。二者相同之处都是以“改天换地”的名义,“先拆迁、后安置”。
心理学家认为扳机会带动手指,人的破坏力会被引诱。中国人也时常将前辈摧折建筑的纵火豪情归咎于木质结构,仿佛烧得活该。尽管如此,中国人不注重本土文化保护是显而易见的。走在巴黎或欧洲其他一些地方的中世纪小城里,无处不在的文明遗迹及建筑群落会让你有穿越千年时光的惊喜与从容,然而,在更为古老的中国,映入我们眼帘的却只是几个孤零零的牌坊或高塔,就像一个单位毁灭了,只留下一个雕着花纹的传达室。
文明,作为“人之造物”被人赋予生命。今天的钢筋水泥同样没有阻挡中国建筑“短命”的颓运。2007年1月6日,随着几声闷响,有着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爆破拆除。据了解,该大楼为国内第一高度“框筒楼”,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该楼至少可以使用100年。然而,到被爆破拆除时,仅仅使用了13年。
“短命建筑”告诉我们什么是“拆迁文明”。就在不久前,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同样瘫倒在一片瓦砾之中。几包炸药的功夫,这个曾经见证过中国足球成长的体育场变成了“美丽的传说”——有人开玩笑说,这一天中国足球遭遇了“9·11”。
诚然,今日中国政治安定、社会平稳发展,少有“恐怖分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和平年代里处处充满硝烟。电视新闻与报纸头版最抢眼的莫过于某某城市又搞了“××第一爆”。“第一爆”的美名与噱头让不少媒体与官员面露喜色。很难理解,在这些创造物灰飞烟灭之际,拍板点火者竟然没有丝毫的疼惜与仁慈。“拆迁文化”为我们展示的时代悖论是:人们一边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击掌欢呼,一边为“和平坍陷”幽灵不散扼腕叹息。就这样,“拆迁”日复一日地腐蚀着文明的根基,朝不保夕的创造就像是在同一平面上铺砖,不会增加一个文明的任何高度——正如互相抢劫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
中国人不知珍视本国历史与创造么?这并不是真相的全部。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近年来伴随着房地产暴利水涨船高的拆迁纠纷中,为什么有民众以死相搏仍不能保全自己的房屋。事实上,正是这种“有心无力”使人们将“拆迁文化”与“和平塌陷”的症结投向了分立的产权制度,使文明忧思转向权利建设。
革命时期的物权
如何毁灭一座城市?两种广为人知的方法:一是轰炸,二是消灭这个城市的产权。当这座城市名义上属于任何人实际又不属于任何人时,必然会在一片混乱中上演“公地悲剧”,芳草萋萋的牧场在人们粗暴、短见的放牧中失去生机,寸草不生。
承认个体的物权,归根到底就是承认个体自治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秩序,缔结坚实的社会之网,借此抵达更高的富庶与文明。照休谟的理解:“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标志着文明的开始。”
显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时,财产分立不过是种奢望,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命都保不住,遑论财产?同样,在国家吞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国土”的时代,这种保护同样因为缺乏道德与法律上的合法性无从谈起。
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既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参照。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这样概括罗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持久的征服。”李约瑟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物权的丧失,被王权与神权霸占,抑制了个人的创造,终于欧洲经济千年等(停滞)一回。归根结底,个体对物权的占有程度,决定了罗马的中兴与败落。
和雅典的民主一样,罗马的物权观念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影响深远,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同样迎来“罗马法复兴运动”。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谈到世界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革命时,人们多谈“自由”、“民主”,至于大革命对个人财产权的肯定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与忽略:1689年脱胎于“光荣革命”的《权利法案》与紧随其后的《王位继承法》确立了英国“议会至上”的原则,同时强化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带来的《独立宣言》将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生命权视为同等重要;同样,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将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这种权利都不得剥夺”写进了《人权宣言》。如果说自由、民主等价值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种高度,那么对个体物权的肯定则让这种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沦落为凌空蹈虚的理想,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
以物权发育社会
在西方,民法被概括为“社会生活的圣经”,是“公民、法人的权利宣言”。市场经济,就是靠这本“圣经”来调整。近些年来,强行征地、拆迁导致纠纷甚至自焚抗议事件偶有发生,它表明部分无序与野蛮的拆迁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05年11月,西安市唐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王永举在办完小区新老物业公司的交接工作后,在小区内被一群男子用刀砍成重伤,左手3个手指被砍断。这已是他组织业主开始维权后第二次遭遇袭击。对此现象,有政协委员感慨:“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小区,竟然变成了‘战场。”
谈到《物权法》与《民法典》的制订,有法学家感慨:现在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有民法典,然而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中国至今没有民法典,现行《民法通则》亦不过是156个条文,而在200多年前,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就有1000多页。新中国建国50余年,至今没有《民法典》,足见国家立法工作的严重滞后性。
人不能活在理想的真空之中,物权是人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个体物权,不会有持久的创造,也不会有真正的人权。显而易见,今日中国不断收获希望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承认个体的人生所得,而中国历史上的积贫积弱同样在于个体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以至于每个人的创造性及创造物消失于时代的风雨飘摇之中。
人类的公序良俗是在个人充分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成。文明的演进同样是财富与创造不断累积、完成历史增量的过程。这种累积,简而言之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了获得这种胜利,人们必须步步为营,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获取人生的收益。试想,一个农民在老家盖了间房屋后到城里又赚了间房,倘使村长以“公共利益”为由拆去了农民乡下的房子,我们就不能說这个农民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为他的后院起了“州官之火”。
个体如此,社会亦如此。只有财产权受到严格保护,一个文明才会拥有真正的前途。否则,一切创造都会在顾此失彼中灰飞烟灭。如果我们承认个体的创造是一个社会赖以进步的源泉,就必须承认保护个体物权就是保护文明宫殿的墙脚。
人们常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没有意义。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无疑是个体自治的关键。和思想国有化一样,财产国有化使个体自治如同镜花水月。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发展经济、重构文明,同样伴随着人们对物权观念的重新认识。
作为权利启蒙的物权
约翰·洛克说,没有个人物权的地方也就没有公正,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亨利·梅因认为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制又自称看重文明。在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早已深入人心,以对抗专制王权。与此相反,中国虽然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人间指南”,但是,自古以来,卧拥后宫、坐拥天下的天子并没有赋予平民保卫自己财产、对抗国王的权利。人们不会忘记,甚至到了几十年前,中国仍有“抄家”流行。

在此历史背景下,《物权法》的规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权利保障法、财产保障法,它更是一部转变社会观念、重塑文化心理、再造政治文明的法律。
不绝于耳的拆迁纠纷以由《物权法》立法引起的激烈讨论,相信许多人对西方“平民对抗国王权威”的“维权经典”已不再陌生。
第一个经典是“波茨坦磨坊”故事。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在波茨坦建造行宫,强行拆掉了一座并不属于他的旧磨坊,被磨坊主告上法庭。最后,法院一致裁定威廉一世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责成在原址立即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并支付赔偿。第二个经典则是18世纪中叶英国老首相威廉·皮特的一段著名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進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同样有句经典台词——“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获得另一种理解:物权制度就是要形成一个坚硬的果壳,使身处其中的种子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并且可以与来自外界的侵害进行有希望的对抗。坚硬的果壳里不仅有着无限的空间和时间,同样可以让有力量的种子适时而出,完成自己的创造与繁衍。在此意义上,受法律保护的分立的物权就像坚硬的果壳一般为每个公民建起坚硬的房屋,使他们可以各居其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共和国。
未解之题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近年来,除了调而难控、居高不下的房价之外,人们同样将讨论焦点集中在土地所有权上面。在过去的文章中,笔者曾经以“型”字的构词法设喻,指明中国“转型”就是“拿土地开刀”。中国的社会解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让每个公民在精神和物质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然而,具体到现实中的土地,身处转型期的中国人同样需要面对一个“不动产悖论”。以私人住宅为例,1990年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住宅土地最高使用年限做了70年的规定,即今天说的“70年大限”。从法理上讲,不动产的特点是它与土地不能分离或者不可移动,一旦与土地分离或者移动将改变其性质或者大大降低其价值。与此同时,使用他人的土地建筑住宅的权利属于地上权,是限制物权而非完整物权。
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动产悖论”是:如果我们把土地比作皮,把房屋比作毛,如果土地不属于民众,就必须承认房屋在这里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不动产”。当大地沉睡之时,房屋与土地相安无事,然而,假如土地做噩梦踢被子,那么这些不安定的抖动对于房屋主人来说都可能是一场“产权地震”,而这些名义上的“不动产”就像趴在床单上的虱子,随时会被抖落下来。正因为此,有人指出住宅土地使用年限不超过70年的规定,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购房者头顶,且不利于提高住房建筑质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关物权观念的再认识与公开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今日中国的开放程度。从没有民法到1986年通过《民法通则》及其后《合同法》等单行法的出台,再到近些年来《物权法》和《民法典》引起的争议与关注,不难发现,“为生活立法”、为可持续的、有保障的幸福立法已经成为“中国共识”,这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人们重建秩序与文明的渴望,同样反映了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高度。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应该说,这句话同样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走出“王”、“国”体制的社会人来说,对个体物权的肯定,就是对个体价值与个体创造的肯定。种种挫折与努力,更意味着今日中国人正在重新寻找文明的坐标,期待有朝一日,连接时间、空间与人的三维,见证文明钉头粼粼,大地繁花四起,人人因创造而得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