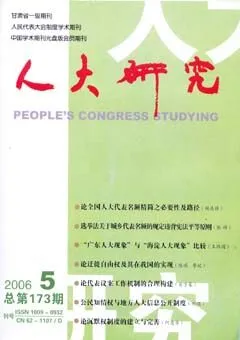公民知情权与地方人大信息公开制度
2006-12-29刘煜
人大研究 2006年5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因此,探讨公民知情权与地方人大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情权的提出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兴起
“知情权”一词来自英文“righttoknow”。“知情权”也称“人民的知情权”(people’srighttoknow)或“公众知情权”(public’srighttoknow)。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知悉权”、“情报权”或“信息权”。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是指公民有权了解社会诸活动的权利,它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要求。
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是相伴而随的。早在18世纪,瑞典就在其《新闻(自由)法》中,提出官方文件应向人民公开,这被认为是“公开原则”的最早表述[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鉴于法西斯主义一度猖獗的原因,认识到要防止当权者违背民意、滥用权力,就应将有关政府工作情况的信息及时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情。由此开始了对“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思考。1955年,美国新闻界著名人士、美联社主编肯特·库珀率先明确提出“知情权”这一概念,并在美国新闻界发起、推动、倡导了一场“知情权”的“自由信息”运动,影响和震动了美国的法学界。尤其是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通过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追求“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潮流。据统计,至2002年,世界上已有近50个国家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2]。即使在尚未制定颁布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也随着世界潮流,对“知情权”和信息公开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知情权”这一明确提法在我国虽然是近年来才被广泛使用,但对“公开发布信息”和“公开报道”的表述早就散见于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法规性文件中。早在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州救灾的内部参考资料后,就曾在有关批示中指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3]毛泽东的批示,不仅下达了公开的指示,而且指出了“公开”可以“唤起人民全力抗争”的作用。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务院曾两次公布法规性文件,规定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有关政府事务的公告和公告性新闻。在司法领域,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文献,都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都提出了政务要“公开、透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党的一个根本目标任务提了出来。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指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要“完善公开办事制度”,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情权”这一概念。尤其是2001年底发生的“非典”疫情危机,更进一步使公民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2002年广州、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重庆、武汉等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都体现了权利原则,并都指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知政府信息,政府都负有向公民或组织公开其信息的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各地各部门也都相继制定了一些信息公开的相关措施,特别是“村务公开”、“警务公开”和“检务公开”的推行以及人大信息公开的探索,促进了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公民知情知政的渠道。
二、公民知情权与人大信息公开的法理依据及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不仅蕴含了公民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原则,而且从国家机关的角度为公民知情权的落实设置了具体的实体正义保障。
从宪法和基本法律中可以看出,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委托代理的关系,选民是委托人,人大代表是代理人。二是“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前者是间接行使权力,后者是直接行使权力。但无论是间接地或是直接地行使权力,人民权力的正确行使都必须以各级人大、政府的信息公开和人民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知晓知情为前提。因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增强人大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保证人民对人大职权行为知情,保障人民对人大监督权的实现。
地方人大信息公开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客观体现。人民群众了解知晓自己所选的代表和自己的代言机关以及自己选举产生、任命的官员“在干什么”、“怎么干”以及“干得如何”,既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一个基本标志,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地方人大实行信息公开,有利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实现,真正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精神。
地方人大信息公开,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地方人大通过信息公开,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渠道,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强调要“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也强调指出:要“经常发布政务信息,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这充分说明公共信息公开已经提上我国政府生活的日程。另外,信息公开与普通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非典”危机、矿难事故等充分证明信息公开制度化已势在必行。因此,人大实行信息公开,有利于带动和促进甚或是监督“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化,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
地方人大信息公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公众的正确理解并积极参与。公众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和谐社会构建目标实现的进程。事实证明,公众参与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社会氛围就越和谐[4]。地方人大信息公开,扩大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为人民群众广泛而有序参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更乐意通过人大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较少地采用或不用非法的甚或是付出极大代价的极端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的实现,进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信息公开制度的路径选择
目前,一些地方人大,特别是很多市、县级人大对政务信息公开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基层人大信息公开缺失(许多地方人大尤其是县级人大一般仅有一年一度人代会的公开报道),而且即便已进行“公开”的地方,也存在着随意性和制度缺陷。如只公布结果、不公开过程,只公开人代会、不公开常委会会议与主任会议等。列宁说过:“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是建设由群众自下而上管理国家的具体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与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作用。”[5]为此,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地方人大信息公开缺失以及随意性大、缺乏制度保障等现状,满足人民对人大职权行为的知情要求,实现人民对人大的监督权,惟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信息公开,且这种公开不仅是行权结果的公开,还应包括行权过程的公开。信息公开制度化,一是要尽快制定出台《政务信息公开法》;二是要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前者没有解决之前,只有从加强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其路径是:
(一)建立和完善会议公开制度
举行会议是人大行使职权最主要的方式。因此,建立和完善会议公开制度,将人大运用权力的过程完全置于“阳光”下,才能保证人民知情权的实现。
1.通过新闻媒体全程公开直播报道“三会”(人代会、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目前,地方人大会议大多只报道人代会、常委会会议,对主任会议的报道几乎是“空白”,且电视报道也都是录播、转播,根本未进行直播,对媒体的开放也是有限的,允许采访的媒体也是特定的。当然,直播也好,全程开放也罢,都需要成本,但是,为了真正的民主,为了人民知情权的实现,付出必要的“成本”是应该的。正如彭真同志所说:“民主就不能怕麻烦”[6]。目前报纸和电视已成为公民获取国家政治领域信息的两大主要渠道。通过电视、电台、报纸全程直播报道“三会”,能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策、议事的公开透明度,便于人民群众普遍、直接地了解人大行使职权的全过程及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
2.通过互联网,对“三会”进行视频直播。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直播“三会”,因不占用电视频道,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更加便利。人们静坐家中就可“参加”人大会议。它不仅突破地域、人数、年龄的限制,而且可以随时开通,即时互动,更有利于保障民权、集中民智、表达民意。
(二)建立健全公民旁听制
建立健全公民旁听制,有利于加深人民群众对人大的了解,强化社会的人大意识;有利于拓宽民主渠道,加强人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提高人大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作用;有利于增强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责任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目前尽管许多地方人大对“公民旁听”已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但对“公民旁听”尚未制度化、规范化;况且许多地方,特别是市、县级人大对公民“旁听”仍未敞开大门,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公民旁听制,同时,公民不仅可以旁听,而且可以旁言,仅“听”不能“旁言”不利于意见的表达,就达不到旁听的目的。旁听的内容可以是“三会”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专题会议。旁听人员的年龄也可以放宽到16周岁,这有利于对青少年进行人大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强化其人大意识。同时除允许我国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旁听外,还可以适当允许外国公民参加旁听。因为允许本国公民旁听,是尊重其知情权,让其直接参与民主;适当允许外国人旁听,使其见证我们的民主,对招商引资、文化交流、人权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健全听证制
建立地方立法听证制有利于充分反映社情民意,有利于立法机关更深入广泛地了解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热情,增强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通过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质量,防止立法的偏颇和缺失,使之更科学、更民主,同时更利于地方性法规的顺利执行。建立健全立法听证制度,一方面体现出人大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在“开门”立法中感受实实在在的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民主。在地方立法听证中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遴选听证陈述人要注意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人数的合理性,以体现利益均衡原则;二是要防止听证流于形式,避免“听而不证”,切忌把听证陈述人的意见等同于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
(四)建立健全常委会新闻发布制度
目前,许多地方党委政府纷纷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并定期向民众和社会各界通报工作情况和重大事项。这是我国政治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有必要及时将履职情况及常委会的有关重要议题和工作情况向人民公布,使其知晓,听其意见。这样做,既尊重了人民的知情权,也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因此,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都应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布不能仅限于人代会期间进行,对于常规性工作也应定期向社会发布,对于临时性工作和事项也可以随机召开新闻发布会。
(五)建立和完善代表候选人和拟任命人员的宣誓承诺公示制度
建立宣誓承诺制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有助于维护宪法至上的权威,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地方各级人大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因为通过宣誓,可以激发人大代表候选人和拟任命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其“主权在民”意识,使其深知当选任命后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同时,通过现场当众宣誓承诺,并通过电视转播公示,有利于选区选民日后用其宣誓承诺之辞对照、监督、评议甚或是质询人大代表和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因此,地方各级人大建立健全代表候选人和拟任命人员的宣誓承诺公示制度很有必要。
(六)建立健全人大代表与选民、选区的联系制度
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的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理所当然要与选民、选区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人大代表与选民、选区的联系制度,主要方式有:一是建立代表公示制,即将人大代表的照片、姓名、单位、邮编、联系电话、代表的权利及义务向选区选民进行公布,便于选民联系代表和监督代表;二是代表应经常深入选区、选民进行走访调研,以起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作用;三是建立代表向选民、选区述职制度。
(七)加强地方人大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地方人大网站
建立人大网站,就是架设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新桥梁,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通过人大网站,一方面使人民群众获取人大信息的可靠性、系统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也使人大常委会更加及时快捷地获得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减少了中间环节和层层过滤造成的失真。因此,各级地方人大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地方人大网站。一是要建立健全人大信息综合网,全面介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动态信息。二是建立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的个人公开网站,一方面向公众公开人大代表的个人信息和履职情况以让人民知情,另一方面通过电子邮件信箱,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向代表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人大代表直接听取社会公众的陈述,了解社会公众的建议,强化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形成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设立电子论坛(BBS)。通过电子论坛,人们可以贴“帖子”,发表观点,展开双向多层交流、讨论,表达权利。四是开设“主任信箱”、“群众来信”、“建言献策”、“要求督办”、“批评建议”、“揭发举报”、“申诉投诉”、“法律咨询”等电子邮箱,使人大网站成为“电子监督站”,使人大监督工作更加透明、更加民主、更加公正。五是建立CIO(首席信息官)制度,设立地方人大CIO,落实专人,固定职位和专项经费,确保人大政务信息的公开。
(八)建立人大常委会档案、文件公开制度
把无需保密的文件,包括会议记录等定期向社会公开,供公众查询。
注释:
[1]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孙国东:《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概览》,http://www.bokee.com/new/display/46495.html。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14页。
[4]谢涛:《“和谐社会”需要构建多元的利益诉求机制》,《学习时报》第124期。
[5]《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
[6]秦醒民:《感悟与启迪——浅议彭真同志关于立法工作的精辟论述》,载《中国人大》2005年第17期,第29页。
(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