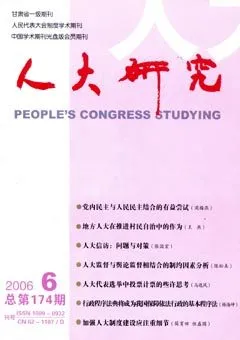禁止“网络语汇”凸显地方立法六大缺陷
2006-12-29朱中一
人大研究 2006年6期
2005年12月29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国家机关公文应当符合国家关于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的规范和标准。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除上海市外,我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立法中,均未出现对“网络语汇”的禁止性规定,上海市的这一规定,确有“标新立异”之处。由于对目前已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些网络词汇的使用进行了限制,该条规定非常引人注目,也招来不少的批评与反对。有人以激烈的言辞指出,这种规定是19世纪的语言“规定主义”、“纯语主义”在中国大都市的“阴魂不散”[1]。而笔者则认为,这个条款无非是一个缩影,其背后表现着我国目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诸多缺陷。
一、在执行性立法中随意加入创制性条款
作为国家标准,《汉语信息处理词汇01部分:基本术语》分别对语言、文字、词、词汇等给出定义。语言是指为了传递信息而使用的一组字符、约定和规则。文字是指人类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词是指最小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词汇是指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和固定词组的集合。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办法》中的“语汇”一词,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种语言的或一个人所用的词和固定的词组的总和”。可见,“语汇”实质上就是词和词组,它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使用的“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词可以由一个字组成,也可以由几个字组成。“字”≠“词”,这个道理应该是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其立法作用是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很明显,该法规定只针对字,而不针对词;只推行规范汉字,而不推行“规范汉语词汇”,其范围和界限是十分明确的。
从标题以及《办法》第一条的规定来看,《办法》属于执行性立法。执行性立法必须将其内容严格地限定在它所要执行的法律的内容之中,而不得设定新的权利、义务规范。但是,《办法》对于网络语汇使用的禁止超出了《办法》所要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范围,其性质是在执行性立法中出现的创制性立法条款。这是违反一般的立法原则的。
二、对非地方性事务进行创制性立法
假如该条款并不是处于一部执行性立法,单就该条款的内容而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就此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呢?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地方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只能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也就是说,地方进行创制性立法,只能针对“地方性事务”。那么,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使用的语言文字,是否属于地方性事务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原因是语言文字使用的主体无法被限定在地方范围之内。国家机关公文的制作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在上海市范围内使用的国家机关公文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的公文,上海市各级国家机关只是这些国家机关中的一部分。这里面不仅包括在上海市以外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在上海市范围内可以被使用;还包括在上海市内一些属于中央直接管辖的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同样如此。这个法规是否可以针对在上海市的驻军制作的公文?是否可以针对法律出版社制作的教科书?是否可以针对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新闻报道?
三、立法用词含义模糊
“网络语汇”一词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就是“网络”二字。“网络语汇”究竟是指被网络使用的语汇?还是指起源于网络的语汇?事实上,无论持哪一种理解,这个概念都是很难准确定义的。
由于目前网络已经非常发达,网络的使用也极为频繁,网络已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虚拟世界。可以推断,所有的汉语词汇都在网络中被使用和发布。如果认为“网络语汇”是指被网络使用的语汇,那么几乎所有的汉语词汇都应被认定为网络词汇。很显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绝不可能想去禁止使用全部汉语词汇。他们所想禁止的是那种“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词汇而已。假如是这个意思,那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就根本无需使用“网络语汇”一词,将“网络”二字去掉,仍能准确反映其立法原意。而在立法中出现“网络”二字,除了使立法用词含义模糊之外,更反映出立法者对网络的“歧视”或者“恐惧”。
将“网络语汇”理解成源自于网络的语汇,同样难以进行判断。究竟由谁,在何时创造了某个词汇,这个确认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在有关“网络语汇”的宣传报道中,“美眉”、“恐龙”、“PK”之类的词,似乎被“确定”为“网络语汇”的代表,但实际上,这种“确定”充其量只能被称为“假定”、“推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调查,举出证据来说,这些词汇就是源于网络呢?
四、立法出现禁止性规定,但不事先公布判断标准
立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构成人们的不作为义务。假如该禁止事项的用语按照语言规则,无法被非常准确地界定,容易产生歧义的话,人们将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准确预期。因此,如果立法中包含对某种行为的禁止,立法机关就有义务在立法中或者授权某个国家机关在法律生效以前或同时提供该种行为的判断标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配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就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中并不包括有关“语汇”的标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至今也未颁布地方标准来界定“网络语汇”。在此状态下,执法权力将是恣意的,因为执法机关可以对“网络语汇”进行任意的扩张性解释。
五、立法不认真对待民意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是立法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本身就是民意的代表机构。同时,地方人大进行立法时,可以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的有关规定广泛地搜集民意。《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也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对于设置普遍性禁止的事项,尤其应充分地、认真地听取人民的意见。从各类媒体的评论来看,对禁止“网络语汇”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就评论的内容来看,反对观点措辞激烈强硬,显示出强烈的“偏好”。既然尚存在如此广泛和强烈的反对意见,为什么还要强行立法?
六、立法不考虑可操作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之所以不对词汇设定国家标准是合理的。国家可以为符号设定统一的标准,帮助人们认字,方便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但人们如何理解这些符号的组合却属于纯粹思想领域的事项,国家既不可能全面了解,也根本无法强制。人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创造新词;也可以为已有词汇赋予新的含义。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极强的变动性,任何政府和组织都没有能力去左右语言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禁止“网络语汇”,实际上就是要政府去办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同时,由于前面提到的用语定义模糊的原因,执法者在具体操作时也将面临困境。究竟哪些是“网络语汇”?立法者既没有告诉人民,也没有告诉执法者。是不是要参照词典来操作呢?哪本词典才是“权威”词典呢?
注释:
[1]见《谁有权利禁止语言?——评两篇有关上海语言文字地方立法的报道》一文,见上海语言文字网论坛。
(作者系苏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