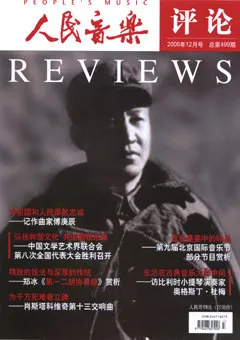评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
2006-12-29柯沁夫
人民音乐 2006年12期
8月的鄂尔多斯高原,秋高气爽,壮美如画。历时一周的“中国·内蒙古第三届国际草原文化节暨首届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首先在神圣的成吉思汗陵园隆重拉开帷幕。8月9日,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音乐会在东胜市“鄂尔多斯恰特”举行首场演出。音乐会由年过古稀的作曲家兼指挥家永儒布先生亲自执棒,享誉于国际合唱乐坛的内蒙古广播电视合唱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来自首都的亚洲爱乐交响乐团和自治区首府的内蒙古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内蒙古民族乐团共200余名音乐表演艺术家同台献艺,共同演绎内蒙古有史以来第一部用交响音乐手法写的大合唱,真可谓强强联合,技艺精湛,盛况空前。
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是永儒布新近根据诗人晨光诗集《啊,草原》的原诗而谱写完成的力作。作品热情讴歌了21世纪内蒙古草原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勃勃生机,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内蒙古草原的现代风貌和神韵。笔者认为,这部合唱不但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时代性,而且具有传统与现代技法交融的高度艺术性,风格浓郁而丰富的鲜明民族性,从而达到了诗与音乐的高度谐和,声乐与乐队的交响融合,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深刻思想内容的强烈时代性
永儒布是一位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以“抒发民族心声”为己任的蒙古族作曲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内蒙古草原的飞速发展、巨大变迁,无时不在激荡着作曲家的胸怀,尤其是在建设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之后,作曲家更是兴奋不已。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由衷地说:“我认为内蒙古草原的今天,已步入了有史以来最和谐安康、最繁荣幸福的时代。作为蒙古族作曲家,我有责任以不同的音乐体裁形式把这一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出来。”也许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他几乎搁置起自己的创作强项——交响音乐的写作计划,而把精力主要投放到声乐的各种体裁(抒情歌曲、不同组合的重唱、无伴奏合唱、大型混声合唱等)创作之中,连续谱写出《草原迎宾曲》《四海》《青春内蒙古》《内蒙古礼赞》《彩云从草原上飘过》《春天啊,永远属于我们》《草原新绿》……等一系列展示和讴歌内蒙古草原风貌的优秀声乐作品。在内蒙古自治区60周年“大庆”即将到来之际,有机会拜读了诗人晨光的诗集,立即为诗集中的绚丽多姿的诗情画意所吸引,并为这位汉族诗人的炽热情怀所感动。于是,他从诗集中挑选出9首具有代表性的短诗,满怀激情地“奋笔疾书”,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九个乐章交响合唱的全部创作。那气势恢宏、雄伟壮丽、富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浓烈现代生活气息的音乐,更增加了原诗的强烈时代感——它既不属于20世纪中叶共和国初生的时代,也不属于20世纪下叶改革开放的初期,而是属于那充满无限生机、蕴藏巨大潜力的21世纪的内蒙古草原。
连续三场的演出成功,雄辩地证明了《草原颂》确实是歌颂新时代草原的一部音乐力作。
珠联璧合的高度艺术性
诗与音乐珠圆玉润,相映成辉。首先,是诗情决定了音乐。诗人多角度描绘出的那种苍茫辽远、博大雄浑、粗犷奔放、深沉激越、宁静安谧、天人合一、慈爱善良、灵动浪漫、刚毅挺拔、壮丽崇高的草原自然美和神韵美,深深撞击了作曲家的心灵,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同时也为作曲家提供了才思驰骋、技法发挥的广阔空间。其次,是作曲家的丰富的乐思、娴熟的音乐技法,深化了原诗的题材内容、诗情画意和诗人的才思豪情。无论音乐主题、旋律音调、节拍节奏、和声复调,还是调式调性布局、速度变化、力度对比,以及合唱音色的选择、配器色彩的调动,都与诗情紧密相连,自然结合,从而使诗歌的诗情神韵得到升华、达到了诗歌与音乐高度的完美结合,所以可以说这部多乐章的大型合唱——既是诗的音乐,又是音乐的诗。以《草原颂》各乐章的基调为例,作曲家除着意表现诗人所描绘的意境之外,更注意诗人总体思绪情感的准确把握并予以创造性发挥,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出神入化和雄浑宏伟、壮美崇高的艺术境界,不仅使人心潮翻涌,振奋激越,而且使人遐想无限、感悟至深。如第一乐章男女高音领唱与混声合唱《走进草原》,不仅有对草原苍茫雄伟的咏诵,还有深爱的挚诚与陶醉,令人赞叹;第二乐章男声领唱与无伴奏合唱《天堂草原》既有“天人合一”之美,又有悠然惬意之情,令人神往;第三乐章混声合唱《蒙古高原》着意表现草原的雄浑壮美,却自然流淌出情不自禁的豪迈,令人抒怀;第四乐章女中音领唱与混声合唱《草原母亲》既宽厚博大,又深情柔美,令人眷恋;第五乐章混声合唱《草原的风》的欢快疾迅中显露勃勃生机,催人奋进;第六乐章男声合唱《父亲的草原》的稳健深沉中蕴藏着刚毅坚强,令人自信;第七乐章混声合唱《草原的舞》既热情欢快又粗犷豪放,令人鼓舞;如果说在第八乐章女声二重唱与合唱《草原之夜》中,作曲家主要根据诗情着意于幽静、安谧、恬美意境的描绘,从而达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效果;而在第九乐章女高音领唱与混声合唱《奔向明天》中,则是作曲家浓墨重彩地抒发了对明天草原腾飞的热切期望和对草原人民英姿勃发的由衷赞颂,音乐辉煌壮丽、恢宏激越,从而达到了全曲的高潮。
声乐与乐队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以往我国、尤其是内蒙古的多声部的大型合唱,由于时代条件等多方面原因所限,更多的带有群众性合唱特征,乐队往往只起着跟随旋律、烘托气氛的伴奏作用。而《草原颂》的交响乐队却不仅仅是烘托式的伴奏,它是直接参与合唱音乐的形象塑造、意境描绘、情感抒发,起着深化主题、升华诗情画意作用的,从而使乐队与声乐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显然,这与作曲家运用了交响音乐手法不无关系。其一,作曲家运用了交响音乐的主导主题和动机手法。首先,《草原颂》的主导音乐主题——“草原”,突出而鲜明,并贯穿于全曲各乐章之中。如开篇混声合唱《走进草原》,开门见山,直接凸现出这一简洁宽广、开放性很强的主题旋律。而在各乐章之中,“草原”主题则依据不同的诗情画意,通过旋律变奏,以及节拍节奏、速度力度、配器色彩的不断变化,予以呈现、延伸和发展。或苍茫辽阔、宏伟壮丽,或深沉博大、坚毅豪迈,或柔情似水、飘逸如云,或轻盈跳跃、欢快活泼,或热情似火、豪爽奔放,或英姿勃发、奋进激越……,从而使九个乐章的合唱达到自然而和谐的统一。此外带有装饰音和颤音的“舞蹈”动机,轻盈活泼、俏皮风趣,分别运用在第五乐章《草原的风》和第七乐章《草原的舞》中,不仅起了深化诗意,强化气氛的作用,而且前后呼应,情趣盎然,很富有色彩和动力。其二,在整部《草原颂》中,乐队与声乐共同抒发情感或乐队单独描绘意境的手法俯拾皆是,如:仅一个乐句的“草原”主导主题,开篇之时就连续咏唱12次之多,除了不同声种与各声部组合的不断变化和力度层次的变幻之外,更多是借助于交响乐队配器色彩的丰富变化,使诗人和作曲家对草原的炽热咏叹抒发得淋漓尽致。第二乐章《天堂草原》由不完全再现的ABA三部曲式构成。简短的“草原”主题引子与反复出现5次的A段“天堂”第一主题,近30小节,全部由乐队演奏。其中,善于描写田园风光的各种木管乐器、善于描绘神幻仙境的长笛、竖琴、三角铁等乐器,以及长于柔情陈述的马头琴、大提琴、小提琴等弦乐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或领奏、或衬腔式与背景式轻柔缥缈地伴奏,如诗如画地描绘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人合一”境界,成就了一段纯器乐的交响音画。B段,男声领唱重复一遍“天堂”第一主题后,立即扩充延伸为由合唱轻声进入的“天堂”第二主题。而经过简短的A段不完全(仅5小节)再现后,又由乐队奏出轻柔的“草原”主题的尾奏,与引子首尾呼应,使《天堂草原》这首合唱犹如一幅镶着金框的天堂草原风景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第六乐章《父亲的草原》序奏中,作曲家首先用铃鼓节奏、大管顿音、贝司拨弦等演奏技法构成简洁而形象的“马步”动机,相继引入圆号、木管旋律,几笔就勾勒出在广袤的草原上,一队骑在马背上的牧民由远而近、引缆徐行、沉着稳健、引吭抒怀的生动意象。而在歌声进入之后,“马步”动机一直作为背景贯穿全曲……。其三,作曲家广泛运用和调动了大型合唱的各种戏剧性手法,如鲜明的速度对比,大幅度的力度对比,各种人声和乐器的纯音色的对比,多种混合音色的组合对比,乐队和人声雄浑的交响与无伴奏纯人声的清唱对比,以及复调与和声织体的纵横交错的对比,丰富而精细配器色彩的鲜明对比,“巧夺天工”的转调、移调、离调、复调性、多调性自然无痕的对比,以及多种地域的音乐色彩风格对比……等,使整部合唱色彩斑斓、变幻莫测、绚丽迷人,从而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
多元色彩与统一风格的鲜明民族性
蒙古民族是人类史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方国、部落、汗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不同时期的分封割据,以及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俗风情、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不同程度地为现代蒙古族文化留下了地域和部落的烙印。反映在音乐上,就形成了形态不同、色彩各异的鲜明地域风格。这既为蒙古族现代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宝藏,也为作曲家采用多种音乐素材创作大型作品(如交响乐、歌剧、组歌型合唱等)之时带来风格色彩难以协调统一的困难。但在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中,作曲家却以娴熟而高超的表现手法,将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乌拉特、阿拉善等多种色彩迥异的音乐风格,以及乌日汀哆(长调民歌)与包古尼哆(短调民歌)、叙事民歌与抒情民谣、英雄史诗风格的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与有着“博”(即“萨满”)艺术遗痕的“安岱”(民间歌舞)音乐等不同体裁形式的素材,加以有机地引用发展、调配融合,既向听众展现了绚丽多姿的地域色彩,又使整部合唱有着统一的蒙古族风格,同时又赋予了合唱鲜活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达到了多元色彩的展示与统一风格的和谐。反映出作曲家始终坚实扎根于民间音乐的丰沃土壤之中,深谙民族音乐传统和民族审美情趣,不断地挖掘民族音乐语言特征与内涵加以科学提炼,并与西方现代技法巧妙地熔为一炉,从而确保了这一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有丰富的地域色彩又有和谐统一风格的民族特色。
笔者认为,大合唱《草原颂》尽管属于开创性力作,但就交响合唱而言,尚属于探索性作品。其中,首要问题是各乐章内容的选材与整体形式结构的部署不够严谨,仅从各乐章标题即可窥知一二,如:“走进草原”、“蒙古高原”、“父亲草原”、“母亲草原”等,分曲内容的雷同,必定限制作曲家才思的正常发挥和整体合唱的艺术水平;其次,交响音乐手法不够丰富,因而合唱的整体交响性特征还不够鲜明,蒙古族音乐中特有的经典传统手法(如精美的呼麦复音艺术、恢宏的潮林哆合唱等),本来就具有史诗性特征和交响性潜力,可惜没有得到运用发挥;此外,通听整部合唱,也会有抒情阴柔有余、粗犷阳刚不足之感……由此造成了《草原颂》的某些遗憾。为此,笔者曾向作曲家直抒浅见——如果《草原颂》的体裁形式,不定名为“交响大合唱”,而定名为“大型合唱”或“大型组歌”,是否更为合适?《黄河大合唱》,并没有“交响”二字,孰能否认其“交响性”和艺术价值?笔者真诚希望诗人与作曲家,一鼓作气,更上一层楼,以将这部蒙古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真正运用交响音乐手法写作的大型合唱《草原颂》,打造成“民族文化大区”的顶级音乐精品,成为一部牢固矗立在蒙古族合唱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部草原民族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传世之作。
柯沁夫(李兴武)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