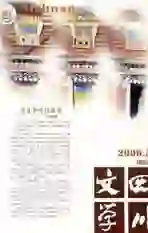乡居
2006-07-21石鸣
石 鸣
“五六月的傍晚,青草很细致似的,整齐地被割去了,有穿了红衣的男孩,戴着小小的笠帽,在左右两胁夹了许多草走去,说不出地让人觉得有意思。”
我不知这“细致”是原文的妙处呢,还是知堂翻译的妙处,它总之实实在在地细致了我遥远的乡居生活,特别是在这盛暑里燠热的正午读到它,仿佛有股清凉之气逸至书页,我被凉爽地舒坦了。
我闭目想起了一些景象,都是乡村的,广阔而充满灵气,它们与我的童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忘记了它们,我的童年是绝对不会宽恕我的,这将使我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整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田园是我的母体,我现在虽然徜徉在大城市中,而那血缘却是深不可没的,在精神上,我是田园的孩子,永久。
如果说这种对田园的依恋仅仅是因为我生于斯而长于斯的话,那显然是简单了。事实上,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乡居只是随父漂流的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那么,我的田园情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五岁左右时随父亲去了乡下。父亲是去做乡村教师。在此之前,父亲是一位山村教师,在北川的深山沟里辛勤地工作着。同“文革”中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父亲选择这样一个边远穷苦的地方,是带着一腔激情去实现他的远大抱负去的。父亲在深山里一呆就是好几年。是母亲的病逝才把父亲唤了回来。母亲因某种不成熟的手术去世时,我五岁,弟弟两岁,妹妹七个月,这些实际的困境使父亲有了机会被调回来。只是回城已不可能,于是父亲去了近郊的乡村做了乡村教师。
为了对我们有个照顾,我先随父亲去了乡下。我那时还小,母亲的病逝也就没有让我刻骨铭心地伤痛——我前几年曾对我那时的表现深深地自责过,但我现在想通了,对于童年,我们是无权指责的,关键是我们现在是否能记住童年和母亲。换句话说,真正的怀念不是一味地感伤,而是珍惜母亲所给予我们的生命。父亲对此的理解大概要比我们深上十倍。自母亲去世后,父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对我们关怀备至,甚至因为担心后妈对我们不好而彻底打消了再婚的念头。父亲的头脑里并未承袭封建的贞烈观,所以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正是一种深切的怀念,也同时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但说实话,我并不希望这种伟大在所有的父母身上普及,这于他们的生活并不好)。
正因为我不是带着伤痛(父亲却是)来到乡下的,所以我去了后,就高兴地感受乡村的景致和乐趣。
川西的田野,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和景致,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年四季中各各不同的清晨和黄昏。清晨,乡村被鸡鸣唤醒后,炊烟马上就在晨雾中将一座座村庄流动了起来。你一走出去,就会感到是在一条河道上缓缓地漂移——眼前的景致是那样的朦胧美妙,给人一种清新的梦幻感。远一点的一笼笼竹或树,更是楚楚如在水之湄的少女了。间或有一两只或白或黑的狗,在雾气氤氲的田间向你跑来,步履轻盈,也不叫,而田里的幼苗刚好齐了狗的半身,这使它们看上去仿佛一片阔大的荷叶上滚动的露珠。满眼都是朦胧柔和且干净异常的绿,人站在田垄上,就像是一株水稻长在田野里。我那时常有一种种在泥地里的感觉。
比之于晨景,田野的暮色也是不逊情趣的。乡村的黄昏,照例也是由一缕缕炊烟开始的。当炊烟散漫地从农舍先先后后的升起后,空气中便游满了淡淡的青蓝色精灵。乡村的黄昏在感觉上也是静的,虽然它有着不同的吆喝和犬吠。我现在回想起乡村的黄昏的时候,总觉得它有一种宗教归属感的意味,因为它总在把人的灵魂引向宁静。我那时很喜欢在这时刻走出由旧时的关帝庙改造的学校,站到田野间,捕捉空气的味道,看眼前的景致,看许多鸟由一块田飞到另一块田(我很奇怪它们能在稻子上立稳栖息),或是飞到电线上或树林里,热闹地啁啾着,那情景是极为动人的。我前几年写过一组总题为《农田事事》的诗,其中的很多感觉都是由这段生活生出发来的。到了丰收时节,田野里还会生出另一番景象,其一是多了许多稻草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立在田间,扎在手上的破布头迎风飘着,煞有童话意境;其二是村童拿了长长的带叶的树枝,在田野里对着一群群麻雀一阵阵疯撵,把一大群一大群麻雀从这块田赶到另一块田,又从另一块田再赶到另一块田,欢笑声响遍了田野。
我喜欢田野的清晨和黄昏,而村童们其实是喜欢正午的,特别是夏秋的正午。夏天的正午,虽然阳光极为炫目,然而村童们正喜欢这种充足的阳光。各自在家吃了午饭,就泥鳅一般溜出了家门,不一刻便在小河边或水塘边聚积成群了。一个个快捷地脱了衣服后,就将黝黑的身体投进水里去,水面的波光便碎玉琼花一般地荡开来,密匝匝的欢声笑语顷刻间升腾而起,将水面渲染得异常生动。水里折腾累了,又上岸折腾。摔跤、或寻些薄的石子打水漂,看谁的水漂儿打得多、打得远;或有带了狗来的,这时就将狗赶到水里去,看谁家的狗游得快。这样一直将到日头偏西,有了父母隔了几个田远大声地吆喝,或谁家的父亲拿了柳条向这边来了,这才慢慢地或匆匆地抱了衣物回家去。但这种欢娱于我是陌生的,因为父亲并不放心我一个人去,而且他也没时间带我去。
不过夏夜于我倒是极具乐趣的,这便是去捉萤火虫。萤火虫于我有一种神秘感,这固然是因为它能在夜间发出光亮四处游动,更在于我那时对“腐草化为萤”的信以为真。我甚至尝试着拿一只碗泡腐一些谷秸,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些夜间闪亮的灵物来。回想那时候抱着碗里的腐草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的心情,对那种投入,实在是有些恨不再来的遗憾。这行动虽然就科学而言是再愚蠢不过的了,然而就童年对于生活的幻想而言,又是何其美妙的意境啊!我同时也很感谢大人们没在那时告诉我那种等待的虚无,以及并不见怪于我对一碗腐草的期待。我是直到读高中上生物课时,才知到萤火虫和腐草是怎样一种关系的。但我一点儿也没为幼时的无知感到不好意思。生活有很多个点,错误有时在某一个点上,其实是异常美丽的。
萤火虫对我的另一个诱惑,是缘于古人将它捉了放进袋子里做灯用的故事。不过我一直没有那种激动人心的体验,因为我一直没有捉到过足够的萤火虫。
被童年忽略掉,而现在十分渴望拥有的乡居的一个妙处,是它独特的幽静。深远厚重而不死寂的幽静。特别是夏秋的夜晚,你可以就了淡淡的月晕或习习的凉风,搬一张竹椅到树下、竹下或瓜架豆棚下,静静地喝茶,看竹影摇曳、月辉漶漫,受用万物之备;或约来三五好友作一番天地玄谈,既能感受万籁俱静,又能倾听草虫浅吟。间或有惊鸟斜出,若空谷回响,最宜谈诡秘怪诞之事。这样浸在夜里,也不必怕蚊虫扰了静谧,先就将一束艾香草在旁边燃了,既熏走了蚊虫,又清香了夜风,夜空青冥,风凉月静,人夜一体,若有思而无所思,无所思而若有所思,那种自然贴切,就像你是夜空下的一棵树了,颇有庄生之逍遥、尚子之清旷,实在是一种神游于物的诗意的栖息。古人描述的“栽竹数竿,宜春雨,宜冬雪;松两株,宜秋月,宜晚风。……谈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内,急取松下风浇之……”的生活,何其清逸旷达,岂城市能求哉?
乡居的另一个妙处,或许是它能给人以家的稳固感。乡村的博大能消解许多繁杂躁动,乡村的朴实单纯在城市的喧嚣后,也就对灵魂的归宿形成了巨大的磁场。中国的士大夫们向来热爱乡居——喜悦着去或忧伤着去,看一看他们的诗文,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心情或生活的记载。
但我有一个疑问,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是心平气和地走向乡居的呢?“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生活,毕竟和他们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有着巨大的反差啊!这种信仰的颠沛,也许才是最大的痛苦,乡居能将他们抚平么?作为他们最后的领地,乡村能给他们多少安慰呢?
当然,这话说得有些远了。我在这里说乡居,并没把它放在文化层面上,将它作为某种文化现象去进行探讨(虽然那也是一个十分有趣而有意义的话题),它仅仅是因为我想起了过去的一段生活而写下的一些文字。现在再回到开头。所引的这一段文字,出自日本宫廷女侍卫清少纳言之手,我在想,一个久居深宫的女子,她是怎样如此细致地去体验田野的呢?
责任编辑 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