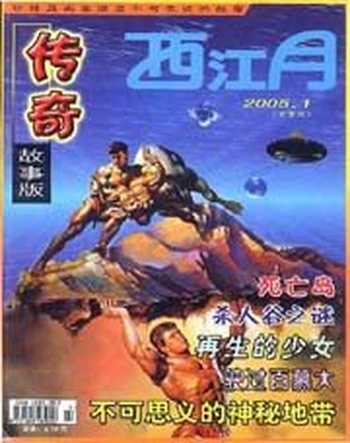绝境中对峙72天
2005-04-29朔夫
朔 夫
[编者语]1973年10月13日,一架从乌拉圭飞往智利的飞机坠毁在安第斯山脉的雪峰上。当时,机上乘坐的是45名乌拉圭橄榄球队队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在茫茫的雪峰上挣扎求生了72个昼夜,最后只有16人生还。奇怪的是,所有的生还者对此次的经历都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于是人们只好把他们奇迹般的生还归结为他们无比的勇气。2003年初,为了纪念飞机坠毁雪峰30周年,乌拉圭国家电视台组织三个尚在人世的当事人重登雪峰。这次,一位名叫坎尼萨的队员终于开口讲述了当年的真实的经历,其中关于绝境中道德与人类动物性本能惨烈斗争的情景令每个人都震憾不已。
意外之灾,飞机撞毁在雪峰上
我是乌拉圭橄榄球队队员。1973年10月13日,我们球队乘专机赴智利打美洲杯联赛。全机共坐了45人,机舱里一片欢笑声,而我的未婚妻安莉娅就坐在我身旁。她依偎在我身边,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眼里全是爱意。
在到达安第斯山上空时,飞机突然剧烈颠簸起来。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久后,飞机的发动机突然停止了转动,飞机开始急速向下跌落。在我们作出反应前,飞机已经接近了安第斯山的雪峰,并一头撞了下去。我听到人们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与机翼折断的声音,接下来便是死一般的宁静。
当我从黑暗中醒来时,周围凄惨的尖叫声仍然此起彼伏。
飞机头、尾部已经断裂,只有中舱一部分尚存。我在附近摸到了一个人,但他没有任何动静,可能已经死了。
当我摸到第三个人时,我听到了呻吟声,那是安莉娅。听到我呼唤她的名字,安莉娅低声哭泣着说:“坎尼萨,我动不了!我的腿痛极了。”
机舱窗透进的微光,让我看到安莉娅的腿被紧紧地夹在了舱壁与变形的座椅之间。我用尽全力将那座椅扳得有些松动,然后抱住安莉娅向外拽。等我将她拽到地板上时发现她的右腿被撞断了,她已经痛得满头大汗。我心疼极了,不断地用亲吻安慰着她。
在清点人数后,我们发现包括8名重伤员在内,共有28个人还活着。我们找到飞机里的急救包,给这些伤员做了紧急处理,然后又将尸体一一拽出葬在一个雪坡上。
我们清点了一下飞机里所剩的食物,发现了不少面包和一大罐葡萄酒,另外,每个人包里都带着一些巧克力与小食品。大家都相信很快就会有救援人员赶到,因此这些食物应该足够了。不过住宿倒成了一件大事。雪峰上白天的温度还能凑合,但夜里的温度竟然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我们只好在天黑后又钻到冰冷的破机舱里,用那些破碎的织物盖在身上取暖。我把座椅皮面扒了下来,盖在安莉娅身上,守在她身边。腿伤的痛楚让安莉娅无法入睡,她整夜都紧紧拽着我的手。当天夜里又有两个重伤员死去了。
我们以为会很快得救,但整整一天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数不清的皑皑雪峰陪伴着我们。在接下来的72天里,我们成了世界的弃儿。后来我们得知,由于这里雪峰林立,飞机不好搜索,而且在雪山与丛林的交界处还坠落了一架与我们同型号的飞机,当局把那架飞机当做是我们的飞机,一直在丛林中寻找,空耗了好些时日。
求生的本能让我们沦丧了道德
第五天过后,飞机上的面包已经所剩不多。人们开始为食物分配的多少爆发争吵。十天后,面包吃完了,饥饿开始威胁人们的生命。也许是意识到我们还要在这绝境中继续呆下去,所有人都开始尽量节省食物,以求度过更漫长的时间。
就在这天,一位名叫菲莎的女孩已经饿昏过去了,她的新婚丈夫是在撞机时死去的,她自己的头部也受了重伤。但是,每个活下来的人只顾着自己,没有人照料她。突然,球队的后卫拉里冲到她的身边,弯腰抢过她的食品袋,将里面的食物向自己口中塞去。他一连抢了几个重伤号身边的食物袋,当我们准备制止他时,他举起一根断铁棍嚎叫着,不让我们靠近,然后从断口处逃了出去,消失在雪峰侧面。我愤怒地要冲出去找他,安莉娅拉住了我,轻轻地说:“让他去吧,反正我们已经挺不过去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我低下了头,吻着安莉娅,心如刀绞
又是两天后,暴风雪来了,我们用破织物挡在机舱破口处,再移上箱子堵住,然后紧紧地挤在一起,相互用身体取暖。我紧紧地抱着安莉娅过了一夜,我生怕她会离我而去。次日,菲莎静静地死去了。当我们将她的尸体移到机舱外时,发现在机舱不远处隆起一个小丘。我们将雪扒开,发现竟然是拉里,他被活活冻死了。我们不知道他不回来找我们是因为被冻得失去了知觉,还是根本没脸再回人群中来。
拉里的死使雪峰上的气氛产生了微妙变化。每个人都对其他人满怀戒备,哪怕是有人无意中经过身边,他们都会下意识捂紧口袋,生怕菲莎的遭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最好的朋友东尼也悄悄地对我说:“伙计,小心点。现在你可是要照顾两个人呢!”
我感激地冲他点点头,心里一阵温暖。我和东尼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志趣相投,亲密无间。这些天来,东尼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帮我照顾安莉娅,还主动地把他带的小薄饼分给我们吃。有他在身边,我总算感到有些安慰。
暴风雪整整肆虐了四天四夜。当天终于放晴时,我们又埋葬了两个饿死的同伴。他们是被活活饿死的啊!哪怕他们身边的人递给他们一小片面包,他们都不至于这样悲惨地死去。但是我没有权利责怪别人,因为我也和他们一样。
埋葬完同伴,我独自在附近的山头走了一圈。这时,前方一个凸起的雪包映入我的眼帘。我扒开雪,竟然看见了一只野山羊。这只山羊已经死去多时,我猜想,它可能是哪只鹰的战利品,被鹰衔到山头准备独自享用,然而还没等鹰吃到嘴,山羊就被漫天的风雪掩埋了。但是不管怎样,望着这只野山羊,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们有救了!”
我连滚带爬地跑回机舱,向大伙宣布了我的消息。人们先是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不知是谁带头,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冲出了机舱,我和东尼也紧跟着跑了过去。当我们到达时,山坡上已经一片混乱。人们互相推搡,破口大骂,最后甚至厮打起来。抢在前面的人迫不及待地用刀割下羊肉,不顾一切塞进嘴里,后面的人则死命地揪着我们的头发往后拖。突然,一个队员和教练打了起来,从他们含混的争吵中,我得知他们争执的原因是考克教练企图拿起一条羊腿。看来安莉娅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生存面前,教练和队员都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像动物一样地厮杀,弱肉强食。
当争夺食物的战斗终于结束后,山坡上又恢复了平静。但是,一些人还在为刚才的争抢耿耿于怀,并对同伴怒目相向,雪峰上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吃完最后一块羊肉后,我瞒着东尼将身上的最后两块巧克力塞进了安莉娅的衣兜里,可她流着泪将巧克力还给我,央求我吃下去。“我不行了,”她说,“你一定要回到乌拉圭,好好地活下去。”我泪眼婆娑地看着她,又将巧克力塞了回去:“不,还是你吃吧。救援很快就会来的,我们一定有办法活下去。”
生死关头我背叛了我的爱人
20多天过去了,安莉娅伤腿已经发黑,而且她的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更麻烦的是,我也开始不停的腹泻,整天头昏眼花。但是我还是一刻不离地守在安莉娅身边,用雪水给她降温,并将巧克力掰成碎屑来喂她。我知道对于一个重病人来说,这点儿食物是远远不够的,但现在,这点儿巧克力非常珍贵了,每当我给安莉娅喂巧克力时,都会有同伴在一旁虎视眈眈,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占有的贪婪目光。但是,我和东尼警告的眼神却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第35天时,大风雪又席卷了雪峰。又有两个同伴静静地死去了,机舱里不停地有人绝望地哭泣。安莉娅已经三天不省人事,一直在说胡话。我揪心般的痛楚,却无计可施。
雪过天晴,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机舱,继续用人肉充饥。回去后,我突然发现转眼的功夫,安莉娅口袋里的巧克力已经不翼而飞。我又惊又怒,大声地问是谁拿走了巧克力。可是大家都低着头,没人敢看我的眼睛。我逐一审视着他们,突然,我发现东尼的嘴里似乎含着什么东西。我猛地冲过去,捏开了他的嘴巴,真的是巧克力!随后,在他的荷包里,我还找到了剩下的小半块巧克力。我一拳将东尼打倒在地,怒斥他的自私,而他则羞愧而绝望地哭泣起来。
经历了这次风波,我将巧克力仔细包好,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吃上一口,但是一想到安莉娅,我又只好咽下了口水。一天晚上,我又一次饿醒了。这时,我无意中摸到了那块巧克力。我再也忍受不了它的诱惑,就掰下了一点放进嘴中。那香滑绵软的味道立刻勾起了我无尽的欲望,我不顾一切地吃了起来,最后,巧克力只剩下了一小块。
第二天早上,当我看到安莉娅沉睡的面庞时,我突然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罪恶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吃掉了她的救命粮,这样的我和我厌恶憎恨的那些人有什么两样!
当天夜里,安莉娅开始发烧了,她一直在昏睡,清醒的时候,就一直用眼睛看着我,目光中满是眷恋。这目光以往曾让我感到温暖,但现在,它却让我无地自容。
在第52天的时候,安莉娅已经耗尽了体内的能量,变得气若游丝。我颤抖着用手将最后一块巧克力喂进了安莉娅嘴里。这时她突然醒过来,深情地望着我,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坎尼萨,我真的不想离开你……可我等不到救援了。你要坚持下去,会有人来救你们的。”她顿了顿,喘了口气说,“我不后悔跟你来,只是我没福气做你的妻子,你知道我多想穿上婚纱做你的新娘啊……”
听到这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安莉娅用手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如果真的没人来救我们,如果你也真的不行了,那你一定要坐在我身边,我要你永远陪着我……”
我哭着扑到她身上,不断地吻着她的脸。但是她的身子渐渐变得冰冷,再也没有气息……
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傻坐在机舱里,呆呆地望着雪峰。每当我想起安莉娅的笑脸,深深的自责和忏悔就会像毒液一样腐蚀我的心。日子仍然在一天天过去,幸存者只剩下16个,而我的心早在安莉娅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死去了。
重回故地,我决定开始新的人生
不知又有多少天过去了,我和同伴们仍然像僵尸一样坐在舱里,没有半点生气。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阵响声,我们突然明白那是飞机的马达声,但我们只是怔怔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考克先回过神来。“飞机!”他激动地喊着,挣扎着钻出了机舱。我们也都跟着出了机舱。一架轻型飞机正在雪峰上盘旋着,驾驶员显然已看到了破碎的机身。人们突然欢呼起来,随后又都呜咽起来。
飞机为我们带来了食品与饮料,人们如饿鬼一样吃喝了起来,但我却没有动。虽然我得救了,可安莉娅却死在了雪峰上。如果我没有吃那些巧克力,如果我能得到伙伴们的帮助,也许安莉娅就能支撑到现在。现在,我只能将安莉娅的尸体用布包好,将她和其他同伴一起埋葬在雪峰上。
我们获救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乌拉圭,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我们的经历,但是我们都默守着雪峰上的秘密,不肯向外界透露我们凭着贪婪、自私、冷酷的动物性本能苟且存活下来的惨烈情景。1974年,有人专门为我们的经历写了一本书,1993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也上映了,可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爱与活力都已经随着安莉娅埋葬在了安第斯山的奎利里卡雪峰上。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妻子儿女,但奎利里卡雪峰的情景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我常常在黑夜里惊醒,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雪峰,又感觉到安莉娅死在我的怀里。我摆脱不了压抑,摆脱不了自责,更摆脱不了梦魇。我开始酗酒吸毒。妻子对我再三规劝,但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她只好离开了我。我再一次陷入了与世隔绝的孤独中。
年初,为了纪念飞机坠毁雪峰30周年,乌拉圭国家电视台找到我和另外两个尚在人世的当事人重登雪峰。当我终于登上海拔13500英尺的奎利里卡雪峰时,30年前的情景再次在我脑海里翻腾起来。我泪流满面地跪在坟墓旁,倾听着雪峰上无边的静寂。我仿佛又听到了安莉娅的声音,“我不能当你的新娘了,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是的,我活下来了,但是此时,我却突然感到羞耻。安莉娅死前曾叮嘱我好好活下去,可我却始终摆脱不了梦魇,不懂得去珍惜自己的生活。我这样又怎么对得起安莉娅纯真的爱情,又怎么能洗涤我心灵的污秽呢?
于是,我默默地跪在坟墓旁立下誓言:我要好好地生活,让安莉娅得到安息。雪峰仍然静寂无声,但是我想,安莉娅一定正在默默地倾听我的诉说,是的,她一定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