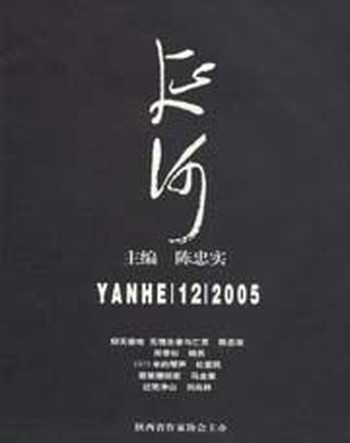感悟甘南
2005-04-29王敏芝
王敏芝
去甘南采风的计划可谓一波三折,从决议到动身有很多变数,但最后形成的团队却天意般的完美。这支不大的队伍由著名摄影师李泛老师带队,成员中有书法家、画家、历史学者、还有从事新闻摄影、技术和影视研究的人士。于是,上天以成人之美之德促成了此次甘南行,我们则以愉快发现之心感受异样地理与文化的双重魅力!
甘南藏族自治州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是一片陌生又美丽的地方,甚至还笼罩着神秘。广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截然不同的人文地理特征和生活方式,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异域后,开心地连表情和语调都与原先不同了,变得比在城市里放松了,不,甚至放肆了……
7月19日,我们经兰州来到了碌曲县的郎木寺。这是我第一次呼吸到清新得带有甘甜味道的空气,第一次看见草原上自由漫步着壮实肥美的牛羊,第一次看见清澈透亮的迎向阳光的溪水,第一次看见滴翠的绿色充盈着整个天地。
晚上,习惯于夜生活的我们还流荡在郎木寺狭小的街道,居然发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比中国游客更多一些,他们几乎都是背包客,聚集在一个木质的阁楼式的小旅馆的名字起得也恰好,就叫“背包客之家”。在黑黢黢的高原中,这里透出的亮光显得很温暖、也很诱人,于是我们也投身其中,立刻被他们的热情感染。“锅庄舞”的舞步并不复杂,我们随着音乐一遍一遍地转着圈儿,窗外偶见一袭藏红的喇嘛或裹着棉袍的藏民经过,再瞧瞧身边的金发碧眼们,这会让你的头脑发生混乱: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
继续驱车南下,两天后我们来到了更让人迷恋的地方——拉卜楞寺,一个很大规模的藏传佛教寺庙,一个对精神生活有无尚追求的地方。
在这里我明白了,精神领域富足的人看起来更安详,因为确信和神在一起的人生总是极具安全感的。每每端详那些或坐于河畔、或行走路上、或半卧于山坡的僧人的面庞,我总想起“平和安详”这个词来。还有无数的信徒,早上天还没亮你就可以看见一群一群的信徒虔诚的转经和叩头。环绕拉卜楞寺一周的长长的转经长廊到底有多长,我没打听,只知道走一圈下来腿疼,可想而知他们用“长跪”的方式丈量这土地需要多少心力。寺庙周围的石头墙有许多处呈现出黝黑光亮的颜色,这都是信徒们用额头叩墙而留下的印痕。
拉卜楞寺的对面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河流对面是山坡,在阳光普洒的时候会有很多僧人坐在山坡的树荫下,轻声交谈。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表现为一种沉默,往往很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和一种表情,任时间像河水一样在身边安静地淌过。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更不好去打扰他们的沉思,甚至连举起相机想去拍照的念头都有所犹豫了。
这里似乎是一个静谧的世界,转经的人三五成群但没有说话,叩头的人匍匐于地全神贯注,习经的人沉默寡语,听到最多的就是几句经文了。不由得,我们也收敛了嬉闹和喧哗,面色凝重地守望寺庙巨大的金顶,感叹宗教巨大的力量,以期安抚自己浮躁的心。
但当我们看到普通藏民迎接他们的节日时,则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那就是——欢腾!
“插剑节”是藏族人一个传统的节日,感受这个节日也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了。在这之前的若干天里,居住非常零散的藏民们会从四面赶来聚集在一起,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妻子、马匹和帐篷,带着早已削好的长达四五米的木剑,在山坡的草原上驻扎,等待节日那天“插剑”和“赛马”活动的到来。几百顶白色的帐篷散落着,几百匹矫健的马儿准备着,山坡成了热闹的大家庭。
清晨六点,活动开始了:男人们骑着马,怀揣青稞粉和五色的吉祥符,一手握缰一手擎剑,从山下呼啸而上;女人们在山下围着帐篷叩头诵经;孩子们打闹在一起,在马背上做着各种技术难度高超的动作。整个草原回响着一声接着一声长啸,这是每一个骑马冲向山顶的人都会不断呼喊的、象征着欢乐宣泄的叫声。他们将剑插入山顶的最高处以显示神勇,用青稞祭祀神灵以祈求护佑;吉祥符不断地被抛撒向天际,这都是他与神的私密对话……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山顶时,都带着某种近乎“贪婪”的心理举着镜头,我们想把这欢腾而神圣的节日纪录下来,想把他们肃穆又温柔的表情纪录下来,更想把这畅快与自在的生活纪录下来。
而对镜头,藏民们表现出羞涩与好奇,在数码相机的显示屏上看到自己形象的时候,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和其他摄影人的到来也增加了欢腾的气氛,孩子们更加卖力地在马背上表演,圆圆亮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让他们看起来非常漂亮;小伙子们整理衣衫要求我们为他多拍几张,他们中没有人会讲汉语,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们愉快的交流;那般高大健壮的马匹是我以前不曾见到的,和着辽阔的草原真是匹配极了!
可是,该返程了,看着草原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掠向身后,知道自己可能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来这里,于是不断回望:五色的经幡飘然于蓝天之下,插着鲜花的玛尼堆处在高高的山顶,令人再次感慨于藏族人的虔诚。但也有隐隐的不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化商业化的习气也会消融掉这虔诚,正像它消融掉其他文化传统一样。所以我一路祈祷,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