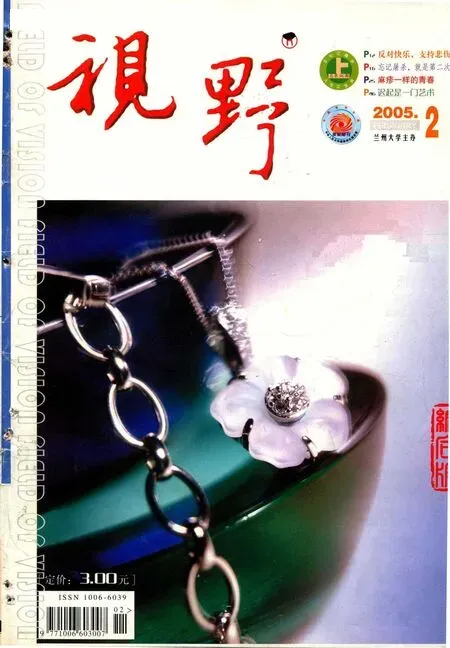窗口之光
2005-04-29邦达列夫
邦达列夫
正月间,风雪交加,巷内的白杨树冻得吱吱直叫,来自上游的劲风把房顶上的铁皮吹得隆隆乱响;房檐上的雪粉不断被风卷落下来,然后顺着白皑皑的栅栏,围绕一个个新的雪堆,飘来舞去。而它,在夜幕中间惟一发亮的这个窗口,透射出恬适的绿色光亮,用窗帘遮掩着,总是那么明亮、温暖,总是那么引人注目,并且使人产生一种困倦和神秘莫测之感。
每天晚上,固定不变地在巷内迎接我的,就是小木房里的这个令人愉快的家庭小灯标,就是这个用窗帘遮掩着的台灯的光亮——我这时想像得出,一座炉火正旺、散发着木柴气味的小木房,里面靠墙摆满了旧书架,一块破旧地毯铺在沙发前的地板上,有一张写字台,玻璃灯罩在昏暗中扩散着光环,那里有一个人,静静地,微驼着背,面带老年人的慈祥皱纹,孤独地生活在书籍的极乐天地里。他无求于世,也不向往世俗欢乐,时而用手指爱抚地翻动书页,时而在室内寂静之中蹒跚地踱来踱去,常常伏案思考和工作到深夜。可是,他究竟是谁呢——是学者?是作家?是谁?
有—次,在去年春天,我望着那个陌生的、神秘的、不眠的窗口,望着那个在室内灯光照耀下似乎永远呈现温暖绿色的窗帘,突然产生—种完全不可抑制的感情。我很想走过去,敲敲窗户的玻璃,看看窗帘被掀开时的轻微摆动和他那慈祥的面孔(我想像那面孔是白白的,稍微眯缝着的眼睛周围刻有网状皱纹),看看堆满了纸张的桌子、塞满了书籍的小房间和地板上的旧地毯……我想对他说,我大概是弄错了门牌号码,怎么也找不到我要找的住家——这样简单地撒个谎,为的是哪怕匆匆瞧一眼他那个十分整洁的生活和工作场所的迷人而宁静的气氛,他的周围全是书,书籍好像就是他惟一的忠实朋友。
但是,我没有下定决心,没有去敲窗户,后来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这一点。
两个月过去了,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改变。是的,一切依然如故。而在静静的小巷里已经充满春色。这时,我看见一只小金虫使劲儿地嗡嗡叫着,开始从暗处慢慢飞来。它撞到了路灯的玻璃罩上,坚硬的甲壳掉落在人行道上,动弹不得。后来又大为惊慌地活动起小爪爪,试图翻过身来。我这时用鞋尖帮了它一下,不知为何对它说:“你怎么啦?”它顺着人行道向一座房屋的墙壁、向一条排水管(离窗口三步远)爬去。就在这时,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不安,一种意外的空虚从五月黄昏的深蓝色中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房子的窗口没有亮,它变得一片黑暗,像地陷了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到小巷尽头,在拐角伫立了20分钟,然后又转身而回,因为还想看看那看惯了的窗口之光。但那窗口却黑着,玻璃反射出晦暗的微光,窗帘一动也不动,不再像往常晚间那样发出令人喜爱的绿光。顷刻之间,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令人毫无舒适之感,这表明:在那里,在那间看不见的小房里,发生了不幸。
我怀着愈益强烈的不安心情,再次来到拐角处,就地抽了两支烟,接着又不由自主地急忙转回,再次来到巷内。我暗自说,现在或者再过几分钟,那个窗帘上就会突然出现绿色的光亮,小巷内将一切如故,将平安无事……
窗口之光没有亮。
第二天,黄昏刚临,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是跑步来到这邻近的小巷。这时,这里出现的意外新情况使我大吃一惊。窗户敞开着,窗帘拉开了,房间的内部、书架和某种地图都露了出来——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初次看到,尽管我曾不止一次想像过这位好在晚间工作的陌生的朋友。
一个相貌像男人、发式也像男人的渐近老境的女人,站在写字台旁,抽着烟,用疲倦的眼光瞧着房间里的空地方。
恰在这时,她忽然发现了我,马上气呼呼地拉上了窗帘——接着,台灯亮了,又像往常那样出现了一小片淡绿色光亮。而我却不禁觉得毛骨悚然,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顿时袭入了心房。房子也好,小巷也好,窗口之光也好,对我来说,一下子都成了昏暗的、虚幻的、陌生的东西。
我这时明白了,是发生了不幸。我想像中的朋友,那位走路时脚下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的白发孤身老人,那位书籍爱好家和哲学家,每晚窗口发亮时都如此吸引我、如此令我心醉神往的那个人,不可能是刚才看见的站在写字台旁的那个生有一副阴郁的男人相貌的女人。在悟出这一真相的最初时刻,我觉得自己如堕五里云雾中,感到一种失去亲人的悲伤,仿佛刚刚收殓了一位故交,收殓了一位如此有自知之明、有创造力、与我最亲近和心神相通的朋友,我虽然与他素不相识,从未见过面,但我终生都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