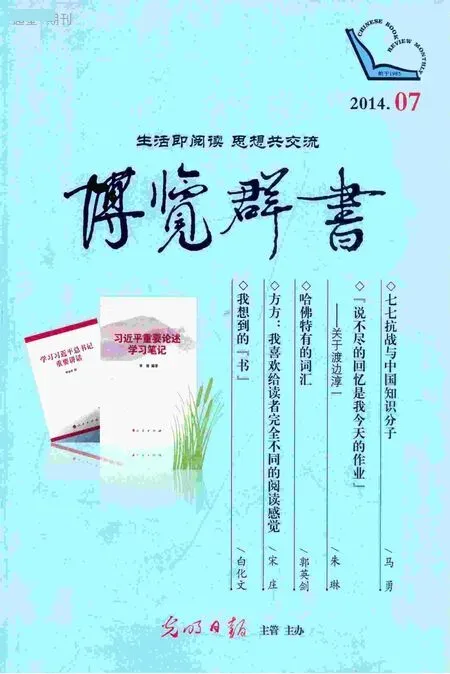古来多少愁人意
2002-04-29刘梦芙
刘梦芙
落花飞絮茫茫,古来多少愁人意。游丝窗隙,惊飙树底,暗移人世。一梦醒来,起看明镜,二毛生矣。有葡萄美酒,芙蓉宝剑,都未称,平生意。
我是长安倦客,二十年、软红尘里。无言独对,青灯一点,神游天际。海水浮空,空中楼阁,万重苍翠。待骖鸾归去,层霄回首,又西风起。
——《水龙吟》
这是清末大词人文廷式的名作。廷式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支持康、梁变法,赞助光绪帝亲政,被慈禧太后革职,抑郁以终。词之上阕以“落花飞絮”象喻清王朝衰落颓败的时世,抒发英雄志士年华垂暮、报国无门的悲慨;下阕写倦对孤灯,神游八极,幻化出瑰丽神奇的理想境界,与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异曲同工。但苏词的基调是旷达,文词则是在徬徨苦闷中寻求解脱。结尾三句言乘鸾飞上层霄,又惓惓回顾西风萧瑟的人世,表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正是屈原《离骚》“陟陛皇之赫戏兮,忽睨夫旧乡”心情的再现。王瀣手批《云起轩词钞》评云:“思涩笔超,后片字字奇幻,使人神寒”;叶恭绰《广箧中词》评为“胸襟兴象,超越凡庸”,均抉出此词之高妙。
甲午(1894)中日战争前夕及庚子之变(1900)前后期间,是满清王朝政治上最黑暗、国家局势最危殆的时期。对日战争惨败,割地赔款;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志士牺牲;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义和团运动遭受镇压,一连串重大事件,交织成一幅幅血淋淋的历史画卷。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年代,传统诗词是反映社会现实、折射作家心灵的一面镜子。清末词坛,是以朝野清流的士大夫群体为主导的,词人意气相投,虽然词作的艺术风格各自不同,但词中的思想情感却往往显示出相同的特征。
前引文廷式词中所写“落花飞絮茫茫”、“惊飙树底,暗移人世”的景象,正是与文氏同辈的词人笔下共有的感触。诸如“鹃啼正苦,奈雨暝烟昏,梦归无据”(冯煦《齐天乐》)、“危楼倚遍,看到云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镜,忽露出、飞来旧影。又愁风雨合离,化作他人仙境”(黄遵宪《双双燕》)、“十分春已去,孤花隐叶,怊怅倚栏心”(沈曾植《渡江云》)、“望中春草草,残红卷尽,旧愁难扫”(王鹏运《玉漏迟》)、“梅花过了仍风雨,著意伤春天不许。……断红还逐晚潮回,相映枝头红更苦”(郑文焯《玉楼春》)、“傍楼阴,东风又起。千红沉损,鹎声中,残阳谁系”(朱祖谋《烛影摇红》)、“东风里,残花藉草,何处更飘茵?……念飘零投老,惆怅逢春”(况周颐《满庭芳》)、“半镜流红涴遍,荡愁心,伤春倦眼”(张尔田《烛影摇红》)……词中意象或相同或相近,无不寄托着词人对国运衰微的沉痛、对繁华之世行将消逝的留恋,而又挽救不得、无可奈何的悲哀。在表现手法方面,即是常州词派倡言的“比兴寄托”,往往形成如陈廷焯所言“沉郁温厚”的意境,词情含蓄而凄沁心脾。当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被困京城,相约填词,成《庚子秋词》两卷,“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王鹏运《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春色凋残后的秋寒彻骨,更是国破家亡时心境的真切写照。这与唐五代、北宋期间词人单纯地伤春悲秋相较,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与辛弃疾“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以及宋末张炎、王沂孙等人的悲凉情调一脉相承。而文廷式词中“海水浮空,空中楼阁,万重苍翠”,艺术形象清晰而又朦胧,美妙却成虚幻,也正是士大夫自陶渊明以来对世外桃源式社会的共同憧憬,但现实的冷酷无情,使梦想终归于破灭。“海燕移家,仙云换影,赢得孀娥清泪”(王鹏运《齐天乐》)、“还见山河残影,恁磨成桂斧,补恨无天”(郑文焯《汉宫春》)、“东风旋起。悄不似仙源,将家小住,便作避秦计”(朱祖谋《摸鱼子》)、“便有桃源思问,不知汉,毕竟知秦。天涯路,关河寸寸,一寸一伤神”(况周颐《满庭芳》),抒情方式或婉曲或直达,无不是封建末世词人绝望的哀叹。概而言之,清季词家在作品中融入家国之悲,沧桑之感,或慷慨激昂,或缠绵悱恻,枨触无端,皆有为而发,境界较唐宋词远为深广,兼以艺术上博采前贤之长,精益求精,取得卓越的成就。至于士大夫词人群普遍存在忠君思想,与爱国之情纠结不分,辛亥革命后尚有眷念王朝,希图复辟者,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扬弃其糟粕即可,全盘否定是明显不合理的。
王国维曾指出,词至后主境界乃大,乃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以王、朱、郑、况为代表的老一辈词人,用饱含血泪的词笔写沧海桑田之变,发黍离麦秀之哀,正是把士大夫词境界发挥到了极处。我们的文学史往往不谈近代文学,就算谈到也是寥寥数笔,却不知道惟有近代文学才最为集中地担荷了士大夫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