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前卫人像摄影
2000-06-06虞若飞
虞若飞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人像摄影界冒出了“前卫”的字眼。不管是自诩的还是人家评封的,反正叛逆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但是,真要仔细寻迹时,却会发现我们无从入手,因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流派展现眼前,我们只能从一列活蹦乱跳的名字——黑冰、潘杰、娟子、姚远、基地、傅百林、韩翔、房翔、于仲安、巍崴、亚辰、谢墨等上去揣摩。他们是否都前卫有待商榷,但至少有点前卫的踪影。
前卫一词源自法语“Avant-Guard”,又译作“先锋”。这个与军事联系更多的术语,嫁接到中国人像摄影后,常用“时尚”、“另类”这样的词来表达。事实上,这场标称“前卫”的运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流行。从总体讲,号称前卫的人像摄影具有形式上标新立异的共同特点,当然也不同程度表露出一些精神内容,如标榜文化厚度,追求独特风格,渴望展现文化精神和艺术心灵的本色。用业界的话说,这是一场“个性彰显的革命”。
有意思的是,经常通过摄影媒体说话的前卫人像摄影师,多数系美术科班出身。如“黑冰”,主创人和员工几乎清一色是搞美术的。他们本来置身摄影之外,从事摄影只是“客串”。他们更注重张扬文化个性,富于挑战性、开拓性、独特性。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影像的探索者和实验者。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应到亢奋的精神,蓬勃的活力,以及青春的圣洁和躁动。这是生命的激情,也正是前卫人像摄影得以产生并扩展的源泉和基础。少数货真价实的前卫摄影师凭着生命的激情,把枯燥的影室变为创造的天地,从而超越媚俗的商业影像制造。
自然,前卫人像摄影并非空穴来风,不是几个美术生凭空可以生造出来的,它不过是人像摄影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中国人像摄影从传统的阴影走出不过几年功夫,然后就是港台婚纱摄影的大举“入侵”,冲击得晕头转向。然而,惊魂甫定,摄影师们才发觉自己被奴役了,感到强烈的压抑,于是便厌倦起来,渴望自己的创造。因此当有人举起“前卫”的旗帜时,大批的摄影师蜂拥而上,追随而来。既然是前卫,也就脱离了传统,也就可以没有规矩,各玩各的,这促成了当前嘈杂又激进的前卫人像摄影的大势。正因如此,前卫人像摄影并未形成流派,仅仅表现为一种时潮。与其说前卫人像摄影是在探求中产生,不如说是压抑情绪宣泄的结果。
前卫人像摄影并非“纯色”摄影,而呈现鱼目相混、良莠相间的状态。正象作家王蒙所说:在先锋这面旗帜所涵盖的文化现象不仅十分丰富,而且也非常庞杂。这其中既包括有文化巨人艺术心灵和艺术精神的极大解放,也可能混有文化侏儒的东施效颦。只是前卫人像摄影赝品远远多于珍品。珍品与赝品混淆,形式与内容异步,流行与独创纠缠,传统与新潮对峙,使前卫人像摄影陷于尴尬的境地。
客观地说,前卫人像摄影师中,不乏有实力或者潜力的人,也不乏独创意识,但是目前还很难有明确的文化精神指向。一提前卫,大多数人就想到形式上的新、奇、怪,想到那些不太容易看懂的东西。误解引来误导,几乎所有的前卫摄影师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形式的创意上,而恰恰忽视了前卫更本质的东西——内容和精神。别出心裁的背景道具,怪异诡谲的服饰化妆,婀娜多姿的动作造型,这一切并没有包装出丰富生动的影像,相反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没有立体感的平面符号,一些被抽空灵魂的“工业模特”。眼下前卫人像摄影最大的弊端就是无力以平实的手法表现人的心灵,形式重于内容,包装淡化个性,形象掩盖精神。许多时候,摄影师的创作成了“造作”。其实这也是中国整个人像摄影界普遍存在的缺陷。许多貌似前卫的追怪求异的作风阻碍了中国人像摄影艺术的健康发展。怪异的外表,正映射出摄影师想像力、洞察力、创造力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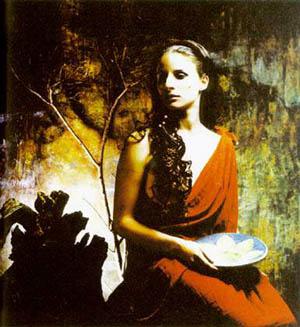
与精神的空乏相对照,前卫人像摄影的形式却时时衍生着很多的变种,五花八门,日趋繁复,造就了前卫人像摄影的表面风光。一些摄影师在影室中感到压抑,想像力无法发挥时,便将创作扩展到室外,如“黑冰”一开始即以外景摄影定位,于是大街小巷、酒吧茶馆,带有怀旧情感的旧的场景,甚至垃圾场都成了摄影师发酵灵感的理想环境。“当狭隘的南方不时地禁锢着他的想像力,同时那种浓重的商业氛围压迫着他的视觉神经”时,象潘杰那样成熟而多变的摄影师走得更远,走向大西北,寻求“南方的突破”,寻求一种空旷的真实。同时各种其他文化和摄影时潮也都反映到前卫人像摄影中来。一些摄影师从纪实摄影中获得灵感,拍摄现场环境人像,事件策划代替了形象造型。怀旧情绪也使前卫人像摄影“泛黄”, 长衫、旗袍、学士帽、格子窗、红木家具、绿军装、红本语录、绸扇……琉璃厂的古玩都搬进了影室,成了绝佳的道具,连远在香港的马元浩先生也搞起了“海派”人像,听说生意还挺红火。近年,随着欧文·潘、理查德·艾维顿等大师的名字流传中国,大批的摄影师又去追踪时装的时尚,或干脆涌向时装摄影领域,“与时装合谋”(潘杰语)。更有甚者,索性从国外资料上模仿,制造流行的中国版本,在资讯尚不很发达的中国,亦可轻易蒙蔽许多人而赢得创新的美誉。
如果上面例举的现象尚具一定创造性的话,那么使前卫人像摄影真正尴尬的是,在逃离一种流行的同时陷入另一种流行,而推动这种流行的恰恰是与前卫精神格格不入的模仿行为。那日松在《拒绝融化的黑冰》中曾描述过黑冰摄影特征:“从前卫出发,走向流行,并与时尚紧密结合,毫无顾忌地张扬了个性,表现自己。原来前卫也能成为畅销商品。”据说黑冰也经常从一些时尚报刊上分析流行然后去创造流行。黑冰的前卫也更多的是商业策略和需要,尽管它的主创人之一严蓉晖标榜创造重于利润。看来前卫人像摄影从一开始就与流行缠在一起,流行是它不可避免的宿命。在前卫人像摄影运动中,更多的是模仿。黑冰之后,崛起了更多的假黑冰、假前卫。原创“流行”多少是可敬的,真正可悲的是“一拨轰”。难怪黑冰叹气:“都是差不多的脸。我们一点也不显得前卫了。我们的反倒变得温和了。”
正如去年第二期《大众摄影》上夏道陵文章所提的,影室摄影是“摄制并非拍照”。现在的摄影室越来越有了工业的意味,许多连名称也改为“XX摄影工厂”、“XX摄影作坊”,最初的主创兼摄影师现在变成了老板,而担任摄影师的则是“员工”。顺理成章,“前卫”也工业化生产了,必然的结果是前卫变成了庸俗的低层次操作。对此,邬竞在《人像的另一种形式》中有过精彩描述:“不少人不思进取,急功近利,不去加强自己,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去感知这个丰富的世界,多彩的人生,而是简单的抄袭模仿。一块绸子围在模特身上,黑眼圈、粉嘴唇,还有块黑纱,或一根羽毛,三只灯,左、右、下一摆,再来个正冲负。好了,这就成了人像时尚,另类的代名词。”摄影师在充实器材丰富背景道具时,太少充实自我丰富思想。在三流的摄影市场上,更多的摄影师仅以一根羊尾巴的辫子来装扮“前卫”的角色。人像摄影在用重彩浓墨包装俊男靓女制造千脸一孔影像的同时,用太多摄影以外的东西包装摄影。缺乏原创力,使前卫人像摄影重复它反叛过的流行。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一些明智的摄影界人士的担忧。那日松先生就曾惊呼:泛滥的“前卫”影像大潮似乎在吞没一切“前卫”。
实际上,有头脑的前卫人像摄影师们也明白自己目前的境况,并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人像摄影》“百期百感”中,潘杰有一番痛苦的思悟:“我想摆脱影楼的模式,去制造与市场无关的人的影像。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下,我开始对我的影像重新审视。”这也正是当前大多数严肃人像摄影师的一种矛盾心态。前卫运动揭示了矛盾,那就是市场与艺术、金钱与精神的冲突。一方面它有明确的商业意图,另一方面它又试图表现出对市场的挑战和反动。
被黑冰称为北京艺术人像摄影的“大哥大”吴波,从美国考察回来后,称黑冰的拍摄风格在美国比比皆是,算不得新鲜事。可见即使站在前卫前沿的黑冰,也不过是在传统的队列中稍微向前伸出了一只脚。事实上,中国眼下的前卫人像摄影仅仅是个前奏,还处于一个演变的过程,是一次迈向新世纪的准备。
真正的前卫是一种大破大立,在反叛传统的同时更具有建设性、开拓性。前卫应该指向文化精神,要试图建立自己的形式规则并以此反对权威的学术及普遍的趣味。我想,在前卫人像摄影中,摄影师的探求精神是优先因素,理想的境界是“摄影师的认真与顾客的满意应当划上等号”。当然,前卫人像摄影的发展也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正确引导非常重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摆脱只有古怪才是前卫,只有西方才有前卫的思想误导。前卫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怪异,平常中往往有最神秘的玄机。道可道,非常道。最传统的也可能是最前卫的。如禅是传统的,但如果把禅的一些公案,如棒喝、吃粥喝茶等拿到现在放在艺术里演示,恐怕仍然是十分生动而前卫的。以粗线条、泼墨为主的中国写意画,就曾经深刻影响了许多欧洲现代画家。其实中国并不缺乏肖像的传统,中国的仕女图许多可拿来作现代人像摄影的蓝本;中国写意人物画怕是世上最抽象而传神的肖像画。如果能从生活、自我精神体验及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融入前卫人像摄影艺术,必将能开创一个全新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