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遭受性虐待女死囚的故事
1999-12-25晓琳
晓 琳
1995年1月5日,让死囚陈燕(化名)永生难忘——当她接过“罪犯监外执行证明书”时。被巨大的兴奋击懵了。清醒后,她长跪不起,泪流满面,不堪回首的往事重又回到眼前……
17年前的冬天,是11月14日,早上7点零1分。29岁的陈燕捂着自己“嘭嘭”狂跳的心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走在初阳斜照的马路上,看他人影一点点变小再变模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瞬间的冲动。她想冲下楼去,飞快地追上丈夫对他说,刚才我给你的那个小瓶里装的是毒药!但是,立刻又有一个声音冒了出来:让他去!这辈子我算是与他完了……
陈燕喃喃地叙述着——
我的婚姻,偏偏还是缘于一门远房亲戚阿宁嫂的报恩还情。我一听对方大10岁,心里就老大的不愿意。不料母亲对他很满意。我讲不出拒绝妈妈的理由。我只好接受他的邀请,赴他的约会。不过每次两个钟头,时间一到就散伙分手。后来,他大概也觉得我与他话不投机。就索性上门来了。这样,我倒也就觉得少了很多的尴尬。他一来全家都陪着。我觉得省心省神更省事。婚礼定在1977年12月14日。我从来没有与他产生过所谓热恋的感情,连恋爱两个字也谈不上的。我们单独在一起我就感到特别的不自在。最难堪的是我们在杭州过的新婚之夜。那一日天很冷,他先躺下了。我在床边倒了一盆水后,看见他还躺在那儿,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就说,你出去呀,我要“用水”了。他问用啥个水?我说用水……就是用水来洗洗身子……他说你就在这里洗,我不用出去的。
自这倒霉的一夜开始,我只有一种“失守”的伤感,而没有一点喜悦的心情。1周旅行结束,我们回到了A市,这一周的“领教”,实在叫我望而生畏。开始的所谓新生活,我想着也后怕。但是结婚。就是这个“事”。没有办法的。元旦过后5日,晚上他回来了,没有说几句话,他就谈到了我的工资。我说我贴娘家10元钱,他说你怎么事前没对我说就给了!语音未落。我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他对我拳脚相加,竟要我回家去将这10元钱要回来!这是在我们结婚的第20天发生的事,我怎么能够忍受?!我的眼睛“突突”在跳,似乎浑身上下都在冒着火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我“噌”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穿上衣服就开门出去了。两个钟头之后,还是回了娘家。母亲心疼地对我说,女孩儿家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母亲硬是让弟弟送我回去,并让弟弟带话给他:下次不准再打人!
因为我心里不喜欢他,干什么就都会不情愿的。大约两三个月后的一天,70多岁的婆婆,在我一再追问之下,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被我丈夫打了,一只手都疼得无法抬起。晚上,我对“挨上前来”的丈夫说,你怎么可以打自己的娘呢?我告诉你,如果我没有嫁过来,你打死你老娘我管不着,现在我来这里做了媳妇。我就要管!正在来“兴头”的他,被我这一说,立即走了神,心中恼羞成怒,拳头巴掌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我吓得倒抽着冷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见他铁青着脸吼着:“我打死老娘我抵命!……”
一场暴力结束后,无法招架的我被打得鼻青眼肿,躲在床角里呜呜地哭。可我没想到下一场“戏”还没开始。他坐下来,喝了一口水。才一刻钟的时间,竟又一把拎着我上了床。接下去的“事情”,我的心寒极了!他要在我身上做的事情,身单力薄的我,岂能摆脱得了呢?虽然我一万个不情愿,但是“事情”又不可随便张扬。毒打与性事是他每天非放在一起做的作业。有一阵,我实在不堪忍受他彻夜的折磨和殴打,老是逃回娘家,可也不是个办法,就试着到法院去。但那些事情岂可以随随便便说出口的?法院的人见我支支吾吾说不清,也就毫无结果地让我回去了。他一天也不肯放过我。结婚6个月后的一天,我一个人悄悄逃到武汉我姐姐处。去武汉只是我有次想自杀前一刹那,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我想以我的突然失踪,让他好好反省自己,也让妈妈想想她为啥一定要我嫁给这个人。我真不明白他的精力竟有这般旺盛,把那个事——当茶喝!事情也真怪,每当他想“喝茶”时,女儿就哇哇大哭。有一天夜里,他在兴头上时,竟然对着嚎哭的女儿。狠命一脚将她踢下了床!女儿被撞得头破血流,连哭声也没有了……我抱着女儿走进了法院。我决定与这魔鬼离婚。不多日后的一天,法院传唤了他。回家后,他对我冷笑一声说:“好哇,你想离婚?不错,你状纸上写的都是事实。不过,我自从与你结了婚就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婚。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我真是恨呀!我认为这种事比遭受流氓的强奸还要绝望,还要愤恨。因为被流氓强奸还可以立即报公安局,然而他比流氓恶劣,却还名正言顺。我想我一时不能挣脱,我就自己先保护自己。于是我想了个最可怜的蠢办法,每天夜间,就穿上厚厚的紧身棉毛衫、棉毛裤进被窝。哪料事与愿违,被他撕碎的内衣内裤也不知有多少条。毕竟那时的经济条件都还差,我悄悄补了再穿。有一条厚毛裤,被他一次次撕剪过,又被我一次次缝合过,上面一条又一条如拉链一样,在入狱后的日子里我还穿过。后来闹离婚,更多的是我无法容忍他打孩子。我真不懂他下手怎么这么毒呢!想想孩子嫩嫩的才8个月,他竟像扔一件东西一般,说摔就摔出去了……第一次,就将孩子细细的胳膊“脱臼”了。小孩哭,他也要打,只要他认为哭得不是时候。他一打,我必定去拉,我一拉他便打我,这已经是太正常的事了。那些年里,我从来也不在医院里洗澡,因为身上大片大片的青紫不断,我怕同事们追问。
我闹着离了9次婚,一次也没有成功。就说那最后一次的离婚吧,时间是1982年9月底。在这以前。我已与他分居了1个多月,为了保证这次离婚能够成功,我的老父亲和弟弟及亲属们,每天一脚不漏地送我上班和接我下班。我对法官说,只要能离婚,我什么都可以不要。这之前,他知道女儿是我的命根子,就死活与我争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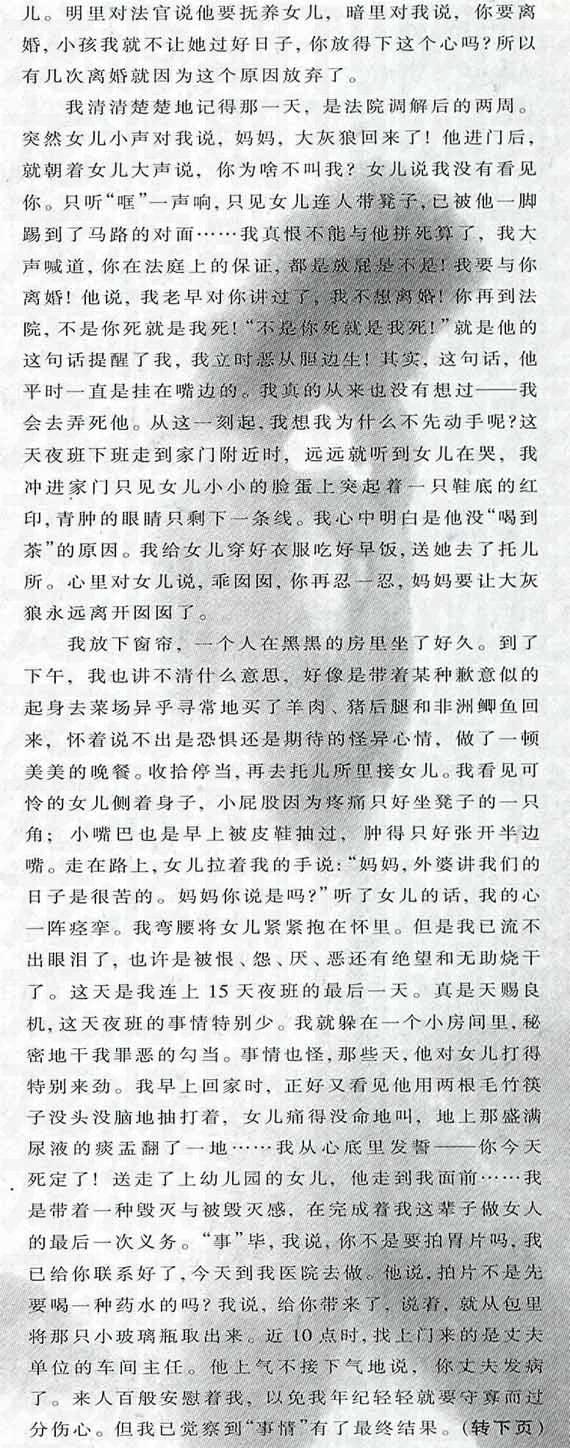
1983年8月16日的下午,一阵警笛呼啸过后,我被带上重重的戒具,投进了死囚的监所。
也不知过了多久,刘警官见我哭完了,就告诉我说,从明天算起,你有10天时间可以上诉,这是你的权利。刘警官说,事到如今,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了。你写上诉。就是救自己。
这一夜,我伏在死囚监房中的那张小木桌上,不吃不喝,奋笔疾书,通宵达旦。求生的欲望如茫茫黑夜里的一支火光,诱惑着我,照亮着我。这一夜。刘警官也没有睡。当刘警官拿着我的这份诉状离去时,我眼中期盼的火焰,可以将铁板熔出一个大洞。接下去的时日,是漫长又漫长的等待。
1983年10月21日,我30岁。只听得一名着藏青制服的女法官威严而慈祥地对我说,我们是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收到了你的上诉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现经审核裁定,特来这里开庭向你宣布:“……以故意杀人罪判陈燕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6年1月30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89年3月16日,我被减为有期徒刑14年。1990年12月13日,我又得到人民政府的司法奖励,又出被减刑1年。在那场生死之变后。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几年后,在A市某居民密集区,出现了一家敬老院。据说,院长今年46岁。在她任院长的两三年里,她多次受到区民政局和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表扬。这是个钟爱事业的能干的女人,这也是个把内心世界封闭得紧紧的女人。读者或许猜出她是准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