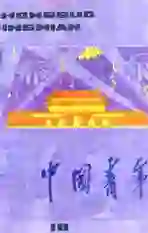守望星空
1997-09-11耿海亮
耿海亮
在千百万年前,千百万光年外的
一颗恒星终于走近了她生命
的尽头。她那曾经放射了亿万年的光辉正逐渐暗淡下去,即将融入那无际的黑暗,她那庞大的身躯也在逐渐缩小,逐渐冷却,一切都将静静地消失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但一阵悸动打破了星系的沉寂,转瞬间她爆发成一个炫目的巨大的光团,光团翻滚着膨胀着,四射的辉光似乎要在这一瞬间将无尽的黑暗引燃……
一颗恒星以最辉煌的方式消亡了,一切又归于沉寂。
在千百万年之后,千百万光年之外的地球上,寂静的夜里,一个年轻人,正在茫茫星海中搜寻、守望着这一切。
他叫李卫东。
守候在寂静的夜里,却为了终结一个全是空白的时代
“错在哪呢?”李卫东像狼一样在山顶围墙内的小路间慢慢地转着。
“发现并观测超新星”,两个月前,刚到兴隆观测站的他接受了这个课题。这个28岁的天文学博士后,领着从20到50岁的三个天文学博士,守着一台国际上已经淘汰的60公分口径的光学天文望远镜,就是这么一支队伍,任务却是要终结一个时代。
天还没黑,太阳,是他现在仰头能看见的唯一星体。但他不用看,便可以准确地想见,天空中所有星座现时的位置。但他等的不是这些。
“就和人有生老病死一样,星星也逃不过由生成到毁灭的过程,而恒星在毁灭前,会发生质变,忽然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仅就亮度而言,其变化相当于由一根燃烧的火柴,变成一颗爆炸的原子弹。”这是他对作护士的妻子所做的有关超新星的最通俗的解释。
古人也看星空,不过那时更多的是星占术士,观察星相占卜吉凶,为帝王的基业。李卫东想笑,自己竟和千百年前的术士做同样的事,但却为了终结一个全是空白的时代。本世纪4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正式为超新星定名,有人翻阅古籍,竟发现原来中国从宋代到清代的古书里都有银河系里某颗星骤然闪亮的记录,“我们中国人在宋朝就发现并记录了超新星。”于是人们欣欣然。
这是我们惯常的骄傲。
可是从1640年以后,这个年份李卫东很熟,中国人,便再与超新星无缘了。300多年了,星空并不寂寞,恒星依旧上演着毁灭前最后的辉煌,可50年的时间里,当国际上银河外星系的超新星发现数量已经累计到4位数的时候,在中国那一栏里,依旧是一个零!
这也是我们惯常的失落。
李卫东他们就是要结束这个“零”的时代。
“错在哪呢?”
300多年的空白,无边无际的星海,从哪下手?国内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那就向国外求援。刚刚成立的“北京天文台超新星小组”通过INTERNET(英特网)向全世界知名的天文台、超新星研究小组、知名学者发出了80多封电子函件,但回信只有7封,其中6封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对不起,我们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这种冷遇也在李卫东的预料之内,你李卫东是何许人也,你中国超新星小组是何许人也?
山顶观测站内的小路加起来也不过几百米,这是第几圈了?
“我就不信……”李卫东一急了就爱说这句话。这次,他说完这话就一头钻进了圆顶室。发现超新星的关键,要有一张由电脑程序织成的从茫茫星海中捕获猎物的密网。他要自己动手织这张“网”。敲一阵键盘,想一阵,卡住了,盯住电脑屏幕就是几个小时,憋急了,就出来,念念叨叨地像狼一样满山转,想通了,再进去敲。“我就不信……”有人尝试过编制这种程序,三个人花了半年,“我就不信……”几十米远的宿舍也不回了,实在累得不行了,就躺圆顶室里的破沙发上睡一会儿,圆顶室里点一盏小灯,就没了日夜的概念,“我就不信……”
后来山上的人说李卫东那时像是着了魔障。
后来李卫东说,那是他上山后最难受的日子。
半个月后,李卫东从圆顶室里走了出来,“网”织成了。网织成了,他就躺下了,半个月,高烧。
那是1995年夏天。
在宇宙的某一个角落,一定有一颗恒星,用她生命最后爆发的光亮,穿过漫长时空,向他奔来……
圆顶室外是24度,圆顶室内也是24度,零下。
“今天有超新星”,每天走进圆顶室,李卫东和他的小组成员们都要说这么一句,这是句不知何日能应验的预言,算是一份希望。然后大家便各自坐在电脑旁。
当繁星在天宇间显现出来时,他们的工作便开始了。
常有朋友上山来看他,也是来看星星。坐在圆顶室外的水泥台阶上,仰望穹苍,星光至大,至亮,至清,从幽蓝的天顶一直垂挂到目所能及的天地交接,久被斑斓的荧屏捆绑,被闪烁的霓虹撩拨的视线竟会在这一瞬间自由地放纵于天地之间,心灵在那一刻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感动。“美吗?”“美!”回答着朋友的问题,李卫东的眼睛仍望着星空。“你们搞天文的,整晚地看星星,是不是特幸福?”这常常是朋友们半开玩笑半是认真问他的第二个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往往默不做答。
望远镜透过圆顶的开口,直指幽暗的星空,像守望者孤独的眼睛。
李卫东他们在望远镜的下面,在圆顶室的底层,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守在电脑的荧屏前。每隔几分钟,屏幕上就会显示出一张由望远镜拍摄下来的星系图,他们要做的就是日复一日地从这些沙粒甚至是微尘般的亮点组成的棉絮状的星图中找寻。每有一张新的星图显示出来,他们都会感到在这星沙中可能埋藏着希望,但很快地,失望又取代了一切。
每个晚上观测300个星系,夜便被失望重重地分割300次。每隔十几天,他们就要把整个星空搜索一遍。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他们无法忍受星空的沉寂。
又停电了。电脑荧屏黑了,圆顶室黑了,整个兴隆山陷入了黑暗。小组的几个人几乎同时叹了一口气。
李卫东向椅子的后背一靠。黑暗中,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多少天了?他一时竟想不出来。5月份到山上,现在已经是12月了,有半年多了?几百万光年,上千万光年,之前?我在等待一个在时间与空间都是绝对遥远的、在我的生命产生之前所发生的一幕!他忽然感到生命与时空间某种不可言喻的矛盾。但这只是一个闪念。超新星在千百万光年之外,妻子在150公里外的北京城里,现在妻子可能在看电视,也可能已经睡着了。也不能怪她有时耍脾气,搞天文的,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守在山上,能怪她吗,男人是应该养家的,可自己的工资还不到妻子的一半……
电脑的显示屏又亮了。
“来电了,继续。”李卫东戴上眼睛,又坐到了电脑前,但他很快发现继续观测几乎不可能了。电路故障,圆顶不能自动旋转了。
但这一夜的观测还是继续下去了,李卫东和他的伙伴们,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人跑到圆顶的二层去转圆顶,转一次拍一张,拍一张转一次,从晚7点到早6点,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夜里,每个人楼上楼下跑了近百次。当早晨他们从碉堡一样的圆顶室里钻出来的时候,人人都是一脸菜色。
这一夜,他们同样一无所获。第二天晚上,观测继续。
这是一种近乎无望的等待,5000个星系,每个星系100亿颗星星,5000乘以100亿,这是一个足以让常人的想像空间达到极限的数字。
但面对浩瀚的星海,李卫东相信,在千百万年前的宇宙的某个角落,一颗恒星,在她的生命即将终结的一刻,忽然爆发出耀眼的光亮,以与时间同步的速度向他奔袭而来。
他等待着。
地平线上那个微小的亮点,却点燃了一段生命的辉煌
“找这个‘超新星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一点。”常有人问李卫东这个问题。“实际一点?”这时李卫东可能会指着对方的戒指或是项链:“只有超新星的爆发才会产生比铁更重的金属,比如金、银……再比如,太阳终有一天会成为一颗超新星……”当然,对方和他都明白,时空距离都在千百万年前的某次恒星的爆炸绝不是四十大盗的宝库,这已经涉及了物质的起源,而太阳生命的终结也在亿万年之后。这时,双方就都会感到,如果再就此谈下去,交流是极困难的。于是话题便被岔开了。
守望者是孤独的。
300多个夜晚在期待与失望中重复着。
1996年4月10日,这个日子李卫东记得很清楚,但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却记得不太清楚。
他记得那天是该他值班观测,但他晚去了一会儿,那天他的一位师弟来观测站,来的目的是要见一位心仪已久的师妹,于是便死缠着李卫东帮他去约那女孩,等李卫东做完红娘回到圆顶室的时候,观测已经开始了。
他记得那天有点阴,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观测助手在向电脑中输参数的时候,却输进了一个“A”,这就意味着“天气状况很好”,电脑并不会自行判断天气,便选择了300个在那种天气条件下,几乎没有观测价值的星系。
4月11日凌晨,李卫东将星系的照片一张一张地对比观察。忽然,在某星系的照片下面,距地平线很近的地方,多出了一个极微小的亮点。“超新星?”李卫东不敢肯定,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在这样的观测区域内,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观测的准确程度。4月11日,天还阴着,无法进行对这一亮点做光谱确定。他决定试一试,他知道全世界有多个观测站,无数的专家与天文爱好者在天空中搜寻,慢一秒,发现权就会落入他人名下。他向国
际天文组织发出了一封电子函件,将那个亮点作为超新星的“候选体”。
“唉,那真是……就是那种……真是……”李卫东现在无论如何也表述不出当时的感受,4月12日,当他打开电脑上的发自国际天文组织的电子函件时,他只听见周围的同事们近乎疯狂的欢叫声,蹦跳声,而后就是同事们的手重重地拍在他肩上,很疼。他记得他当时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晚上我请客、我请客!”
1996年4月12日,国际天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公告确认,由中国北京天文台李卫东、乔琪渊、裘予雷、胡景耀四人超新星小组于1996年4月11日发现一颗超新星,定名为1996W。
在请客之前,李卫东没有忘记给在北京的妻子打电话报喜。“开玩笑,你不是说特别难找吗?别骗我了。”任凭他在电话这边喘着粗气急红了脸,妻子就是不信。
星空灿烂,但守望者依然寂寞,在沉静中,一个新的时代正悄悄开始……
李卫东和他的同伴们结束了一个时代。这同样意味着他们也开始了一个时代。
各中央级的新闻媒体,以显要的位置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首次发现了河外星系的超新星的消息。一时间有关超新星的文章出现在大小报刊的科普专栏里。“超新星“李卫东“超新星小组”以极高的频率在传媒中反复出现。但仿若超新星的爆发一样,在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这很正常,毕竟,中国知道超新星为何物的人,太少了。
很多人把这第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归于偶然,而“偶然”两字在李卫东的生命轨迹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生在大别山区的他,自小对天文并无兴趣,清华大学的老师来到他的高中招生的时候,问他愿不愿意考清华,他说:“不,我想考师范!”他是冲着不交学费还有补贴去的,家里穷。“那你就考北师大吧。”“您说哪个专业好考?”他问那老师。“天文、物理、化学。”李卫东第一个听到了天文,就把天文填进了自己的第一志愿,而后也就真的考上了,并且在这个专业,由本科、硕士一直念到博士,直到今天作了博士后。甚至在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还想换一个专业,学计算机,但一个偶然的因素又打破了他改行的幻想。
一个夏天又如往常一样,静悄悄地过去了。
1996年10月18日,李卫东他们又在一张星图上发现了一个微小的亮点,但上帝似乎有意和他开玩笑,第二天又是阴天,不能进行光谱确定,他又将他们的发现作为超新星的候选体,上报国际天文组织。
李卫东和他的组员们几乎是一有空就跑到电脑旁,19日,没有回音。
20日,没有回音。
21日,没有回音。
1996年10月23日,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他们终于等来了国际天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的通告,证明他们所提供的“候选体”是一颗超新星。
但这一次人群没有欢呼。
因为在小组全体成员的名字后面,还有一个共同发现人,一位英国业余天文爱好者,但他发现这颗超新星的时间是10月23日,比李卫东他们整整晚了5天!
尽管李卫东和他的小组成员发信质问国际天文组织,尽管国际天文组织很快地回复了,并很客气地列举了诸多客观原因,但李卫东他们相信,真正的原因在信之外:一个刚刚成立一年多的观测小组可以发现一颗超新星,这是运气,但不可能发现两颗。
一颗是运气,两颗是偶然,那么三颗、四颗,而且是在一年之内呢?到1996年底,李卫东领导的超新星小组共发现超新星6颗!这是一个无法用任何幸运、偶然一类的词来解释的、响当当的数字。
终于,李卫东他们小组的电子信箱里热闹起来了,世界各地的天文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业余天文爱好者的信件雪片般飞来,有祝贺的,有请教问题的,有交流信息的,这其中也有当年对他们的求助信置之不理的专家、组织。这些资料似乎来得太晚了,但李卫东他们需要,需要这种承认!“应该说,现在每多发现一颗超新星,就会增加我国天文界在国际天文领域的一份筹码。”
李卫东忘不了4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他在北师大读博士研究生,恰逢在我国西安召开一次国际超新星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的超新星学术权威都到了。但这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
术会议,足以令中国人感到尴尬,讲台前演讲的是外国人,底下提问的是外国人,讨论得热火朝天的还是外国人,中国的专家学者只有看的份,听的份,我们没有发现过超新星。
在会议的间隙,李卫东走到一位美国超新星学术权威身边:“打扰您,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不可以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正在与几个外国专家闲谈的美国专家,扭过头来。我们可以想像,他那时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李卫东那谦恭的表情,也可能根本没有看到他手中写着问题的那张纸,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就足以让他硬硬地说出后面的话:“不,我很忙,我没有时间!”
李卫东说不出但也永远忘不掉那时的感受。
我们不该程式化地把他的那次经历与今天的成功联系起来,但今天的成绩,却可以给他4年前的那段经历一段对比强烈的参照。李卫东领导的超新星小组自1996年4月10日至1997年7月20日,共发现超新星15颗,在“近亮星”里,同期发现数量世界第一。
李卫东他们捕捉到的超新星多数都在“光极大”之前,这也是世界领先。
另一个值得李卫东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所发现的超新星类型之新,之多,是其他超新星研究组织所无法比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别人捕获的是平平常常的兔子,而李卫东他们捕获的兔子,长着3只耳朵、4只耳朵,仅一只这样的猎物就足以成为猎人炫耀的资本,而这样的兔子,李卫东他们手里有一群!
“如果再有国际超新星会议召开站在讲台上的,一定是我们!”李卫东这么说,极其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