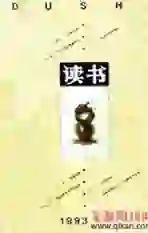灵均芳草伯牙琴
1993-07-15许苏民
许苏民
《吹沙集》是萧
立足于理性的审视,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科学—理性”的工具,努力揭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特定时代人类历史实践的水平,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他强调“连环可解”,从浩繁的哲学原典中爬疏剔抉,努力揭示哲学范畴从朦胧到清晰、从抽象到具体、从贫乏到丰富的逻辑演进,勾勒出中国哲学发展的“大圆圈”和“大圆圈中的无数的小圆圈”,展示出中华民族的哲学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逻辑。
同时,借助于审美的形象思维的体验和感性观照的辅助,作者又十分注重以诗人的直观能力去“神交古人”——全身心地投入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化情感共鸣的审美体验之中,去悬想事势,遥体人情,设身处地体验特定时代经济政治的外在刺激与哲人的亲缘地缘关系、师门授受、文化教养、性格气质、身世浮沉等等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哲人心灵的深层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其理论思维的制约作用。
——在这里,作者给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理性”工具的运用注入了审美体验和观照的生动的感性生命,而感性的审美观照(形象思维、体验、直觉)亦服从和服务于理性的求真目的,其中亦渗透着理性分析的因素;这情理交融的体验促进了理解,而深刻的理解又对象化为生动的陈述和再现。于是,哲学史的陈述就不仅仅是黑格尔之“正、反、合”式的单纯的逻辑演进,而是以把握过去时代的真髓和血肉的“真实性”代替了那种只有逻辑的骨骼而没有感性生命的血肉的所谓“客观性”。
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的理性方法,并不排斥研究者的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历史使命感,通过二者之审慎的结合,后者将给历史科学的研究以不竭的动力源泉,前者亦将给予研究者的道德激情和使命感以科学的理性规范。
在中国哲学史界所注重的“三际”(周秦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中,作者尤其钟情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认为这一时代的哲人以朦胧的历史自觉顺应了中国社会行将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步潮流,其思想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是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亦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结合点;其砥砺气节、自我超越的道德情操更体现了“光芒烛天、芳菲匝地”的人格美。然而,作者在阐明历史科学并不排斥情感、及其所以“一瓣心香向顾(炎武)王(船山)”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揭示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拉住活的的历史洄流对哲人的理论思维的制约,致力于分辨其“言志之作”与“应酬之作”,辨析哲人心灵中新旧杂陈、矛盾重重的思维格局,揭示其理论思维的误区及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在这里,求真的科学态度始终是作者全部立论的生命所系,而道德激情和历史使命感则十分自然地体现于其科学态度之中。这样,作者也就自觉地避免了把不可重复的既往的历史当作“当代史”来写的所谓“真历史”的误区,而是以完整准确地把握对象自身中的灵魂的科学性代替了那种仅仅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从而“使过去变成了现在”的主观随意性。
《吹沙集》中除收录了作者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论文、演说外,还收录了反映作者追求美与真之统一的心路历程的诗作,这是《吹沙集》的又一特色。“灵均芳草伯牙琴”,是少年时纯真的向往;“梅蕊冲寒破雪开,……吸收诗情向未来”,是青年时如火的情怀;“九畹兰心凝史慧,五湖鸥梦入诗篇”,是壮年时广阔深沉的思绪;直到老年,“劫去高吟火凤凰”,仍然自信“一瓣痴葵蕊不枯”。对于“海上琴心”、“火中鸣凤”的咏叹,与其论说相映照,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哲人将求真与求美结合起来的文化精神的自觉继承。
(《吹沙集》,萧
品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