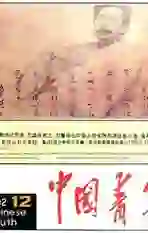广佬与北佬:五十步笑百步吗?
1992-08-24李继泽
李继泽
再度“南飞燕”
邓伯伯南巡,来到珠海亚洲仿真公司,老人家顿时为之一振:啊,清一色的年轻人!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要拉拉年轻人的手。”
这是亚洲仿真公司年轻人的殊荣,也是所有“广佬”们的殊荣。
“北佬”们于是又眼热起来:瞧人家活得多带劲!咱哥们儿也不缺胳膊少腿的……
于是,“南飞燕”再次起程。
在新的南下潮中,除了那些不日就要返回的“学大寨”者外(人们把南下参观考察比为当年的“学大寨”),剩下的就是那帮义无返顾、破釜沉舟不当上“准广佬”决不罢休的年轻人了。
如果说,在第一次南下潮中的“南飞燕”们对广东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发开放财”,以及连蛇肉都敢吃之类不无轻蔑因而难以认同的话,那么此次的“南飞燕”们则显得实际多了。
试以笔者自始至终目睹的“丽人行”故事为例。北方某省城的3位女大学生,名字分别叫石歌、倪云、路岭,毕业后都有了令当地人眼热的工作。然而3人都对那缺乏挑战性的机关工作和每月固定的一百几十块钱感到乏味,于是共同行动互相壮着胆砸了手里的铁饭碗,联袂南下闯入深圳。一看,嗬!到底是邓小平推崇的地方,这里的商品意识是那样强烈!这块土地离世界是那样近!几年中我们内地人还在那儿坐而论道评头品足地争论不休,而人家已不声不响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地把经济搞上去一大截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加上她们的漂亮、机智,无亲无故无后台的3个女仔拿着报纸上的广告到不同单位应聘:面试、谈条件,双向选择,既有老板婉言推拒的,也有她们发现了有什么不利而不再回头的。当她们从家里带着的上路钱快要告罄时,3人都分别找到了可意的去处:石歌在一家厂当报关员,不久就因为业务需要挂上了PB机;倪云先是在一家宾馆做职员,后又“飘”到一家行业杂志做编辑,临阵磨枪翻了几本工具书之后居然也像模像样地组稿约稿了。当一位算命先生预测她到30岁就会拥有“百万身家”后,她真的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冲着“百万身家”去搏杀了;路岭在一家日本人投资台湾人管理的手表厂做了大陆雇员中职务最高的雇员,厂方还许诺将来把她的户口迁入深圳,不过她认为户口已并不重要。
最有趣的是南下潮中有一部分曾经做过一段学问的人们,想当初他们是何等的热血沸腾,可是经济改革的浪潮把他们冲刷得迷惘失据了。失据的人们终于在广东找到了“据点”:埋头搞改革和把经济搞上去的人是最聪明的,民主的种子只有在富裕的土壤里才能发芽生根。
一位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曾失意回到山东老家。而如今,他成了广州一家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内容的杂志的执行总编辑。他过去是最看不起被史书称为“南蛮”之地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中国的劣等民族。来以后却从他们那独特的思维中捕捉到久违了的商品意识,于是努力把自己融进众多的“广佬”中去,从而迅速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然,他并未忽略这块土地上文化的贫乏,正是这个缺陷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得以将自己对世界的科学感觉付诸实践,在使这个世界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中,他充当着一个积极的角色。
像他这样对自己进行反思之后投入“南飞燕”行列的现象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偶然,而是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必然。
财大气粗的背后
好多南下的“北佬”们都喜欢这样评价“广佬”:他们财大气粗。
有两位从北京来的某大报记者,慕名前往佛山市某企业采访,首先提出要见厂长,厂长听说是从北京来的记者,不但拒而不见,反而出言不逊:“什么?××日报的,不接见!北京的记者怎么能写出广东的改革?写出广东的企业家?”办公室的同志为难了,只好说厂长有急事要外出,就采访科长吧。采访完回到北京后不久,两位记者将连续奋战写出的一个大稿快件寄给厂长,并附有一封信,大意是说请厂长审阅修改后签字寄回。厂长不经意地翻看了稿件的前几页,居然不大恭敬地将稿子扔进了字纸篓:“哼!北京的记者写文章还是用过去那些套词,这样的文章我在部队当报道员时也会写。他们真想写也可以——先来广东滚3年!”
另有某新闻机关的领导同志南来与一位农民企业家交谈,末了征求企业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企业家直率地说:“第一,你们批‘左批得不够,对‘左的一套太客气,太温良恭俭让,致使他们总是横行霸道。第二,对改革歌颂不够,对改革家宣传不够。广东的改革多伟大!老百姓说是第二次解放。我注意到你们发的焦裕禄的文章,而我说珠江三角洲的焦裕禄——新时期的焦裕禄就不少,缺少的只是发现。几百年几千年的富裕梦,今天成为现实,大功劳啊!大英雄啊!前无古人!为什么邓公南巡我们万民同欢?因为他宣告了改革者有好下场。”
还有一位知名女记者来到珠江三角洲,有关部门电话通知某县的新闻秘书予以接待。新闻秘书只不过是个副科级干部,浑身还充满着农村干部的味儿。他先是甩出一句“省骂”,然后对抗道:××日报去年整整一年没有广东的一个头版头条(他显然是把怨气都撒在这位女记者身上了),我们县没有什么值得她写的。
细品上面三个故事,有见解的人可以看出,广东人的所谓财大气粗后面,其实分明透出一种“阴柔”,一种下者对上者的怨气,再引伸一下可以说是一种请求,一种呼唤,一种祈望:请了解我们吧,理解我们吧!
五十步笑百步吗?
除了怨,当然也有哀——哀其不幸,这是一位广东某局下属的一个公司经理去中原的某个大城市开了10天会后的全部感受。
这位40岁的司徒经理应邀来到中原某大城市的水利电力学院开会,其间拜访学院70多岁的本专业最具权威的老教授。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仅是老教授家的住房狭小和因工资低请不起保姆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老教授家里竟连部电话都没装!他心想,在我们公司,许多普通工人家里都自费安装了电话哩。司徒经理当即向学院领导表示,我们公司投资几百万元(他这个经理一人在外就可以作主,足见他公司的实力),为学院安装几百门电话,补偿条件是前5年的电话费收入归我们,5年后都是你们的。
对于学院来说,这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不花一分钱,电话就装上了。这种求之不得的事,应该抓住不放。立即拍板吧?可等到他们研究研究以后,给司徒经理的答复是:不成。原因是什么,司徒经理明白了,无非是怕我们赚了他们的钱,这和当初我们怕香港老板赚了广东的钱一样。但那时广东人很快就从怕到横下一条心再到欢迎香港老板赚我们的钱了,如果没有香港老板赚广东人的钱,也就没有广东今天的发达。老实说,现在广东人要赚内地人的钱很容易,就像当年香港人赚广东人的钱一样。你学院不敢与我合作,总有人敢与我合作嘛!我只是为学院感到遗憾。看来观念不改变是最大的不幸。
故事还没有完。到了晚上,学院请与会者上舞厅跳舞,两位数一张的门票另加饮料点心,费用全由东道主负担(内地不少城市舞厅生意特旺,大多数是公费请外来的客人跳舞,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慷慨,假如告诉他们如今“广佬”已逐渐兴起了“AA制”——吃饭玩乐后各人付各人的那一份钱,他们可能会斥之为不讲“人情”)。请到司徒经理,司徒回答:“我不会跳舞。”这回轮到学院的人不可思议了:“你们广州来的不会跳舞?谁相信!”但信不信由你,司徒经理真的不会跳,因为平常工作过后剩下的时间很宝贵——全部用来睡觉。当晚,他在招待所就接到公司从广州打过来的电话,他也往广州香港深圳打出了10多个电话,一算,电话费100多元。招待所的服务员不解:从来没见过住这里的人打那么多电话,他到底是个什么官?司徒经理说:我打电话花掉100多元,但我因此为公司赚回了100多万元。
还有许多事情都容易使人看到“广佬”与“北佬”间业已存在的差异:
——前面出现过的那位拒北京知名女记者于门外的某县新闻秘书还有一段耿耿于怀的记忆。那次他带着一队企业界人士去四川公干,住进成都的一个宾馆。吃晚饭买单时,发现异常地贵,询问有没有搞错。餐厅服务员回答没错,其中包括你们晚上进舞厅的门票。“我们没说要去舞厅呀!”“噢,我们对港澳同胞都是如此。”“我们是广东××县的。”说着,拿出身分证,人家不看;又拿出有镰刀斧头标志的党费证,人家还是不看。“反正你们南方来的人有钱!”唉,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当一次“憨佬”吧。想不到在重庆看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一个什么楼的时候,他们又被当成“外宾”而要付高价门票。气得这位“广佬”一个劲地骂着:简直是盆地意识!
喜欢思考的读者大概会提出问题:“广佬”们所表现出的现代风,其实好多都是从香港“拿来”的。他们对“北佬”怨也好,“哀”也罢,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管是“广佬”还是“北佬”,大家都处在追赶“四小龙”的跑道上。相对于北方来说,广东是领先若干步,但相对于“四小龙”以及世界上发达国家,无论南北,都差一大截!
而今我谓南北
对于已存在的南北差异这个话题,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而笔者从选择这个题目作文章开始,就暴露出“扬南抑北”的倾向。其实,笔者本是地地道道的“北佬”,不过由于南下从军后转业未回原籍而成了“准广佬”。笔者实实在在地认为,如果真的要用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来形容“广佬”对“北佬”的态度的话,那么应该去掉这个成语原来所含有的贬义成分,让“广佬”好好地笑一笑“北佬”,从而促使“北佬”憋着一口气,努力苦干,争取赶上甚至超过“广佬”,至少不要让差距越来越大。
许多“北佬”朋友爱用文化作标准,说“广佬”们大都是钱袋满满,脑袋空空,“穷得只剩下钱了”。但是,“广佬”们在经济改革舞台上表现出的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敢于“拿来”的气魄,以及不为风浪所左右而一门心思搞经济的专一精神,难道不正是一种文化一种素质吗?如今所有人都承认“商品经济是个大学校”,而在珠江三角洲,就连拾垃圾卖咸酸的老头小孩都具有商品意识,你说这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再说,假如“广佬”人人都有很高的文化,又何须引进“北佬”人才?其落后的方面正好为南下“北佬”提供了用武之地。
有一首诗写得好:你是北方的白杨/我是南边的垂柳/你用你的挺拔/我用我的俊秀/绘出这世界我们的共旨……
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