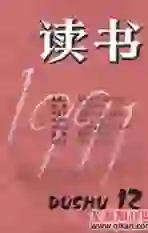三种用途
1991-07-15王依民
王依民
由于《<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是钱锺书先生两部最重要的学术巨著的索引,所以它对研究者来说,比一般的索引工具书多了几分用途。这用途大致有以下三种:首先,它的直接用途是有助于研究钱先生及其学术思想。郑朝宗先生的《序》说:“钱先生是以学识渊博著称的,读他的书的人不仅乐于听取他对学术问题的意见,同时也渴望知道他究竟精研了多少古今中外典籍,接触了多少古今中外作者。”这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因为根据这份书单和名单并统计其被征引的多寡,可以分析钱先生的学术结构,推断钱先生的学术渊源。譬如我们看到钱先生大量引用老庄、禅宗书、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如普洛提诺、爱克哈特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著作,也许可以看出他辩证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倘再进一步细检他大量引用的《论语》、《周易》和上述著作,更可以理解他的辩证思想一与不一或易与不易双行双遣、执其两端而得乎中的思辨特色。又如我们看钱先生较多引用莎士比亚、列奥巴迪、蒙田、培根、格列尔巴泽这一类西方作家,而没有引用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对照他自己的创作特色,也许能参悟他艺术趣味的某些方面。其次,这份名单和书单可能是一份最好的中西文化史阅读指南。初学的年轻人如果根据钱先生的征引量来选择自己的阅读范围,一定会读到最优秀的著作,分清该先读什么书,后读什么书,就能起步正,取法高,在学习上不至于走弯路。有一定学术基础的人也可以对某些人或书推究一番,如英国十七世纪文家蒲顿(Robert Burton)的《解愁论》(Anatomy of Melancholy)似乎在中国不算是一部显赫的名著,为什么钱先生一引再引达数十次之多,仅次于莎士比、亚黑格尔和《圣经》?这是钱先生的偏向?还是它蕴藏着一座富矿?倘若推究不出所以然,我想会有人鼓起勇气去啃这部又厚又大的书吧?或许还会有出版家鼓起更大的勇气去组织翻译出版吧?第三,有助于研究中西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研究专人专书。傅璇琮先生曾经说过,今后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钱钟书研究》第一辑,第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是很中肯的。我想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历史、语言等学科的研究者,恐怕也适用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者。了解钱先生研究成果的办法,当然莫过于细研他的著作。不过有了这部索引,当会弥补我们记忆能力的不足,减少我们的翻检之劳;并且在研究专人专书时,可以集中检读钱先生的所有论述。以上所说的三种用途,也可以说是使用这部索引的三种方法。
据说写书和出版是遗憾的事业,那么我觉得本书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即《谈艺录》的索引稍嫌简略,因为这部分只有人名索引而没有书名篇目索引考虑到本书的篇幅,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至少一些专书应当立目并入人名索引,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少索引都有这个先例,不妨依循。《谈艺录》引用专书和释典一般按照惯例均不标出作者姓名,但这些书恰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惟其重要,才为人所熟知,故无须标举作者姓名;它引用一些最著名的别集、笔记,如《朱子语类》、《日知录》等等,也常常不提作者。现在没有书目篇名索引,就把这些最重要的内容遗漏了。例如《庄子》在《谈艺录》中出现近三十处(每页复出以一次计,下同),《五灯会元》二十余处,《文心雕龙》、《大智度论》、《宗镜录》十余处,《诗经》、《论语》、《孟子》、《淮南子》、《史记》、《论衡》、《世说新语》等等五至十处不一,现在无从检索,不能不说是颇为遗憾的。
(《<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陆文虎编,中华书局一九九○年三月版,17.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