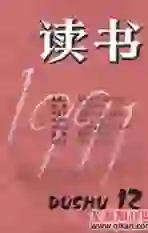“持续”与“汇合”
1991-07-15黄仁宇
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陆版序
这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前后连贯,通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纪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
自明朝至现今的一段,原拟定也照同样体裁叙述,出版者还盼望我出一本《赫逊河畔再谈中国历史》。只因历史的进展成螺旋式,愈至后端积累的分量愈重,内容也更复杂,其内容不容易保持文艺副刊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几种工作,不容易摆脱。所幸已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英文本Chian:AMacro-history(中文本题为《中国的大历史》,可望于年内出版)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已编排完毕,即将出版,英文本也在编撰中),都由作者执笔。读者不难从此中看出,上述前后连贯的特性并未因元朝而中断,也因明清而持续迄于今日。而且在二十世纪末季,中国的历史也确切的与西洋文化汇合。
对大陆的读者讲则因上述书刊尚待问世,刻下有将所谓“持续”及“汇合”两点扼要作梗概的报告之必要。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个到二十个的小朝代,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我们仍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的和有系统的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豁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
朱元璋创建明朝,他的种种措施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实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造成行政之张本,结果节节失败,却没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带服务性质的事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没有展开,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他只凭己见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范围的说法即是“与民争利”和“聚
明朝的财政与赋税以较落后的部门(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为基础。三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时又全面恢复,而以人身服役为原则,即各级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补修理均无预算之经费或供应之承办者,而系无费由各地里甲征集而来。朱元璋更利用“胡维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狱去打击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一三九七年户部报告,尚有七百亩田产以上者,全国凡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其名单也进呈“御览”。如此造成全国皆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庞大之扁平体,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挥,虽有短期间之平等,而缺乏经济上之组织与结构。
唐宋时之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物资周转,明朝放弃此种办法。朱元璋的财政体系成熟之后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的短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以接受二三十个县的接济;一个县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机构交纳财物。户部不再成为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会计衙门,只能核销小数目此来彼往的供应,无从筹牟全局的重新分配,本此情形之下,服务性质的事业也永远无法展开。大凡现代化之前,民间的经济组织有赖与政府官衙交往开始。意大利的银行家即因代教皇输纳各地的十一捐而发韧,日本的“藏元”和“两替”也系承差于幕府及各大名,才开始出头露面。中国明清间的商人始终无此机缘。
过去有些历史家以为明后季行一条鞭法,朱元璋的财政税收体系,即已改进。殊不知财政与税收为承纳于一个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法制性的连系,牵涉到官制与兵制,以及乡村里甲和城市街坊间的结构,也与法庭判案的能力与社会风尚全都有关。明清的制度,既然如此之特殊,如果一经更革,则以上各种因素全要更革。一条鞭法只是各地会计制度局部间的修正,与全面更革的范围相去至远。五十年前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其结论则是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我们也可以更大胆的指出虽有明清之交替,康熙时将丁额永久的固定,雍正时的火耗归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税收开始出现,剿办太平天国期间开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之财政仍与第三帝国全始终。我们只要从鸦片战争时支持扬威将军奕经的军费,和甲午中日战争前供应北洋舰队的经费即可看出:清代承明之旧,只有零星支付局部需要的能力,而无全面经济动员打破局面之可能性。所以从长时期远距离的角度看来,明清之体制为一元。
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可是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附带申明:这种观点只因我们在六百年后体验到,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国家不能适应于外界新潮流之创痛,才能产生。在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决策时,一般人士未尝不以之为得计。一个大陆性格的国家动员时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企图长期保持各地区间之平衡,不计较对外折冲时一时一地的祸福得失,都有它特殊之逻辑。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为全国的标准,并不完全是缺乏头脑,明朝即为中国惟一之朝代其用兵由南至北而统一全国,而且因为其资源零星搁置,各地的总督巡抚无从跋扈割据而尾大不掉。有明一代除了有几位王室人物和农民造反外,并无文武官员拥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像嘉靖朝的张经和崇祯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纸文书的逮捕,随意处决,为以前所未有。而承着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之外,清朝又继续如此的纪录达二百六十七年。除了所谓“后三藩”,系明降将曾举兵反之外再无一个重臣背叛朝廷,这样的纪录为西方之所无,在中国也仅有。因为其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待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会价值(social value),所产生的社会秩序,以“尊卑,男女,长幼”作纲领,有替代法律之功效。虽说今日我们已不能欣赏此作风,也知道其标榜不尽符合事实,却无法否定其为地缘政治下之产物。本书已一再提及中国反映着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读诗书之士人统治大量农民,无法应付变叛(variables),所以才强调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这些特点都因明清帝国而发展到尽端,直到鸦片战争才彻底暴露这样的体制不能在现代社会里存在。
一提到现代社会,则当中端倪纷纭,可以发生无限的争执,我个人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根据着居留在英国、日本、美国和旅行其他各地的经验,则发现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程序,当中无不有一个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在数目字上管理亦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的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的原则,零星杂碎地去权衡各人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之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这体制上之改变,绝非轻而易举,通常有类于脱胎换骨。大凡近世纪各国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流血不止,通常与这种改变有关。一待某一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种数字,尚可以随时商酌,大体上以技术上的要求作主,不必笼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了。
说到这里,我更要提醒读者: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并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本来也是“气数将尽”,这也就是说专制政体全赖人治。当初皇帝如康、雍、乾日理万机,还能称允文允武,以后之君主实为典章制度之囚人,况且宫闱间的纠纷与黑幕愈多。及至慈禧太后主废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之一代不如一代,已难能维系人心,遑论及忠臣烈士之“死社稷”,是以本来即有覆亡的征象。再则参入这“换朝代”的机缘中又有了一个“改造帝国”之必要。明清两朝合并为五百四十三年,也和第一帝国之四百四十一年及第二帝国之六百九十八年(内有五代十国之分裂局面五十四年)大致上等量齐观。这第三帝国既有收
所以中国的长期革命,费时必多,为患必烈。法国“老虎总理”克里曼梭曾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亦即一经发动,玉石俱焚的公算极高,很难照应到各人各事内在的公平。康梁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自愿牺牲,即是已经看穿长期流血之无可避免。
但对中国事情,当时只有极少的人能看到全局之高低纵深,大多数人士只能随着内外压力,一步逼一步,逐渐觉悟到大规模改革之无可避免。迄至辛亥革命之后,肇造民国,犹且不能解决问题,才有五四运动之展开,知识阶级觉悟到改革必从本身着手,及于文化和教育。
我曾在《万历十五年》再版(一九八六)之跋,称为“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写出:国民党专政期间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共产党则因借着土地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集团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之间敷设法制性之联系。这样的程序,也和所有产业革命先进的国家之所经历符合。其最后的目的则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能做到这地步,中国历史即已与西洋文化确切的结合。大凡管制人类群众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劝,由神父牧师及政治指导员主持之。二是武力强之就范,受军队巡警法庭的操纵。三是策动各个人之私利观(我们也可以强调其为开明之私利观〔en-Iightened self-interest〕),于是各个人赴利避害之间,即已间接的趋向于集体的目标。以上也带相对性格。迄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只采用一种方法,即能将其他两种方法完全摈弃。
最后我希望与本书读者共同保持一点检讨中国历史的心得,此即当中的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很多骤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看来却仍合理。中国既已在二十世纪几乎亘全世纪的尽瘁于革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殊死战八年,即已打破四千年的纪录,在人类史上也是仅见。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亦超过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时间的平等,而在给新体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现在进入建设时期,应该能克服困难,使国家资本有民间经济作第二和第三线的支持,在新世纪里成为一种稳定全世界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如此,我们衷心希望如此。
一九九一年二月于纽约州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由三联书店在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