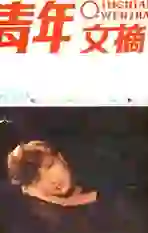伴着朝阳向前走
1988-11-01屈明光先燕云
屈明光 先燕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球医学领域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医学的两大组成系统发展畸形,诊断技术依靠高科技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突破,而治疗技术却长期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人类却梦寐以求“生病不吃药”的自然疗法。于是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预言:疗效高而无副作用又方法简便的自然疗法,将只能在21世纪诞生。
然而未曾想,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解决了这个难题,打破了这个预言。
一时间,他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
他叫周林。1954年出生的人。
潮湿,阴冷。上海的冬天。
周林的手冻了,红肿溃烂。听课,抄笔记,一双手总是裸露的。擦药,变着法儿地打听偏方,总是无济于事,又疼又痒的手背,真让他吃够了苦头。如果是学医的,他恐怕那时就动开了脑子,可他学的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是上海交通大学三系的学生。这一年,是1974年。
春暖花开,冻疮自然好了,手背上,却留下了一块触目的伤疤。
“冻疮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他找来资料,想闹个明白,结果令自己大吃一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盟军部队,就因冻疮冻伤非战斗减员一百万。
一个问号,接一个惊叹号,在周林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1978年冬。寒风呼号,夜色沉沉。
在距昆明30公里以外的群峦叠嶂的山坡上,一个人正蹲在一个装满凉水的铁桶旁边,把双手久久地浸泡在水里,时而又把两手抽出任凭寒风吹刮。泡了又吹,吹了又泡。双手发麻,疼痛钻心,浑身颤慄,手指手背痒痛的红点变成了肿胀的斑块,可他仍在浸泡着、浸泡着……
这人正是周林。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脑子里时时装着“冻疮”。查资料。节衣缩食买电器元件、化学原料。左一个设计,右一个方案。一台能够模拟人体频谱的冻疮治疗机,由这个年轻人研制出来了。
眼下,他正在人为地制造冻疮。肉体虽然有着难耐的痛苦,他心里却乐滋滋的。因为这冻疮是他经过无数个寒冷的夜晚的苦战得来的“成果”。
他急忙奔回小屋,接通电流,把双手伸到机器下面。奇妙的现象出现了:第一次,20分钟,痒痛消失,一块块流过脓的创面干燥了;第二次,又用20分钟,鲜嫩的肉芽上覆盖了痂皮;几天之后,痂皮脱落,满手的冻疮痊愈了!
年历已换过好几本,此时是1983年冬天。
周林已调到云南轻工业研究所。他带着自己五年研究的成果,满怀希望地来到所里。他认为,现在面临的是推广问题。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搞什么冻疮治疗机,不务正业!”
“你那个东西有什么推广价值?倒贴钱也不值。要干,就请离开研究所。”
火,碰上了水。屡番碰壁,险些碰扁了鼻子。冷冰冰的面孔下,是冷冰冰的心。不理解可以逐步理解,要命的是压根儿就不想理解。周林的船还未驶出港湾就面临搁浅的危险。
正在这时,来了这场大雪,据说是500年罕见。难道是天公助他,冻疮患者激增,好机会!周林和助手王杰,拉来铝板,自己动手,赶制机器,在南屏街上开了个临时门诊点。3人操作20台机器,一开张,马上买卖兴隆。机器不停,人也不停,中午啃点馒头,直累得头晕眼花。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光春城就有这么多的冻疮患者;昆明的冻疮患者也才知道,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机器,能制服又疼又痒、钻到心窝里去的那份痛苦。
白雪,轻柔地飘洒。
忙碌中,周林心头不时袭过一阵阵担忧。妻子产后热卧病在床,儿子又得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母与子,此刻怎么样?
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几天下来,小伙子手瘫脚软,走路发飘。翻翻记录,嗬,共治愈2951人。
专家给治疗机以“见效快,疗效高,明显优于目前国内常规治疗方法,值得大力推广”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国家新产品“金龙奖”。
冻疮治疗机的传说不翼而飞,飞到了遥远的北国。
大雪后的那个春节,周林和王杰飞赴沈阳。正月天,传说可以冻掉鼻子。就凭着部队这份需要,这份信任,他们豁出去了。西南到东北,在中国的版图上划了一条斜长的轨迹。
大年初五,俩人走下飞机。好家伙,一下子和掉冰窿里差不多,身上的衣服在北风里跟纸一样,直往里透风。10多台机器分6个点使用,他们马不停蹄,顶风冒雪,奔波在赤峰、哈尔滨、旅顺、大连……
结论出来了,冻疮治愈天数为两天,治愈率达98.99%。
有人说,周林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困难时的信任和支持,比成功后十倍的热情更为可贵。但是又有这样的说法,周林“六亲不认”。
有情无情,毋需赘言。请看——
1985年4月,《中国青年报》刊登文章《一个待结尾的故事》。文中人司德林瘫痪在床,长满褥疮,烂至骨头,危及生命。两名自愿帮助他的女护士,只能天天为他清洗疮口。
周林读不下去了,放下报纸。妻子张雪珊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应该帮助他。”是呀,他想说的,正是这句话。可他自己,那时被迫离开工作,薪水全无,一家三口的生活全仗着妻子那50多元工资呀。
一定要帮助他!周林挤出钱来,自己装了一台简易治疗机,航空快件托运到了北京。
司德林的褥疮痊愈了,来信报喜。9月份,打听到周林要参加全国发明展览,他赶来了,如果他看到周林拖着尚未恢复的病体,背着60多公斤的展板,从团中央一步一步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布展,不知他会如何想。别的人都雇车拉展品,大概也就五六元吧,周林掂量了一下,不行,没钱。咬咬牙,展板就上背了。
司德林从报纸上知道了周林的困境,一见面,他抓住周林的双手,淌下了眼泪。周林没见过他,有些纳闷。“我是司德林,我好了,没想到你自己的处境这么难……”
周林也确有无情的时候。让他自己来说好了:“我真正对不起的人,是我的儿子。”神情中,饱含着辛酸与内疚。
当你一见到这孩子,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爱画,大人们开会的时候,他静静地趴在桌边,眼睛几乎贴在纸上,画一个圆,画一道线。“怎么,两个发明家,不能治好自己的孩子吗”孩子妈妈的那双美丽的眼里,流淌出一种痛苦,那么深,那么沉……
在大观幼儿园的儿子,时常被父母“忽略”,以至小朋友们全走了,仍坐在值班室等着爸爸妈妈。
1985年9月,孩子发高烧,整整病了一个月,体温常在40度。紧接着,孩子不能走路了,一走路腿就疼。这时候,周林自己才从重病之下逃脱,事业正逢关键时刻,又处在所里“停发工资,停止工作”的艰难日月,真的焦头烂额。
早上四点排队,领孩子看病,一家医院接一家医院地跑。医生见这孩子大脑袋、漏斗胸、下肢发育不好,疑惑地问孩子的父母:“这孩子怎么象困难时期出生的,你们是生活困难还是离城太远?”
小张哭了。真的,两名大学生,一个独苗苗,岂有不疼不爱之理;小张本人就是昆明医学院的老师,又有什么不便。如今的孩子,已有营养过剩的趋势,偏偏这一个象困难时期里的,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呀?
就在这种时刻,周林接到了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国参加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世界青年发明展览的通知。
灯光下,张雪珊和妹妹,连夜为他赶制出国穿的衣服。别人出国有公费购买服装,他没有。一针一线,是张雪珊抽着心丝缝起的。
带着双重忧虑登上远行之程,他全没有出国人员那种志得意满之色。
凝望着丈夫的张雪珊,心头有许多话,到嘴边,却只有一句:“不要想不开,我们有许多支持者。”
北京。出发前7天,小张的电话追到了周林:“孩子又病了,外婆被撞伤,我又安排了上大课……”声音哽咽着。这个聪慧的坚强的女性,终于感到了惶恐,感到了孤立无援。
“我不能回来,没时间,也没钱,只有靠你尽力了。”话筒里,电流传送着周林焦急的、无能为力的回答。
继冻疮治疗机之后,周林又不断开拓,研制出了WS——频谱多功能治疗机、呼吸道治疗机、关节炎治疗机、鼻炎和喉炎感冒治疗器、妇产科治疗机、生物反馈血压调整仪、动物保健治疗装置等10多种医疗仪器。在成千上万种医疗器械中,他的发明是唯一获得中国国家发明奖的治疗仪器。
1987年3月。瑞士巴塞尔。第7届国际自然疗法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瑞士、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周林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
周林到达的第二天,瑞士巴塞尔报便登载消息:“周林来了,他总在微笑,只有他才知道治疗机的秘密。”
同样,周林免不了要治病。
瑞中友协主席欧文患哮喘病10多年,用遍欧洲的名药,均未奏效。经三次治疗后,呼吸通畅了,睡眠也好了。
侨居瑞士的一位开饭馆的中国人,长期当厨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手腕、手臂不能抬起,欧洲名医均未治好,他只好从香港寄膏药,但肉都贴烂了也不见好。这回仅治疗三次,他的手腕、手臂就活动自如了。
最有意思的是,瑞士发明者协会副主席卡瑞,专门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系,要求请周林为他夫人治病。这位夫人于26年前作心脏搭桥手术,手术成功了,脚却开始溃烂,下肢循环不畅,请遍欧洲著名医生,结论是:不能再治好了,只能采用人工皮,进行保守疗法。因此只得一直雇请私人医生,采取被动治疗。
为了中国的声誉,周林去了。
谁知这位老夫人却说:“我已经和私人医生商量了,不能让中国人来治。中国人只有红茶菌和巫术。”
退却,意味着让整个中华民族蒙受蔑视。周林知道,他是代表中国而来的。于是,他平静而坚定地回答:“你丈夫知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不相信,我愿以一级骑士勋章为证。”
私人医生妥协了,但丑话说在了前头:一旦出了问题,周林要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他不提供任何消毒设施,如果被感染,他一概不负责。
周林答应了。
周林让老夫人撕掉美国研制的人工皮,露出了一个很深的溃疡洞,脓血即刻向外流淌,奇臭难闻。周林给老夫人清洗干净了。
十分钟治疗后,周林问她感受怎样,她说感到有无数钢针扎射进患处,向全身流动,这是多年没有的情况。
又治疗40分钟,天色已晚,周林便告辞了。
第二天,周林通电话询问情况,老夫人回话:多年来一直冰凉无知觉的脚,昨天一晚上都感到很热,难以入睡。
周林坚持前去察看。打开纱布,看到再也没有新的渗出液,并且结痂了。
周林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私人医生当即表示,同意周林继续治疗他的这位病人,并把全部医疗费用转给周林。
卡瑞先生高兴地宣布,他愿作为代理商,负责在整个瑞士推广周林的治疗机。
老夫人发出了恳求,希望周林长期住在她的别墅,为她治病。
周林婉言谢绝了:“我不能这样。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需要我回去治疗。”
在瑞士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部部长为周林签字:这项研究是中国对人类、尤其是对贫穷国家的一大贡献。希望中国能提供价格便宜的机器,以援助贫穷国家。
……前前后后算起来,周林共获得了9次国际奖。他成为了我国在世界上获奖最多的发明家之一。真正不简单!
在国内,周林自然成了新闻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次次地登载关于他和他的治疗机的消息。
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全国青联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昆明青年十杰之一……
接见、握手、拍照、讲话……
他真的置身在旋风之中。换个人,早觉得功德圆满,便可躲进光环中,稳稳当当地生活,品尝荣誉带来的甜蜜了。然而他偏不,好象总是自找苦吃。对荣誉,他不愿多谈,就象不愿多谈自己一样。
对了,他只有34岁,抛开职称和头衔,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然而,他又是一个不寻常的青年,他前边的路,还很长很长……
(原载《科技日报》本刊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