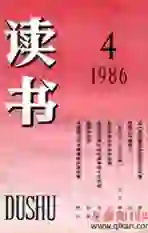编后絮语
1986-07-15
读书 1986年4期
据说,粱启超当年向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有没有著作,粱均作否定的答复。校长表示,这样的人进“清华”是难了。任公听言愤,然作色曰:“我粱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段故事,素为治学术史者所称道,因为它说明学问与学历不能绝对地等量齐观。
这道理也能用在办刊物上。讲学问,说道理,自然无如写一篇学术论文来得透辟、周全、响亮,可能因为这个原故,广征博引、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现在比较容易组约,可是要请求写一篇“言在书中,意在书外”的书评,一则廖廖千字的“品书录”,有时反而困难。作者不是不帮忙,实在也为难:你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我评上学位或职称吗?
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是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给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
领会学术,吸收知识,有正常的途径:各种学校,讲义教材,学术论著……这如同是过去仕进的“正途”,不可忽视。但是为学也往往有“别径”,那就是不拘形式,不限格局,只求心领神会,不在背诵记忆,更不要什么教条、陈规了。
只因有这看法,我们编《读书》几年,只觉得文章写法还不够杂,篇幅还不够小,整个说还不够多样,却不觉得非要把自己挤到“正途”去不可。自然,也因此吃了苦头:创刊未久,就有一位同志到编辑部来,要求退订,因为发现这杂志无助于孩子考大学。这位同志是对的,错在我们向读者说明不够。
明乎此,则读者尽可自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