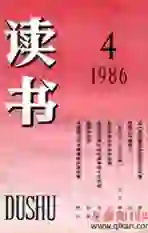从一件事看领导者应有的风度
1986-07-15洪禹
洪 禹
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有一封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给我的回信。有的同志要我写点当时的情况,写点感想。但也有同志认为,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还来歌颂毛泽东同志是否合适。我觉得,人们的经历不同,对同一件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如何评说,由谁来评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做出了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就是,一个人的功绩不能掩盖他的过失,同样,他的过失也不能淹没他的功绩。
几十年来,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因为从这里,我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风度。它给了我一种持久的勉励和鞭策的潜在力量。
毛泽东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洪禹同志:
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很久就收到,报对你不起,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在关于你本人的具体问题上,当然这是你一方面的声音,而别方面的我还未听到;但是我觉得你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确是我们的党组织值得注意与必须注意的。因为今天离你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半月,在这期间内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去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给我的信付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
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大多了。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我觉得,毛泽东同志的情,是给我,同时也是给许多被错打成特务的同志,在政治上的平反。
记得那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和一些同志刚从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晋东南鲁艺口到延安鲁艺,当时,我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文学系研究室搞研究工作。不久,在以康生那本小册子《抢救失足者》为信号的抢救运动中,由于运动没有严格遵照党中央规定的“九条方针”进行,使得一些单位产生了“左”的错误,从而把许多同志打成了特务分子。我就是其中受害的一个。
对于那些真正受骗上当,当了国民党特务的失足青年,是应该抢救的。但是,把经过千山万水,沿途冒着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风险,好容易才到达延安的革命同志,当作反革命加以抢救,却是个悲剧。
万万没有想到,一些搞“抢救”的同志,居然对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搞车轮战,搞逼供信。在数九寒天,深更半夜他们把我从被窝里掀起来,冷得我直打颤,但他们说:“你没有问题、为什么吓得发抖”?他们只知道有问题的人会吓得发抖,却不了解真正的反革命,有时会故作镇静;他们更不了解,没有问题的人,遇到这种突然袭击,不但会冷得发抖,更会气得发抖。他们捕风捉影,有时会使你啼笑皆非。如他们质问我:“没有问题,为什么总是用广东话同你的爱人说悄俏话?”我说,假如我是特务,不说广东话,也是特务,不是特务,无论说什么话都不是特务。可是在当时,在康生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下,连这样最普通的道理,他们都听不进去。
审查我的同志,曾逼着两位所谓小特务来同我对质。当那两位同志承认我所说的,我和他们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别无其他关系这一客观事实之后,主持对质的同志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拍案而起,训斥那两位同志:为什么见了“特务小头子”就吓回去了,等等,一位参与“抢救”的知名作家,竟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在窑洞里拖过来推过去,并且用他的文明棍极不文明的狠打我的脑袋。我提出抗议,他却说:“如果以后证明你不是特务,我向你赔礼道歉,你还可以打我”。
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曾详细交代我的历史。一九三三年我在福建厦门大学附中先后参加读书会、远东反帝大同盟、共青团(CY)。后来,因为当地组织被破坏,两位直接关系人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先后被捕而失掉关系。在白色恐怖下,我离开厦门,于一九三六年到广西重新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并且加入了那里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一九三八年经地下党同志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大”、“鲁艺”学习,然后到敌后根据地工作。一九四三年组织上决定我和一些同志再回延安。总之,我用大量事实说明,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没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用,审查的同志居然把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经历说成是假的;把我在敌后严酷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过程中一切好的表现,都说成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伪装进步打进革命队伍的一种手段。总之,他们对我的历史一笔抹杀,全盘否定,并且说,他们是不会错的,说要是在整风以前,还可以说他们可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现在经过整风,再也不能说他们主观主义了。这些同志还反复说明,他们是代表组织代表党的。就这样,他们主观的判定我是反革命,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党中央发布命令,要我们的队伍向广大的沦陷区“星夜进军”这样的形势下,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申诉信,诉说我的冤屈和他们的种种错误观点和做法。
我在信中说:我以为,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不是被真正的敌人抓住,而是革命者被自己的同志当作反革命对待。我不是反革命,正如一部苏联小说中所描写的,我是“布琼尼将军的士兵做了布琼尼的俘虏”。他们这种唐·吉诃德战风车式的“抢救”能代表组织、代表党吗?我以为,最可怕的敌人,正是这些同志头脑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把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倾向革命的朋友,甚至是介绍我到延安的地下党员,都看作是不可信的,都不能作为我是革命者的证明人;相反,对于一个曾经被捕、写过悔过书,后来仍然同情革命的朋友,却被他们断定是坏人,并由此断定我也不是好人。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推理和判断,是不能说服人,经不起反驳的。因为即使我的那个朋友真的变坏了,又怎么能够把我同他划等号呢?究竟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特务,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正确的郑重的做法,只能根据我的全部历史和思想言行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但是他们把凡是工作中表现好的都看作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凡是有缺点错误的都看作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按照他们这种观点和是非标准去看人,还有谁会是好人呢?至于他们靠逼供信,靠对质来断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就更成问题了。万一对质的同志一口咬定,而组织上又据以定案,这岂不是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任意交给随便什么人去判决了吗?
我在信中还说,在抢救运动之后,我仿佛是自由的,因为再没有人日夜看守着我,但是我仍然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控制着我,这就是他们既不公开宣布我是反革命,也不宣布我应予甄别平反,而是采取长期拖下去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做法无论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这只能伤害无辜、制造混乱,绝不可能帮助党组织弄清问题。我希望党中央关照各级党组织密切注意,千万不要因为革命节节走向胜利,就以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因而可以对受审查的人任意处置,或者置之不理。我以为,党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十分细密的关于人心的组织工作,任意对待受审查的人,后果不仅仅是一两个受到粗暴对待的人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给毛泽东同志的申诉信,是我直接送到当年他的住地王家坪的。他将怎样对待我的申诉,我无法事先知道,我在信中说,我知道他很忙,不可能管我这么具体的事,我只希望他听到我的声音,知道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象我在运动中遇到和见到的种种使人难以忍受的情况。
没有想到,我的信不但没有石沉大海,也没有退回原单位。毛泽东同志深知被当作反革命的人,是收不到他的亲笔信的。他派警卫员把回信送到我手上。
在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以后,我极度兴奋,反复阅读。他的信使我从郁闷、愤懑和过度的精神紧张中解脱出来,满腔热血又重新沸腾起来了。我从信中感到毛泽东同志诚恳、谦虚、信任和尊重同志。感到他的确是反对主观主义、支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他的信充分说明他相信从国民党统治区跋山涉水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投奔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正如当时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同志说的:“如果有那么多的特务,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在延安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毛泽东同志的信,我的所谓政治问题,不知道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能解决,甚至有可能长期“暗挂”下去。因为那些审查我的同志,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是他们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精神状态,使他们总以为自己正确。
当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去找安部长的时候,他热情的接待我,说关于如何解决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在经过复查、组织上给我彻底平反之后,我写信把结果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说明由于复查同志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澄清了莫须有的问题,恢复了我的历史本来面目。从此,我结束了革命者被当作反革命对待的日子。组织上把我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工作,接着让我参加中央工委工作团,跟安部长一起搞土地改革。一九四八年底,组织上又让我报考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
毛泽东同志不仅解决了我的政治问题,当他知道许多同志被搞错了的时候,他就公开向大家赔礼道歉。记得当年在延安大学礼堂,毛泽东同志曾脱下帽子,深深地向大家鞠躬、表示很对不起被搞错的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是对的,我们错了。”毛泽东同志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和许多同志。当时,许多同志是含着激动的眼泪对着毛泽东同志的。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风度相比,那位曾经对我进行武斗的知名作家,却是另一种风格。他在五十年代中央直属机关党代会期间,同我编在一个小组,当他在会上见到我时,似乎有点尴尬,这说明他也是感到内疚的,但却又做出一副似乎从来就不认识我的样子。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所走的革命道路不是平坦的。十年动乱时期,一些想使历史悲剧重演的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在延安时期被某某放跑了的特务。我曾提到有毛主席的信为证。可是有人偏要说:“当年洪禹根本不可能给毛主席写信;即使写了,毛主席也不可能给他回信;即使回了信,也不可能保留到今天。”并且说:“有也是假的。”他们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当然,事实终归是事实,一切诽谤只能说明,在某些人的头脑中,那种历次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左”倾顽症还在继续。
从事情的全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绝不象有些不吃人间烟火食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连职责所在的事都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更不象“文革”时期人们所常见到的一些人那样,只要你提点意见,就说你猖狂反扑、攻击革命群众运动,从而给你罪上加罪,使你长期受冤、没完没了地对你进行批斗。
毛泽东同志对我这样一个受冤屈的、在当年既没有重要身份和地位,素不相识的普通党员,从政治上给予如此周到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正因为比起整个中国革命所要处理的问题来,个人问题毕竟是一件小事,但是毛泽东同志却没有把它当作小事,而是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做了妥善的处理。我感到,为解决我的问题,他象部署一个战役那么切实、细致和周密。毛泽东同志这样做,不仅是为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为我们全党树立一个正确对待人对待问题的榜样。这就是我在延安时期看到的毛泽东同志的领袖风度。这样的领袖风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我深深感到,千百万人民群众,所以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跟着共产党去进行革命斗争,或者说,中国革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离开领袖人物那种紧紧吸引着群众的强大向心力是不可想象的;相反,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给我们全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我们的党组织更加健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少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多了,即使领袖人物犯了错误,也可以减少或避免重大的损失,个人问题,即使没有领袖人物的干预,也同样可以及时得到合理的解决。我认为,只要实现了这种质的飞跃,我们的党,必然是更加有力量,更加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