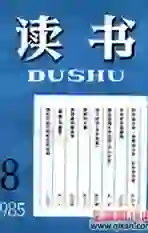研究人 再现人
1985-07-15叶式生
叶式生
五十年代后期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曾经极大地改变了数以万计的人和家庭的命运,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专用名词:“右派分子”。它的政治分类意义可说是尽人皆知的。但它所指称的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样子?他们怎样生活?天天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特别是,想些什么?他们怎样成了“敌人”,成了之后又将怎样?……所有这些,不曾身历其事的人们就难于详知了;众多的后来者自然更是很少知道。《北大荒的呼唤》以一组互相关连又能各自成篇的“系列小说”,构成了一幅形象鲜明而各具性格的“右派”群像。十分可贵的是,作者的笔始终严格遵循着现实主义的轨迹,丝毫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去有意无意地美化、拔高她的人物,或出于某些非艺术的考虑而去再造历史。这些人物虽然用墨多寡不同,却都是可触可感的血肉之躯,当年不是“鬼”,如今也没成“神”,而始终是人,人所具有的他们无不具有。作者几乎完全不用什么奇笔,也很少有意设置什么悬念,但她所描述的一切却又使人感到那样奇特,那样出乎意料,甚至不可思议。这奇特从何而来呢?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所谓“人学”,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研究人的学问;再现“人”的艺术。《呼唤》所以能生动逼真地再现出一系列“人”,同作者对人的认真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研究,突出表现在对人的性格变异的探索中。
正如环境温度和压力的变化会导致物态变化一样,人的性格状态在社会温度和压力变化时也会出现异常。一对交好多年的朋友同时升迁,一个清醒如昨,知道自己仍是自己;一个头昏脑热,眼里骤然消失了一批故人。两个慷慨激昂的斗士一朝同陷逆境,一个消沉沮丧,一个自强不息。这种种性格突变实则都有其内在依据,人们对之感到惊讶不过是由于原来环境的局限,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处在不完全的、较低的层位上罢了。在平常情境下,人们的性格深部大抵都有某些角落处于闭锁状态,只是多寡深浅不同而已。这种闭锁又不尽是“自为”的,面往往是“自在”的,以致人的自我意识都不易察知,别人自然更难于发见。只有在非常情境下,某些闭锁角落才会打开,使性格深部的某些潜在素质升华或裂变出来,形成性格突变的表象。正是这些表象的突变,构成了人的性格发展曲线上的一个个关节点。对这些关节点进行探索剖析,并在清晰逼真的相关背景上将它们放大描绘出来,则可以说是“人学”即文学专擅其长的功能,同时也是其最为精细复杂的一项任务。《呼唤》的作者在这方面的严肃努力和认真探索,我以为正是作品中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性格刻画得既鲜明逼真,而又富于动态的最重要原因。掩卷回味,我们自能发现:那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性格,特别是这些性格的变异和发展,无不在不同角度上深刻着一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和自然环境打下的印记。
人和人是需要沟通交流的,越是境遇悬隔的人,这种沟通交流也许就越重要。《北大荒的呼唤》这部作品,所描写的虽然都是些当年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但无论对过来人还是后来人,了解他们都会是有益的。从这些人物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的潜在的力和美怎样在“低温高压”下升华,种种密封的恶和丑又怎样在同一环境中裂变;可以听到历史和民族沉重的脚步声,听到爱和希望呼唤……
(《北大荒的呼唤》,陈瑞晴著,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