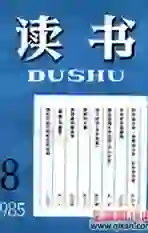神酣意热话《醉乡》
1985-07-15凌宇
凌 宇
健忠同志:
《醉乡》我读过了,而且不只一遍。从记忆的库存里,我极力去搜寻一种已经出现过的小说模式(包括你过去的作品),以便拿来与《醉乡》比较。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形成了这种习惯。这几年来,我读过不算太少的作家的新作,读过之后,常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某种类似的模式下意识地叠印在这些作品上。我丝毫没有贬低这些作品的意思,文学创作中的相互借鉴实属常事。然而这次,搜寻的结果使我失望,我找不到我需要的模式。——《醉乡》在整体的格局上,是一种创新。创新是被批评家用滥了的词,用它来评价《醉乡》,我真有点惴惴不安。但愿不要因为我的孤陋寡闻,造成基本判断的失误。
你端出的是一碗乡下人家酿的酽酽的“包谷烧”。读完《醉乡》,我强烈地感到一股热流从心头涌起,并向全身流布。真想嗬嗬地哭一场,又哈哈笑一通。……凉风沿山谷吹来,心头升腾起不可言说的快感。这种感受在我读过的你先前的创作中是得不到的。我读过你的《五台山传奇》《乡愁》《甜甜的刺莓》和《水碾》,读这些作品,犹如吃一碗凉粉,或者掺着山泉水喝一碗江米酒,爽快、舒适,却不过瘾。这些作品归根到底,大抵是一种历史的反刍。正如你自己所说,是“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昨天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的思辨具有当代性,而思辨的对象——作品展示的社会人生却是历史的。通过《醉乡》,你完成了你的创作的重要转折,即不只是对人生的思辨,而且,做为思辨的对象也具有了当代性(我是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使用这个概念的)。
是的,你已经站到生活发展的潮头上了。《醉乡》把湘西土家族当前的人生现实,不,应该说是整个湘西当前的人生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于我国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同步化(至少在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和为此施加的政治影响方面是如此),《醉乡》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然而,共性永远代替不了个性。你写的是湘西的乡下人,他们的人生自有不同于其它地区农村的特点。在你、还有我的故乡,《醉乡》里的人物,我都见到过,甚至可以说我十分熟悉他们。只是这些在生活中原先散见于不同村寨的人物,被你集中在一起——在那个雀儿寨,由于席卷全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浪潮的冲击,也由于人生中常与变的交织,演出人生的新场面。《醉乡》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实行农村经济改革后,在雀儿寨经济领域内出现的新的竞争,这已为作品提供的情节发展线索所昭示。在这方面,你安排了两条线索:贵二与天九、大狗的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冲突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竞赛范围,在其内在蕴含上,反映着不同的道德与人生价值观的对立。要确定这场冲突的性质,必须对人物各自经济活动的目的、手段及其道德基础做出分析。
你提出了一道难题:贵二“算不算社会主义新人一个?”你不置可否地将球踢到了读者一边。也许,作家在作品中真实地写出了生活中的“这一个”,他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不负解答的责任。我们却无法绕开这个问题。
贵二发了财。这个原先连自己也难养活的人物,奇迹般地一跃而为雀儿寨的经济强人。他赖以致富的方式,是他的勤劳,和利用经济信息、掌握新的生产手段、开发自身的智能潜力。这同时导致他自身社会成分的改变——从依附土地的农民、流浪者到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人的决定性的转变。而他在富起来以后,又慷慨地向邻舍、乡亲伸出援手,其行为含有共同致富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在客观上,使贵二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主观上,贵二丝毫也谈不上抱有改造农村经济结构的雄才大略,他只是在丧失土地的情况下找一条自救之路,找一碗饭吃。当然也含有更积极一点的考虑:为乡邻榨油提供方便;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社会身分发生的质的变化;援助别人也不是立足于走共同致富道路的认识,慷慨全出于乡下人的“情义”观。你深刻地发现并把握住了在农民身上出现的主观精神与客观存在的分裂。一方面,急剧变化的形势或先或后将他们推向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中,另一方面,他们背负的沉重“旧生活包袱”使他们在主观上与这种变化不相适应。这种分裂将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新人在现实中是已经有了的,但你终于选择了贵二这种更带普遍性的形象,是不是有意提出在新形势下弥合这种分裂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不论如何,贵二这个形象的内在蕴含,必然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天九、大狗与贵二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具有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对农村的经济改革,天九与大狗确有过不同程度的怨愤与抵触情绪,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它。如果撇开他们活动的道德基础与具体手段不谈,在一种抽象意义上,大狗的离乡又离土(譬如他从事一种合法的个体经商),天九一只脚踩着土地、一只脚又离开土地的经济活动方式,与贵二的离土不离乡,恰恰构成农村经济改革后必然出现的三种新的经济活动形态。它们之间会有一场经济竞争。然而,贵二与天九、大狗之间发生的,不是单纯经济上的君子之争,你的兴趣不在这里。透过经济活动的表象,你看出了其背后的人生观与道德观的对立。大狗是做为一种破坏正常经济、腐蚀山村灵魂的力量出现的。你描绘了一种社会寄生现象。先前,他寄生于政治的荒谬,现在,他又非法地从社会经济脉管里吸取血液,并将病毒带进社会肌体。他们在社会上走钢丝、赚活络钱,为个人省力快活而损人利己。大狗与贵二以新的社会身分在雀儿寨出现,都发生在各自走出湘西、在大口岸跑了一趟之后。对“外”开放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你有意安排了两个相似的场面让他俩返乡——两个“幽灵”闯进了雀儿寨。这使你的描写染上了一种象征色彩。这样,与乡下人传统道德同步的经济发展与破坏这种道德基石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冲突便在雀儿寨出现了。这就是在经济上贵二与大狗冲突的实质。你有意将大狗漫画化,来突出你的爱憎。然而,是不是也有点因此失去了在其他人物描写上的那种从容和冷静?天九的刻划却是很有力度的。他属于山村中那类精明的人物。他要超过贵二,当雀儿寨的“首户”,这原没有多少不好,相反,它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股推动力。问题在于他的发家是以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做基础的。你从这类人物身上,敏感地闻出了一种富农气味。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了做为一个队干部在农村中占有的“优势”,一切损人的举动全在“合法”、“合情”的形式下进行。他巧妙地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转移到自己的荷包里,就象当年他们利用职权多吃多占一样。他的发家终将以影响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代价。《醉乡》警钟似提醒着人们对这种潜在危险的注意。——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已越来越强烈地发出了对这种情况的抱怨。与天九相比,大狗这类人物的破坏作用性烈,然而明显,易于识别。天九的作为是一种慢性毒剂。贵二这类人物今后的兴衰起落,将越来越严重地与天九这类人物行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单从雀儿寨经济领域发生的矛盾冲突这一情节发展线索看,《醉乡》就浓缩了这么多的现实蕴含,但《醉乡》提供的远不止这些。你沿着出现在贵二身上的主观精神与客观存在的分裂,向社会人生的更深层次开掘——我们就要接触到《醉乡》反映的社会人生的个性特点了。
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物——矮子贵二做了《醉乡》的主人公。先前,他在经济、政治乃至相貌上都是卑微的,在雀儿寨,他是一个多余的人——他无力养活自己、受人欺凌、失去了恋爱、结婚的权力,连姓氏也差点忘记——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他人的价值的失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他提供了命运转变的契机。从贵二的崛起中,你不只是看到经济翻身的表层意义,而且深一层地发现了他的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雀儿寨最漂亮的婆娘竟然主动投入他的怀抱。香草当然是图他口袋里的钱,以满足她的虚荣与享乐。在一定条件下,钱虽然可以看做人的价值的象征符号,但人的价值绝不等于金钱。杨梅寨的牛哥之所以同意将漂亮能干的满妹许配给贵二,是由于他发现了通过经济上的崛起反映出来的贵二的智能,当然同时也因为他“忠厚老实”。贵二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确认。这一事实诱发了贵二生命的自尊,直觉到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并日益增长出对生活的信心。但是,精神上的卑微感并没有因经济地位的突变而消失净尽,以至大狗公开以天九家女婿的身分向他的合法权利挑战,并继而霸占香草以玷污他的人格时,他仍然鼓不起勇气与大狗抗争。直到大狗第一次败在他的手下,他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竟如此强大,感到自豪、欢欣和满足。”这对于贵二,确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你没有简化人物精神转变的过程,而是真实地、极有层次地描绘了贵二自我意识觉醒的缓慢得令人焦急的心理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贵二开始摆脱命运对自己生命的支配。这仅仅是开始,直到终卷,在他的理性世界里,也只具有“‘行路难。再难,人们也不能不走路啊”的朴素认识。然而,这又是一种极可宝贵的开始,这一朴素的认识将是贵二通向更高层次人生认识的阶梯。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贵二的脚步沉重又缓慢?他背着的“旧生活包袱”又是什么?从《醉乡》提供的情节发展线索看,当然是他受尽屈辱的人生经历培养而成的严重的人生卑微感,说严重些,就是一种奴化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在外部,存在着他们无力抗拒的巨大人生压力,在内部,便是对命中派定的厄运的认可。逆来顺受、信守乡下人的“本份”成了他们的人生信条。甚至他们身上的善良、忠厚、诚实等素朴的品格也同这种不能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思想状态死死缠结在一起。捉住徘徊在湘西山村的天命思想的幽灵,你便找到了解开湘西人生奥秘的钥匙,也获得了一个最可靠的观察基点。
做为湘西人,我要感谢你塑造了老乔保这个人物——一看到他,便使人百感交集。诚如你说,这是一个“可笑又可爱”的人物。他善良、热情而又带着几分乡村的狡诈(这是不含贬意的,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也许比聪明、机智之类更贴切些。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中性词)。即便这狡诈,又透出多少坦诚与天真!然而,他又是怎样顽固地信守着湘西人世代相袭的天命思想。看着他的阴差阳错,他的不合时宜,他的可怜的满足,岂止是令人可笑而已,真使人想大哭一场!这个人物,是不是有点象沈从文《边城》里的老爷爷,《长河》里的老水手?通过他,你把视野延伸到湘西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种深远的历史感觉!这种历史感兴唤起人们沉重的责任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从老乔保身上,为贵二这个人物寻根,但作品的意象已给人们指示出这一思索的方向。老乔保不是贵二精神的形象补充,也不是贵二将来的影子,你不是在为屈原安排一个婵娟。贵二与老乔保有许多精神上的联系,,但又有许多不同。在许多根本性的回题上,从一开始就见出贵二与老乔保的差异。贵二终将从历史的茧缚中脱出,以不同于他的前辈们的新面貌出现在湘西的土地上。
——你将对人生的深层次的思考与毫不掺假的湘西人生现实性结合在一起,没有人为地赋予贵二更高的人生起点,也没有主观地赋予主人公以人生哲理思辨的头脑,你让他实实在在地站在湘西现实的土壤上。这样,你对人生的思辨,或者说,从《醉乡》客观人生描绘中透出的人生哲理蕴含,完全脱去了书斋气。
这种要求湘西儿女摆脱传统命运,从精神上站起来,摆脱“对网和对人的依附”,飞进“自由的空间”,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才是《醉乡》的真正灵魂。你是将主要笔墨放到这方面来了。人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在作品中只提供了一种背景。——这样说也许低估了经济领域的变革在作品中的意义。因为没有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人生中更深层的人际关系,例如道德、价值观、爱情、婚姻结构等,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醉乡》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动力,它震塌了雀儿寨原有的价值观、爱情、婚姻结构的基础,导致价值观、爱情、婚姻形态的巨大变动。
你用了那么多的篇幅去描写雀儿寨的多种爱情、婚姻结构及其产生的变化,然而,却没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过去你写过,例如《水碾》和另外一些作品。但是,看来你讲浪漫爱情故事的能力,比你写充满酸苦与辛涩的畸形婚姻逊色。在《醉乡》里,这种畸形婚姻(或爱情?)形态的描写简直到了集大成的地步。你写出了多种婚姻及两性关系形态——天九与叭妹、玉杉与天九、贵二与香草、香草与大狗,各有各的模式,各有各的特定内涵。而且,它们无一不是畸形的。即便贵二与玉杉的爱情,也没有丝毫的浪漫情趣。你真有点儿冷酷,那样不留情地将有关人物放到那张现实的人生“网”里,揭示出其中的全部复杂性与微妙性,严峻地道出了生活的真理。你通过婚姻、爱情这面镜子,映照出三个乡村妇女的不同人生命运。叭妹是愚昧而可怜的。在男女关系上,她缺乏起码的人的觉醒。对她来说,人生只有婚姻,而无爱情。她对于天九,只是一个得力的劳动帮手和生儿育女的工具;香草大约暂时只会爱自己、爱钱,却不会去爱人,无论是与大狗或与贵二,都只能成为露水夫妻。做为两种极端,叭妹与香草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的感觉。在叭妹,是愚昧的障蔽;在香草,则是金钱的扭曲。但大狗与贵二,情况又稍稍不同。即使只是对美貌的倾心,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爱。更为复杂的情况发生在玉杉身上。在她与天九的纠葛中,在天九方面,是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之外,寻求一种爱的补充。应该说,他是“爱”玉杉的,爱她的聪明、貌美,以至特有的“女人的魅力”。虽然他是趁人之危以遂私欲,并毫不顾忌因此而带来的道德后果,但他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爱的满足。在玉杉方面,除了经济压力使她摆脱不了天九的纠缠外,也未必全出于被动。天九的仪表与能干,对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天九将先前的贵二比下去了。这种遭到雀儿寨舆论非议的关系,他俩谁该负责?也许,天九该负主要责任,但玉杉也要负责。也许,他俩谁都无责可负。唯一的办法是象坎脚阿公那样,对她俩之间发生的一切不置一辞。任何主观的评议都成为多余。
在上述种种婚姻及爱情关系中,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究竟什么是爱情?是精神上的同步?是生理上的和谐?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相貌上的相互吸引?如果我们不是将爱情的理解浪漫化,那么,任何单一的标准都无从说明爱情与婚姻的客观现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上述种种婚姻与两性关系形态,都远非健全的。一切都混乱而失章次,全是错中错,粘在一张错乱网上的人们,只能按这个秩序排列。你真实地再现了它们的全部复杂性,一点也不欲净化它们。而且,你还有意给这些一点也不浪漫的婚姻提供一种浪漫的背景,香草对贵二的挑逗以山歌传情的方式出现,天九与玉杉的会面竟采用情人约会的情节,你是不是有意向艺术的常规挑战?然而,正由于这种具有诗意的浪漫背景与人情乖张的两相对照,见出人与自然的分离,完成着你的讽刺。
讽刺并不是你的目的。这些远非健全的婚姻与两性关系形态,在《醉乡》的整体审美追求中,到底只是一种陪衬。在你的美学的价值天秤上,重心是向着贵二与玉杉的爱情倾斜的。他们之间的爱有着道德、情感的共同基础,只是一张不健全的关系网将他们隔开了。但他们逐渐地挣脱这面网的束缚,两颗心在逐渐靠拢。你是那样精细地揭示着人物情感演变的前因后果,勾画出他们各自的心理轨迹。你没有做那种大团圆结尾的蠢事,而是用大量的伏笔与象征,暗示出他们爱情的最终归宿。这将是一种获得了自由的,有着丰富而健康(不一定十全十美)的爱情内涵的结合——乡村灵魂终于向美皈依。贵二与玉杉爱情关系的这种演变,在《醉乡》里,是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变、自我价值的发现、精神上摆脱对外界的依附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你通过经济、政治、道德、婚姻与爱情关系等多角度的透视,立体地再现了农村经济改革后,湘西山村出现的人的精神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变化过程,完成了《醉乡》里人对命运自主把握这一人生审美追求。
做为一个有机整体,《醉乡》的全部人生蕴含是根连枝接,生气贯通的,我的分析却将它弄得这样支离破碎。需要一种综合,以找出作品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在作品内部,是依靠你画的那张“网”,即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粘接成的,这已如前述。诱惑人们回头反顾的,是你赋予作品怎样一种浑一的外部表现形态。从结构上看,《醉乡》是以贵二的经济地位与精神世界的变化为主线,旁及与这种变化相关联的社会人事展开故事情节。这毫不足奇,你只是采用了一种通常的小说结构方式。然而,在这普通的情节藤蔓上,却结着怎样一串果实!借湘西的特产来比喻,那是刺莓、板栗、猕猴桃、老虎豆和八月瓜!——一种连续的土家山寨风俗画的集成。其厚实与繁密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婚丧礼仪、吵架斗殴、墟场风貌、妇姑勃
你是在唱一曲浪漫的山村牧歌?已有的艺术模式立即使人们想起,古朴的山村美德、纯真的爱情、迷人的大自然的风景、人与自然的契合……,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果戈理的五月之夜?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龙舟竞渡?不,《醉乡》不是月光下的梦境,凄迷、幽美;而是太阳下的风景,明朗、轮廓分明。你用现实主义烛光,澄清笼罩在山村风情上的浪漫的迷
就在这繁密的人生风俗画里,蒸腾起《醉乡》的全部情感氤氲。诚如你说:“《醉乡》的基调是欢乐的。”——伴随《醉乡》人生审美追求而产生的,是你对贵二与玉杉等人物摆脱“对网和对人的依附”,飞进“自由的空间”的喜悦。然而,《醉乡》的情感蕴含远不是单一的。单一的欢乐反而会使作品产生的这种情感效果有限。你当然清楚这种情感处理的艺术辩证法。在《醉乡》里,“乡乐”是以“乡愁”来铺垫的,二者互为依傍。在描绘每一幅人生图画时,你的内心里翻腾着怎样各不相同的情感潮流,读者是能够确切感受到的。你当然知道,你是怎样咀嚼过浸透在贵二当年“象野猫黄鼠狼一样,在黑暗山洞里蛰居、爬行和躲藏”的变态心理中的、可怜的玉杉不幸遭遇中的全部酸苦,牛儿和兔儿要吃“屋那么多”一堆肉里的辛涩,老乔保梦游地府及其可怜的人生满足里的苦趣,老乔保向牛哥提亲场面里的温馨与甘甜,贵二向玉杉求婚遭到拒绝后“似河水一样袭上心头”的悲哀……,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这一切,在《醉乡》里化合成一股浓浓的乡土悲悯感——一个出身于湘西的知识分子对故乡人生真味独得的感受。你的心紧贴着湘西的平凡人生,从这种强烈的乡土悲悯感里推出你的乡村欢乐。这是拌和着苦痛的欢乐,是“含泪的微笑”。然而,当你抒写这全部人生感触时,文字的表面却是平静的,没有大喊大叫,你在使劲抑制自己情感的主观冲动。《醉乡》鲜有主观情绪的直接渲染,情感渗透在人生风景的描述中。但是,中间也夹着一点不尽和谐的成分。在大狗的描写上,你或多或少失去了应有的冷静,有一点浮躁,忍不住要“骂娘”。这当然是因为这个人物的行为“实在太令人切齿”。但倘若,你不是仅仅看到他的可恶,也看出他的可怜——实在也很可怜,他是那样深地沉沦在人生的泥淖里而不能自拔——那么,你的叙述也许就能获得与其他人物描写相一致的平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特定的社会人生内容的传达,大约依靠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环境而获得特有的韵味与美感。《醉乡》的语言与其传达的人生内容、风俗及内在情感是和谐而统一的。我不知道,如果抹去《醉乡》语言的浓郁地方色彩,你笔下的这些人生风景会变成什么样的型范?《醉乡》更集中、成熟地体现出你自己一贯的语言风格,你奉献的是一份“土仪”,具有典型的湘西味道。你是那样醉心于湘西的词汇与用语,并穿插着那里特有的情歌、哭嫁歌、上梁的祝辞等等,你捧出那么多的语言收藏,这是你长期滚在生活里获得的报偿。于是,你有了自己的语言风格——素朴、淳厚而又沉稳。
人物语言构成《醉乡》强有力的表现因素。在《醉乡》描绘的每一幅人生图画里,你不仅大量采用人物的对话,还将本可由你出面的叙述转化为人物的内心语言,如上卷第五章与第十一章,表现农村经济改革后出现的喜人变化及人物的梦境,几乎整章地化为人物的内心独白。这当然比由你出面叙述的难度大。因为不仅要道出事情的始末,而且要使语言对象化,——切合人物的特定身份。这不仅是叙述,而且是作品里的湘西乡下人的叙述,而且还是湘西山寨的“这一个”人叙述。它必须表现出人物特定的心理、性格与气质。你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人物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尤其是老乔保这个人物的语言,更是神气凸现,妙趣横生。他向牛哥提亲时的那一大篇说辞,不但是熔铸了老辈人人生感兴的以情动人的佳作,而且集中表现出老乔保的性格特征:他的热情,他的估价人的标准,他摸准对方心思的“狡诈”,不免几分乡下人特有的夸张,更多诚挚与实在——说的都是“本情话”。从人物的言谈里,能瞧见他的须眉和神色在飞动。
是到了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了。你看,写了这么多,也只是就《醉乡》读《醉乡》。虽然也偶尔提及你先前的一些创作,却没有将它们做为一个“体系”来考察。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什么话要说,也只能留待今后了。我只是感到,从《五台山传奇》,经《甜甜的刺莓》《水碾》,到《醉乡》,你似乎一贯地将湘西山寨做为你观察人生的窗口。你始终注视着那些普通平凡的乡下人,同他们在一起,跟踪他们的足迹,感受他们的悲欢,并将你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所得,浓缩到湘西的寨子里来上演,显示出你在艺术上特有的执着追求。这使你的作品构图集中、紧凑、小中见大。然而,利与弊从来就是孪生子,这种构图方式常使你的作品紧密有余,而舒展不足。一读完《醉乡》,我就有了这种感觉。也许,这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直觉。但我仍要冒昧地向你建议:扩充你的人物活动的舞台。湘西是那么大,不只有山寨,还有城镇、水码头;不但有农民,还有水手、乡村知识分子、过去时代遗留的工商业者、资本家,以及各层的多种模式的“头”。如果能有一部包容了这各种人物的人生图景,在一种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里,写出湘西大人生来的作品,那该多诱人啊!我渴望着这样一部巨著能在你的手中诞生,而你,是有可能做到的。——这已是题外话了,还是就此“带住”,并祝好!
一九八四年十月底,于岳麓山下
(《醉乡》,孙建忠著,载《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一九八四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