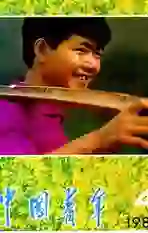“铃声”从民间传来
1983-08-21杨小洋连瑜华
杨小洋 连瑜华
去年12月1日,福建电视台的负责同志正在审看一部刚从“下面”送上来的电视剧。
片名—一《铃声叮当》。
编剧、导演、摄影、演员、制片—一一伙爱好文学的青年!
五十分钟的播映时间,对观众来说并不算长;但对等待着“判决”的“制片人”来说,却是一分一秒熬过来的。
随着电视剧结尾那叮当作响的铃声,演播室的门打开了。台长老雷同志满脸喜色,拍着“制片人”的肩膀,郑重宣布:《铃声叮当》通过了。随后,老雷对福建电视台的几位同志说:青年人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搞出来的电视剧达到这样的水平,不简单。当心啊,“民间”在向我们挑战了。
民间“文联”
在福州市有一个既松散又紧密的民间“文联”。说它松散,是因为十几个成员,八小时之内都有自己工作的“角落”;说它紧密,是因为八小时之外,这些年轻人紧紧piao在一起,讨论文学,讨论人生。
他们之中有团干部,有教师,有工人,有忙忙碌碌的个体户青年,也有一些初露头角的青年编辑、记者。在他们当中,有学历的人不多,有志气的人不少。他们不主张胡来,但他们也不很“安分”。
在去年年初的一次聚会上,讨论十分热烈:
——我们不能总是单干。“文联”“文联”,就得联合起来,有所作为。一个人有再大的激情,写首诗又能打动多少人!
——最有影响的还要算电影和电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已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谁都有权利捷足先登。
——现在几乎家家有电视,可节目都是“大锅”里出来的,咱这“小锅”就不能试试吗!
——一个省有几十万人,精神文明的花坛,靠少数园丁是远远不够的,搞电视剧大有奔头1
搞电视剧,这最佳建议很难说归功于谁,好点子不都是在七嘴八舌中跳出来的吗!
社会上,总有人觉得文学青年有点“狂”。“狂”这个词的确说中了一些人;但鲁迅笔下的“狂人”有一句名言:“从来如此,便对吗?”敢于突破“从来如此”的框框,不正是改革者所需要的勇气吗?
在这民间“文联”中,齐红是位相当稳重的大姐。在我们社会里,能被称为“大姐”的人,不容易啊。她在省文联工作。职业信息告诉她:拍电视剧这是千千万万人需要的工作,同时这也是千头万绪的工作。在七嘴八舌的酝酿中,她静听着,观察着,掂量着每个倡议的分量,也把握着大伙的情绪。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的时候,她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写文章只需要一支笔,拍电视剧可要一整套设备啊!
到底是“民间”“文联”,来自三百六十行。宋晓峰所在的“计生办”(计划生育办公室),虽然不涉及艺术,但一套录像设备却是全新的。小伙子平时兢兢业业钻研录像技术,领导早就有心让他练练兵。这回借用一下岂不是两全其美!小宋对大伙说:“我看问题不大。”话虽不多,但一锤定音。
新的“工程”就这样起步了,那正是闽东春暖花开的时候。
铃声留步
这民间“文联”中,有位很有才气的“指导员”,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前线广播电台的张建中,伙伴们都称他是“大兵”。他从小喜欢文学,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小说、散文。这次搞电视剧,他是当仁不让了。
剧本是一剧灵魂。几天来,张建中都在思考着,捕捉着。这天,他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五四”新村。路上的行人不多,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忽然,他发现路旁有一位清洁工在风雨中清理堵塞的下水道口。积水没过脚面,垃圾被水一泡,泛起白沫。清洁工从头到脚,被淋得湿漉漉的。只见她在风雨中一把泥、一把水地干着。下水道终于通了,雨水在下水口形成了一个旋涡。清洁工抹掉脸上的汗水。这时雨住天晴,她拿起铜铃又叮叮当当地摇起来,招呼人们倒垃圾了。
当张建中把这一切拍入自己心灵里的摄像机时,“扫马路”三个字在他心里翻腾开了。他不止一次听到过,一些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孩子时,常常本能地骂道:“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就让你扫马路!”尽管文学作品里有人为清洁工唱过赞歌,但偏见和习惯势力还远没有退却。在这个岗位上的年轻人,有的把口罩拉得高高的,有的把帽檐压得低低的……
小张碰到的这件“小事”,此时此刻对他变成了一种“威压”。眼前这清洁工霎时高大了,他决心借助这形象榨出人们心头的“小”字!
两个星期后,青年们再次聚会,张建中和齐红大姐合写的剧本,打动了这伙年轻人的心。大家说:“铃声”催你们动笔,我们也就在“铃声”中起步吧。电视剧的名字正式定为《铃声叮当》。
车到“民间”
到底应了齐红那句话:要搞一部电视剧千头万绪,它毕竟不是靠一支笔啊。在这扯皮成风的社会里,一个打不出旗号的电视剧组能迈开自己的步子吗?说来也怪,车到民间“绿灯”多。
摄像机的事,晓峰虽然在会上答应了,回来后心里也打鼓:这样贵重的机器真让拿出来吗?他蹑手蹑脚敲响了主任的办公室,鼓足勇气把拍电视剧的想法一五一十汇报了。领导是有远见的明白人。盖主任说:“小伙子,拿去用吧。设备放着要生锈,拍片练兵我支持。”宣传处长戳着晓峰的前额说:“虎头蛇尾可不行,要干就干他个虎头凤尾,拿出象样的东西!”摄像机到手了,小伙子扛在肩上向齐红报到。
电视剧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一个街道里巷。车水马龙的闹市里,寻找一片听摆布的场景是不容易的。他们来到福州市庆城居委会。街道主任是省人大代表、五十八岁的林淑英同志。她深知清洁工的甘苦,一听说要把他们搬上屏幕,劲就来了。她和青年们一起选地点,定时间。拍片那几天,把秩序维持得井井有条。
这个由十几位青年组成的摄制组,没有浩浩荡荡的车队,没有眼花缭乱的灯光和道具。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摄像机是放在竹筐里用自行车驮运时;当人们了解到他们拍片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资金又是靠自己筹集的时候,人们几乎是有求必应。车到民间,不仅是绿灯放行,更多的是添上一铲煤,提上一桶水,助他们一臂之力!
骆驼总会走出沙漠的
绿灯放行,并不等于一帆风顺。戈壁滩上固然没人阻挡,但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力量跋涉前行。
连拍片工作的ABC都不甚了解的年轻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边拍,边摸索,边讨论,边修改,进度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摄影师的工作要算是最辛苦的。开始的时候,晓峰连摄像机都端不稳,摄下的镜头不是上下抖动,就是左右摇晃。可小伙子有一股拧劲,非拍到自己满意不止。几组镜头拍下来,汗水淋漓,手臂发麻。
重拍,累坏了摄影师,演员也要一次一次地重演,那滋味就可想而知了。扮演男主角的是福州缝纫机台板厂的团总支书记邱燕昆,扮演女主角的是福州市广播电台的记者金诚峰。这些从未演过戏的青年,有好几次让导演训得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当大家辛辛苦苦忙了一阵,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审看录像,了解拍摄效果时,有时真是大失所望。有的捂着脸看不下去,有的指着屏幕骂骂咧咧。构思不理想,调度不恰当,表演不适度……彼此要求都很苛刻,自我挑剔也毫不留情。品评的结果往往是推倒重来。有的唉声叹气了,有的悄悄掉泪了。
“骆驼总会走出沙漠的”,这是导演范希健的声音。在最困难的时候,导演扶正了大梁。范希健同志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31岁。在接受齐红大姐邀请时,他深知拍片不易,但在同龄人面前,他别无选择。此刻,他知道这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
“骆驼总会走出沙漠的”。这话虽不是什么警句,但此时此刻却显出神奇的力量。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最令人难忘的是拍摄工作的最后一天。他们凌晨三点起床,第三次奔赴金山寺,要抢在日出时,拍下一组镜头。演员们赤脚站在冰冷的江水中,迎来了从江面升起的一轮红日。当人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结束了第一个回合,马不停蹄地赶到西湖公园。在那里,他们用船代替“轨道车”,反复十几次才拍好岸上的另一组镜头。下午,他们又返回闽江口,追赶夕阳,拍完预定的最后一组场景。这个星期天,他们整整干了18个钟头!
半年多的时间,从台江区清洁队到福州市离休干部休养所,从福建师大到前线广播电台,事情千头万绪:演员体验生活,配角熟习环境,再加上谱曲、录音等后期制作,这一切都靠这几个年轻的“骆驼”在沙漠中穿梭,叮叮当当的铃声,催他们上路,催他们前行!
去年12月24日晚,福建省电视台正式播放电视剧《铃声叮当》。观众们欣赏着、品评着,但人们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来自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