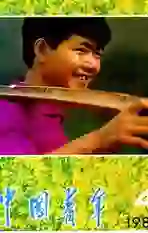小溪(小说)
1983-08-21张为赵曙光
张为 赵曙光
一个护士死了,医院的人们也许会惋惜。她虽然刚从军医学校分来不到一年,有人说不定还拿她的名字对不上号,但她毕竟太年轻。据说还不满十九岁。
可是如果听说她护理过的病号竟然夜里悄悄跑到太平间外面,顶着露水和凉气为她守灵,工作人员劝也劝不回去,大家又会怎么看呢?
六五一结核病院的总值班日记上,确确实实记载着这样的事。关于守灵,据说起初是夜班护士电话报告“四个病员失踪”。总值班员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还为“结核病员难管理”大感头痛。可是在找到了他们,劝他们回去休息的时候,他却被那个场面弄得鼻子发酸了……
“感情”这个词几
杨大成一入院就对王小清发怒,这只是因为他感到憋气。早上被钢丝床嘎嘎吱吱的响声吵醒,他猛地想起是躺在医院里,心里一沉,就怒了。
他原是舰队里公认的“标准水兵体魄”。可就是一张轻飘飘的诊断书,就把他弄进了医院。
弄得钢丝床响的,是那个叫梁黑子的新兵。他好象还在连队,抢先起床穿衣服,很响地走进走出,扫地,拖地板,给别人打洗脸水。接着,那个叫朱锐的就连忙起床,一边说:“哎呀哎呀,我又起晚了。”一边和梁黑子抢活儿干。他也是个倒霉蛋,刚从高中考进军政学校,没学到一年就搬到医院来了。梁黑子用快活的河南调儿回答:“中,中,您都请歇着。”
“又装什么假积极,不怕人讨厌!”
这一位是要塞区的观测兵刘玉,是个留小胡子,爱照镜子,爱哼“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的角色。据他自己介绍,他是因为探家超了假,到医院想混个病假条搪塞搪塞,不料倒真查出了肺结核。如今他已经是第二次住院,讲起往事还满脸得意,好象因祸得福了。
“也没人晚点名表扬你们,也捞不着立功受奖,一大早扑扑腾腾的,吵人家睡觉!”他喝斥完了两个做好事的,又蒙上头。
梁黑子不敢动了。朱锐对着被子说:“身体有病,精神不能有病嘛。捞不到好处就不学雷锋啦?”
“得啦得啦,”刘玉又伸出头,“有病就要多休息。怎么的,是雷锋叫你们来吵得别人不能休息的?”
这乱糟糟的地方!杨大成更烦了。连吸几口烟。
走廊里响起了送药小车车轴的吱吱声。这回刘玉起床了。门开处,一个小护士推门进来。杨大成斜眼看她,个子不到自己的肩头,肥大的工作服在身上直晃荡;尤其可笑的是那顶圆圆的护士帽,松松垮垮地扣在头上,老象要掉下来。她就是王小清。
刘玉对她满脸堆笑:“王护士,今天是搓棉花签儿还是起瓶盖儿?等你指示啊!”
王小清歪歪身子,斜斜大口罩上的两只黑眼睛,娇声娇气地一笑:“你呀,剃头刮胡子去!”
“我请问,留两根胡子到底算什么错误?”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呗!”
“那好哇,我请问了:马恩列斯都留胡子,你王小清小姐怎么打发他们四位?”
“他们要是参加解放军哪,保险都剃了。”刘玉噎住了,朱锐和梁黑子都乐了。杨大成一沉脸:有什么可笑的!他披上衣,推门上阳台去了。
阳台上染着初夏明媚的阳光。杨大成一低头,看见楼下面居然有一条小溪。它滑过一道黄沙铺底的浅沟,漫进一片嫩绿的草滩,浓密的草缝里到处闪射出斑斑点点的光亮。从那里隐隐传来淙淙的水声。
“你也喜欢这条小溪?”
王小清不知什么时候跟出来了。杨大成不友好地扫她一眼。他看见了一双亮亮的、睫毛向上扬起来的、孩子般的黑眼睛。
“它真好看,是不是?你要是想家了呀,看看它,心里就好受了。”
这算什么话?堂堂的海军老战士是让人当孩子哄的吗?杨大成怒气升上来,直拱脑门子。
“呀,你好傻呀!”王小清大惊小怪地嚷起来,“都肺结核了,你还抽烟!”
杨大成不理她,又摸出一支,就着烟屁股续上,然后深深吸一口,长长地吐出来。
她却笑了,黑眼睛透出稚气:“你象我二哥,也是牛脾气。”她递上一只药杯,“我妈老骂他‘犟脖子牛。吃药吧,别抽烟了,真的。”
她的手又小又瘦,白极了,却没有光泽,手背上看得见粉红色的毛细血管。杨大成把脸扭到一边。
“给呀!”王小清抓过他的大手,把药倒进他手心里。
杨大成没料到她竟会动手动脚。他真火了,把药片狠狠地摔在地上,牛一样瞪着王小清。王小清怔怔地望着他,淡淡的红晕从口罩里爬出来,在眼睛底下散开,黑眼睛里也包上了亮亮的泪光。
阳台上的响声引出了三个病友。刘玉问了声:“怎么回事”。王小清低下头,轻声说:“没什么,是P、A、S的糖衣掉了,怕有点变质。我再去换。”
她低着头推着车出去了,过一会又低着头拿来了药,把药和药杯都放到了杨大成的床头柜上。
然而这一次的交恶却没有断绝两人的接触。杨大成不吃药,不盖被子,为所欲为地对身体采取破坏性措施,果然招来了肺结核真正的惩罚。他发烧了,剧烈地咳嗽,而且咳出了血。他被移进了急救室,插上了氧气,吊上了静脉滴注针。如果换了别人,也许会为这境遇伤心。可他只会发怒,他不信这倒霉的肺结核能最后撂倒他。“怕个鬼,肺癌才好呢!”他真象一头身上插满了刀的西班牙斗牛,拼命冲向最后一把刀。在白天繁复的会诊、检查、治疗之后,夜里,他趁值班护士离开之机,拔掉了输氧管,拔掉了输液针。
“你这是干什么呀?”值班护士没隔一会儿又来了。是王小清。
杨大成冷冷地一笑,扭脸不理她。
她扑过来,迅速把输氧管插进他的鼻孔,可他又把它拔下来了。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放下正整理的输液针又来插管,他干脆把她推开,低声吼道:“讨厌,滚开!”
他一翻身,背朝着她,猛咳了一阵,闭上了眼睛。他感到胸闷,胸痛,浑身酸胀。他太疲倦了,恍惚中,他好象见到了他五岁时就死去的母亲。这是他幼时生过的一场大病留下的印象:他躺在母亲怀里,奄奄一息,望着母亲抱着他流泪、抽泣……
抽泣的声音使他惊醒了。站在床边的是王小清。她没戴口罩,手里捏着输氧管,眼泪顺着小鼻子小嘴流到下巴尖儿上吊着。见杨大成翻过身来,她带着哭腔说:“都怪我,你一住院我就惹你生气了!可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一股热浪打上来,杨大成那颗石头般的心动了一下。他感到眼皮子发涩,连忙慌乱地点点头。
“感情”这个词儿,杨大成历来“恕不恭敬”。可是当他看见王小清挂着泪珠一笑,不禁眼皮又一涩。不过这种感受,后来一直是珍藏在他心里的秘密。
什么样的失恋都痛苦
与杨大成不同,梁黑子一开始就喜欢上王小清了。
他俩第一次打交道是为打针。这个伏牛山区的小娃子,长得矮胖矮胖,圆脸圆眼睛圆鼻子头,脸上经常带着好奇、小心、谦恭的神情。可是针一扎进屁股蛋里,他就喊起来了:“好大姐,不敢打呀!”
王小清本来劝他:“不怕不怕,只有一点点痛。”听他喊自己“大姐”,竟红了脸,笑得弯下腰,连忙护住注射器,停止推药。
她看过他的病历,知道他比自己大三个月。自那以后,她倒真对他摆出一副姐姐的架式了:叫他做个棉签打扫个卫生,用的是吩咐的口气;做他的思想工作,用的是哄劝的口气;他要是受了别人的委屈,她还要出来保护保护。梁黑子有四十几元钱,大半是参军时从家里带来的。谁知刘玉知道了,说要买一双牛皮鞋,点着名找他借走了三十。为这事儿,梁黑子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晚上。他不敢告诉别人,却悄悄告诉了王小清。王小清一听,气呼呼地找到刘玉:“刘玉,你干什么欺负人家小梁?”
“这是从哪说起的呀?”刘玉见她就乐。
“不害臊,四年的老兵找人家新兵借钱!”
“这是两厢情愿的呀,怎么的啦?”
“什么什么?人家不敢不借给你,知不知道!”
“是吗?可笑!好好,遵命,鄙人马上送还。”
刘玉把三十元票子朝梁黑子床上一摔,一撇嘴:“傻呼呼的,看不出来,倒学会了告刁状!”
刘玉不但知道梁黑子钱包里有钱,还知道那里面藏着一张姑娘的照片。还钱的事情以后,刘玉就对梁黑子没有好脸了。杨大成转入急救室后,有一次刘玉故意当着王小清和朱锐的面,似笑非笑地说:“黑子,把你老婆的照片公开公开嘛!”
当时四个人正围着一个脏盆子拔脏棉签,有说有笑的。听刘玉一说,大家一楞。梁黑子刷地红了脸。
刘玉追问道:“你每天中午躲在被窝里看的是什么?”
“哪里……不是……”梁黑子尴尬极了。
“是对象吧?”朱锐故作好奇,想给他个台阶。
梁黑子勉强点点头。
王小清却大感好奇,嚷道:“快把照片拿出来看看——刘玉你少讨厌,什么老婆老婆的,难听死了。”
“那叫什么?亲爱的?”
“亲爱的怎么啦?你不要把高尚的字眼说得流里流气的!小梁,咱们别理他!”
叫王小清一鼓劲,梁黑子涨红的脸上露出一点儿笑。他伸手在贴身病号服里掏出钱包,果然抽出半个巴掌大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乡间小镇照相馆的作品:反差大,色调生硬,画面呆板,一幅亭台楼阁的布景,正中立正站着一个穿方口扁头土布鞋,胖圆脸,表情由于紧张和害羞显得呆滞的农村姑娘。
“她好象比你大两岁吧?”王小清怕把照片弄脏了,用两个指头捏着一个角。
“只大两个月。”
朱锐和善地问:“是青梅竹马?”
“哪,俺俩总共才见过两回面。”
“包办婚姻呗!”刘玉说。见梁黑子点点头,他又一本正经地问,“花多少钱啦?”
“七、八百吧。”梁黑子又连忙笑笑。
“那个每次都把六五一医院写成六五一部队的,八成就是这位亲爱的吧?”
梁黑子紧张了,望着刘玉“嘿嘿”傻笑。
王小清糊涂了,连问:“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他怕那位亲爱的知道他得了肺结核,不跟他,钱也白花了,就给人家写假地址呗。反正大地名没写错,邮局试投也能收到。”
朱锐皱起眉头问梁黑子:“真的?”梁黑子只是乞求地咧咧嘴。朱锐说:“你这样做恐怕就不对了。”
王小清又摇脑袋又摆手,说:“算了算了,不就是把地址写错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朱锐说:“为人要忠诚老实,何况是对终身伴侣!”
刘玉也帮腔:“就是嘛,就是嘛。”
王小清不对朱锐,却对着刘玉嚷嚷:“什么呀什么呀,人家生了病,怕家里挂念,有什么不对的?”
“你倒会替他找台阶。”刘玉说,“问问他自己嘛,到底是怕人家挂念还是怕丢了老婆?”
梁黑子的脑袋耷拉下来,抬不起来了。
王小清又嚷嚷:“就算是又怎么样?得了肺结核就希望别人都快点把你们甩啦?”
刘玉忙挤挤眼睛说:“好好好,姑娘们要都象你这么想,我们还有什么后顾之忧!”
朱锐却认真地说:“王护士的好心,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这对我们有多大帮助呢?得了肺结核,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交了厄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残酷现实。难道靠哄,靠骗,就解决问题了吗?我们怕复员,怕退学,怕把对象吹了。可怕有什么用?我说跟别人比起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多了一道坎坷,多了一次锤炼和考验。在这种意义上说,咱们真是幸运呢!”
王小清大受感动:“这就是你在可能会退学、会退役的情况下,还每天坚持学数理化的想法?”
“对。”朱锐庄重地说,“我准备再考理工科。”
梁黑子突然抬起头,拖着哭腔说:“就俺是个孬种啦!您请都放心,俺明天就给她写信承认错误,今儿黑了就写!”说完就呜呜哭起来。
“别哭。”王小清忙制止他,“还是个男子汉呢!”
可是过了半个月,梁黑子又哭了,而且哭得极伤心。他寄出了“承认错误”的信以后,迟迟不见女方回信,终日愁眉苦脸。王小清嘴上不说,心里也捏了一把汗。后来梁黑子的哥哥来了信,说女方家里得知他得了“痨病”,退了婚也退了礼。对他的悲伤,朱锐觉得滑稽可笑:“不了解就谈不上爱情,没有爱情又有什么必要如此伤心呢?”刘玉则跑去报告王小清,“哎,你弟弟的高尚爱情完蛋了,正在无限痛苦呢1”
王小清翻他一眼:“你这个人呀,为什么别人痛苦了,你就高兴呢?”
“别人有的我都要”
梁黑子丢了未婚妻,情绪低落。刘玉却更警觉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小新兵蛋子跟王小清更近乎了。“还真有想吃天鹅肉的?”他悄悄地监视起两个人来。
那天下午,朱锐带着外语书,跑到外面不知哪棵树下啃去了。杨大成刚从急救室转回来,躺在床上睡觉。梁黑子坐在床边小凳子上埋头伤心。刘玉算准了王小清要来找梁黑子,就躺在床上装睡。果然她来了。只听她往梁黑子床上一坐,压低声音问:“小梁,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这个样子嘛!”
“俺现在想啥都没心,俺觉得活得没劲。”
“你呀!对象吹了就活得没劲了?还不如我!”
“俺谁都不如,谁都瞧不起俺。”
“讨厌,谁瞧不起你啦!我是说你该学学朱锐。”
梁黑子不吭气了。王小清又噗嗤一笑说:“其实呀,我也不行。我刚穿上军装时,也想象过堵枪眼呀,救火车呀,要当一个真正的雷锋呀。可连想家都克服不了。到现在还想妈妈,想吃她炒的硬蚕豆……
“你猜我最怕什么?癞蛤蟆。刚到军医学校,新学员都参加劳动,盖新教学楼。清理地基,开头我干劲可大了,后来石头里蹦出来个癞蛤蟆,吓得我一整天就站在边上看别人干,说什么也不干了。结果晚上专门开我的班务会呀!班长说:‘啊,一不怕苦二不伯死,碰到个癞蛤蟆就不要组织纪律,不要完成任务啦?偏要我作检讨。我哭啦,我说,‘哼,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怕癞蛤蟆!……”
梁黑子“哼哼”地笑了。
“我特别怕晚上一人呆在外面。在军医学校的时候,我们短期下连当兵,在一个劳改农场搞守卫。本来女同志都是双哨,有一天不知怎么,半夜叫我一个人上了一班哨!哨位在一片树林子里,那天晚上有风,树叶儿乱响呀!还有云,半个月亮呀,一会儿遮黑了,一会儿又亮了,真害怕呀!我听到有个声音,‘啪嗒啪嗒,从小路跑过来啦。我端起半自动步枪,使劲喊:‘谁?声音停了。我更怕了呀:‘谁?不说话我就开枪啦!结果你看,真走出一个男的来。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那边生产队喂牛的,牛丢了,队长叫我出来找。我一听,放心了,说:‘好,你去吧。,他连忙说:‘谢谢,谢谢!跑了。
“过一会儿,‘啪嗒啪嗒又响起来了!我吓得要命,端起枪喊:‘谁,再不站住我开枪啦!就看见几个黑影一下躲到树后边去了。我想,这下子坏人真的来啦。反正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开枪,我的子弹又是早就上了膛的,我对着他们使劲一扣扳机。不知怎么扣不动!我差点儿瘫在坑里……结果,他们包围了我,一把夺走了我的枪。原来是一个副连长和两个战士。副连长冲我吼:‘你搞的什么名堂,怎么不问口令?他把我的枪哗啦哗啦扳两下,又说:‘哼哼,幸亏忘了打开保险,要不然还把我们枪毙了呢!”
“头起跑的那个呢r”梁黑子兴致勃勃起来。
“就是啊,那才真是个越狱的劳改犯,副连长他们就是去追他的!”
“嗬嗬嗬,劳改犯叫你给放了,追他的倒差点给你崩了,嗬啊嗬……”刚醒的杨大成嗡嗡说。
王小清补充说:“不过那个犯人天不亮就给捉回来了。农场周围几十里都是‘网,谁也跑不掉的。”
过了一会,梁黑子叹口气,诚恳地说:“王护士,俺喊过您大姐,叫人笑话了。俺倒觉着你象俺娘!”
“呀,讨厌,你怎么瞎打比方!”
“当真哩,俺遇着伤心的事了,俺娘就是这样,给俺讲笑话啦,讲故事啦,让俺宽心。”
刘玉听到这儿,对梁黑子也宽了心。如果一个小子想求爱,哪有管姑娘叫娘的!他望着王小清发愣。不知什么时候起,她的一切一切,与日俱增地刺激着他的幻想。终于在一天熄灯的时候,他向全室成员郑重宣布:他已经向王小清送交了“第一封情书”。
三个人都很震惊。梁黑子用眼睛翻他,杨大成眼睛里燃起了怒火。
“你真的爱她吗?”朱锐问。
“要不我把情书底稿公开念一念?”
“胡来!”杨大成拉开被子上床。
“这件事你是认真考虑的?”朱锐又问。
“伙计,别以为只有你们啃了两本书的会动脑筋,咱什么问题都认真考虑。怎么的?”
“那你找她,你认为合适吗?”
“你说咱配不上?嘿嘿!”他挑衅地扫视大家,“论家庭条件,咱是工人子弟,她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女,爹妈是县中学教师。论本人条件,她当护士,干部里头最小的。咱复员回家当工人,工资带奖金,比她拿得多。比不上她的,就是个身体呗。可咱听说她也有什么病!”
刘玉把王小清的情况摸得这么清,出乎大家意料。说王小清有病,更叫大家吃惊。大家沉默着。
“所以咱就想开了,至少我自己不歧视自己!”刘玉扬起了眉毛,“你要看咱矮一头,咱偏要比你高一头!咱活一天,就要痛痛快快把这一天玩得美美的!别人有的我都要!怎么的,咱就这样!”
“问题是怎么样才叫活得美。”朱锐说。
“别卖弄啦,说几句大道理,你就当上指导员啦?你常爱用‘意义,梁黑子天天做好事,有意义吧?他可会写假信骗取婚姻呢!咱这直截了当的,第一步就敢公开情书,怎么的,倒没‘意义了?”
朱锐懒得跟他辩了。梁黑子象挨了当头一棒,又蔫了。杨大成不耐烦地翻个身,连读“关灯”。
第二天,当王小清推车进来发药的时候,屋里空气紧张起来,四双眼睛都跟着她。她低头戴着大口罩,对谁都不敢看,把药杯摆在每个人床头,转身就走。临出门,回头低声招呼:“小梁,你出来一下。”
梁黑子象屁股上有根弹簧,蹦起来跟着出去了。不到两分钟,他回来了,尽量想表现得若无其事,胖脸蛋却忍不住放出光来。他把一张迭得小小的纸条交给刘玉说:“王护士叫还给你哩。还叫告诉你,再写这玩意儿,她就交给护士长了!”
刘玉脸上的肌肉僵硬了。他首先意识到丢了丑。但过一会儿,他却又自嘲地淡淡一笑:“恋爱自由嘛,何必搞得这么可怕!小题大作,可笑可笑1”
当着大家的面,他随随便便地把情书撕碎了。
不怕死
自打从急救室出来,大家都说杨大成变了,变得消瘦了,和善了,不抽烟了,配合治疗了,有时还独个儿哼哼唱唱的。这天上午,风和日丽,王小清来接班,远远见他坐在小溪边一块石头上,好象在望着溪水发呆。走到他背后了,才听见他在唱歌。他反复唱的是这么几句词儿:“唱吧朋友们,明天要航行,航行在那夜雾中。快乐地歌唱吧,亲爱的老船长,让我们一起来歌唱。”他唱得很轻,音调也不准,但嗓音很浑厚,流露着深沉的回忆和向往。觉察到身后有人,他回头一看是王小清,不唱了。
“呀,想不到你唱得这么动人。你唱呀!”
“嗬嗬。”杨大成搓搓手。
王小清笑了,十分快活。杨大成看她:军装衬出了纤细的身段,刚洗过头,军帽拿着,半干的头发用一块花手帕系在脑后,象山石中涌出的乌亮的泉水。那双黑眼睛亮亮的,甜甜的。“讲点你们海军的事儿吧!”她突然要求,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那有什么好讲的。”
“呀,随便讲一点呗,我可孤陋寡闻啦!”王小清一噘嘴。“那就讲唱歌?”杨大成问。
“讲什么都行。”
“我们不唱歌,干啥呢?第二天要出远海,头天晚饭后能上岸的不上了,都上甲板了。也没入起头,也没人指挥,都唱啊!”
“海上生活枯燥?”
“你说呢?除了天就是海,除了海就是天,舱又小,几十天,一两个月。你说呢?”
“那你们不喜欢大海?”
“不喜欢?”他瞪起了眼睛,但立刻又柔和下来。他叹了口气,“以后完啦,回不去啦!”
王小清知道勾起了杨大成的伤心事,沉默了一阵,说:“在哪儿不一样吗?你不喜欢陆地?”
杨大成笑笑,看着她,象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经常远离呀,有谁能比我们更喜欢陆地!”
“那不就行啦?”
“没那么简单哟!”
“哼,”王小清突然一撇嘴,“没看出来,你的感情还真丰富!我以为你就会发脾气呢!”
“你记仇,就不好了。”杨大成低下了头。
王小清笑了:“我记你的仇干啥呀?不配合治疗,倒霉的不是你自己吗?”
杨大成松了一口气,又忽然想起来说:“朱锐呀,学我耍混,你得过问过问了。”
原来,医生告诉朱锐,他肺部空洞较多,要做肺切除手术。于是他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吃药,还开始学抽烟。王小清听了不相信,跟杨大成一起回到楼里,她匆匆换上工作服,提着体温栏就去查体温。进了病室,果然见朱锐靠墙坐在床上,手指间正夹着一支烟。王小清呆望了他一阵,哀求似地说:“不要这样好吧,朱锐。”
“不要什么呀?”朱锐表示奇怪。
“不要这样好不好,你的意志那么坚强的呢!”
“我的意志并没有丝毫衰退呀!”
“……那你不吃药,还抽烟。”
“没那么严重。”朱锐吸一口烟,猛咳起来,呛出了眼泪,“你知道欧米埃尔吗?”
王小清摇摇头。
“欧米埃尔曾是个美丽得出名的姑娘,后来衰老得丑陋无比。雕塑大师罗丹就雕塑了这么个丑老太婆。结果呢,比美丽更加震惊世界。懂这个意思吗?”
王小清又摇摇头。
“美丽的东西也会衰亡。这就是罗丹说的真理。我们何不在丑陋和衰亡到来之前就结束呢?好戏都在高潮收场的。”
“你瞎说什么呀!你平常不是这样说的!”
“你错了。我平常说的跟这个不矛盾。我住院第一天就这么准备了,生病之前就这样计划人生了。”
“不怕死,是吧?”刘玉插上一句,“好样儿的嘛!”
朱锐释然一笑说:“王护士你放心,我没事儿,真的,保证配合治疗。”
王小清被弄糊涂了,也没词儿了,只好给大家发体温计。发到刘玉面前,她又低下头。刘玉突然指着她的工作服说:“哎,王护士,你的兜怎么湿啦?”
王小清这才发现,工作服左兜湿漉漉的。她伸手进去,摸到一个凉冰冰、软绵绵的东西,脸就吓黄了;猛地拎出来甩到地上,竟是一只大癞蛤蟆。吓得她尖叫一声,木制的体温栏“砰”地摔到地上,十几支体温计蹦出来,全摔碎了。
癞蛤蟆是刘玉放的,可是他没想到会闹出这么个结果。十几支体温计呀!王小清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儿,不知所措地连连说:“看你,这可怎么办……”
梁黑子下了地,默默地捡起体温栏,递给王小清。她接过来,忍着抽泣,转身跑出去了。梁黑子蹲下,抓起那只癞蛤蟆。这个素来怕刘玉的新兵站起来,两眼直逼刘玉。刘玉也紧张起来。这时,杨大成却发话了:“小梁,把癞蛤蟆扔出去!”
梁黑子没反应。杨大成下床,一只手拍到他肩上。梁黑子挣了两下没挣脱,癞蛤蟆在他手里被捏得四脚乱弹。杨大成冲着刘玉说:“你运气!要不是如今,哼,我就背个处分!”
刘玉心里发怵,脸上却不在乎地一笑:“想揍我呀?来吧!挨了揍再叫医院开除我,都行!没地方治了就是个死吧,怎么的,咱也跟朱锐一样,不怕死!”
“跟我一样?”朱锐嗤地一笑,“可怜1”
“我爱……”
亲爱的黑子同志:
您好吧!您一定还在生俺的气吧?自从上次您来信说住院了,俺娘就要退婚。俺不答应,她就说俺爹就是死在“痨病”上的。俺哭了几天也不管用。前天你们医院来了信,开口管俺叫姐,管自己叫妹妹。她说现在“痨病”能治好;还说您因为退婚,难过死了,说明您对俺好是真心;还说现在青年人恋爱,就是要忠诚;还批评俺这时候离开您,对您身体可不好。俺边看边掉泪,就念给俺娘听,她听着也点头叹气,可过后还是不答应,气得俺又跟她吵一架!
您放心,俺写了这封信,就是要您告诉俺那不知名的好妹妹,俺和您这辈子好到老,海枯石烂不变心。反正婚姻自主,俺啥也不怕……
梁黑子眉飞色舞地念,杨大成和朱锐拍巴掌喊好。还没念完,朱锐说:“我说小梁啊,前一段你们订婚倒没什么爱情,这么一退婚反而把爱情给找来啦!”
杨大成说:“你们猜,写信的是谁?”
梁黑子说:“王护士呗,旁人谁知道地址!”
朱锐说:“主要是只有她的心这么好。这信得给她看看,可她怎么还没上班呢?”
“她就是这一班,怎么没来就不知道了。”一直置身局外的刘玉突然插话了。癞蛤蟆事件后,他本以为科里会狠狠整他一顿,打算破罐子破摔,硬着头皮顶到底。不料等到第二天也没见动静。他向杨大成打听,杨大成没好气地告诉他:“人家王护士兜着了,掏钱赔啦!”“要她掏什么钱?”“她说是她打碎的呗,记她的差错呗,等着全院点名呗!”“我不用她来这一套!”“你,你还想叫她挨批呀?”“我去承认,还叫她挨什么批?”“批她欺骗领导,包庇坏人坏事!”“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她为啥包庇我?”“说你有病,怕你吃亏呗!”
这时,经朱锐一提,刘玉的心里象被戳了一下:“我问问去,她为什么没来上班。”
谁也没料想,他出去一会儿,就慌慌张张跑回来,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她病啦!很重的病!”
刘玉曾听说过王小清有病,这病叫“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但他不知道,这就是“血癌”。王小清是刚从学校分到这所医院,就被发现确诊的。送到军区总医院住了两个月院。这种病极难根治,只要病情稳定了,就可以延续生命。于是她坚决要求出院投入工作,还要求对病号们,甚至尽可能对工作人员保密,使大家象对待常人那样对待她。不答应她是不可能的,医院只好让她边工作边治疗。而这一次她突然病倒,属于慢性白血病的急性病变,可以说是最后时刻到了。
四个病友都傻了,半天才决定马上去看她。
六五一结核病院有近三百张结核病床,却只有三十几张普通病床,很好找。但结核病号当然不能往那里去。四个病友利用治疗后到午饭前的空隙溜出去,很快找到了王小清的病室。但里面的人太多,他们没法进去,只好从窗外的帘缝往里看。
那是一个单人急救室。她仰面躺着,陷进软褥子里,被子盖在瘦小的身躯上,显得瘪瘪的。她的脸色苍白而且泛黄,两个鼻孔塞上了棉花,显然是刚出过血。她显得疲乏,喘气好象很费力。
看见了她,四个病友很难过,好象终于相信了某个可怕的事实。睡午觉时,他们又溜去了。这次很顺利,看望她的人和医生都走了。“睡着了,就不准出声,看看就走。”进门以前,杨大成下了命令。
王小清闭着眼,鼻孔里的棉花已经拿掉,一缕汗湿的头发斜着贴在苍白的额头上,使她显得神态安恬。四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刚在她床边站定,她就睁开了眼睛:“你们……你们怎么才来呀?”
有一阵,大家都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
“王……俺姐,你好吗?”梁黑子问。
“痛啊,”王小清笑笑,“胸部一压就痛,四肢关节痛得象刀搅。典型症状。”
又沉默了一阵。王小清眼睛转向天花板,终于说:“我原来以为至少还有五、六年的时间,没想到会这么快。一般应该有五、六年左右的呀!”
朱锐忙说:“别伤心,你第一次都好了,这次也会好的。”他想笑笑,可脸上肌肉不听话,没有笑成。
“我不如你,”王小清看着朱锐,泪珠儿终于滚了出来,“自从得了这个病,我就常常难过,晚上偷偷地哭。我才十八岁,比小梁还小……”
一阵感情的震颤滚过四个男子汉心头,大家都不敢看她了。
“活着,多有意思呵!”王小清悲哀的眼中闪出一丝神往的光。她象自语似地说:“我护理过的病号,好了,出院了,高高兴兴的……有的专门来跟我告别,有的临走忘记了,还有的因为生我的气,最后也不理我……多有意思啊,可我,我为什么要死……”她抽泣起来。
朱锐突然冲动起来,两手在胸前乱摸:“别,别……我不想死了,我交给你……”他从衣袋里掏出个小药瓶,眼泪乱流,“这是毒药,是我住院前偷偷准备的……我还自以为是,其实我算什么东西呀!”
“低声点!”杨大成低声吼他。
他拿着个小药瓶,手在发抖。王小清对他叹了口气说:“你会好的,其实你把手术看得太可怕了。我们年年都有手术以后痊愈出院的。”她又象想起了什么,把眼光落在刘玉身上,“刘玉!”她亲切地叫他。
“嗯。”刘玉站在床脚,心神不宁地低着头。
“你来。”
刘玉不敢抬头,往前挪了一步。
“你来呀,到我床头边上来。”王小清声音微弱地说,“别生我的气吧,刘玉。”
“不……不……”
“不要生我的气。我是说你写的那个信。我还小,不知道怎么谈恋爱,我害怕,而且我还有病。我……我没有权力害别人……”王小清又哽咽起来,“我……我本来想好好跟你讲清楚,可,可又怕讲不清。我不该用那种方法刺激你,可我又怕你再写……”
“我……不……”刘玉突然转身推开三个病友,冲出门外,一屁股蹲在走廊里,放声号啕起来。一边哭,一边没头没脸重重地打着自己……
他惊动了值班护士……
两天以后,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
从礼堂那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哀乐声,从阳台外边传来了淙淙的溪流声。
很久,他们才开口说话。
“俺的那封信,到底没能念给她听!”梁黑子一张口,眼睛就湿润了。
“她留恋生命,因为她爱别人,她没有绝望。而我不怕死,因为我自私,我绝望了!我胆小,我真渺小啊!”朱锐似乎在梦呓。
杨大成默默站着,把手指捏得嘎吱吱响。
刘玉哺喃地说:“她怕癞蛤蟆……我连个对不起都没顾得说……”他突然想起什么,对大家说,“她害怕晚上一个人呆在外面!”
三个病友都愣愣地望着他。
“晚上,她在太平间,咱们去陪她!”他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