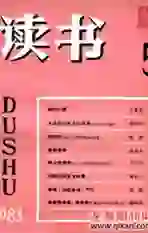安·佩蒂《焚烧的屋宇》
1983-07-15之岱
之 岱
如果说三十年代美国文坛明星是海明威,四十年代是诺曼·梅勒,五十年代是塞林格,六十年代是索尔·贝娄,七十年代是乔埃斯·卡罗尔·欧茨,则八十年代最有希望的似乎是安·佩蒂了。
安·佩蒂一九四八年出生于美国东海岸,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研究院,以后即留在母校当文学教师,经过四年的不断向《纽约人》等报刊投稿,还不到三十岁就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歪曲》(一九七六)和《秘密与意外》(一九七八),另外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冬景》,为此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的文学奖。
一九八○年她又出版长篇小说《各得其所》,去年秋天又发表第三部短篇《焚烧的屋宇》。将近十年的努力,使安·佩蒂逐渐得到美国的读书界和文艺批评界的承认。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等作家,而是美国新进的重要作家之一;因为她善于捕捉美国青年一代的气候和趋向,正如三十年代海明威和费茨杰拉特那样敢于使用准确简洁的语言创造新型人物,从而为读者留下了强烈而又难忘的印象。《纽约时报》曾称安·佩蒂有非凡的才华,她的作品侵入了契佛和厄普代克擅长叙述的丰富的领域。而《时髦》(Voque)杂志则把她的近作《各得其所》誉为四十年代卡森·麦卡勒斯的《心灵是孤独的猎人》和五十年代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如今,美国读书界欣赏安·佩蒂的新作,称之为前线来的捷报,人人以先睹为快;目的是要了解这一代难以捉摸的青年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新事物,那批散居在纽约郊区的时髦人物又有了些什么新的争吵和窃窃私议。他们之中有的虽已迁居加利福尼亚州,因为那里终年不见雪花,反而怀恋起东海岸来了;冬景就得象个冬天,雪花不必装在塑料小包里才买得到。这些青年男女一个个渐省人事,难道还相信人生就只有恋爱而已?他(她)们比前辈的时髦人物过得更理想吗?男女之争是否分了胜负,还是仍在争之不休?生活、自由、幸福的追求有无进展?这正是广大的读书界要知道的问题。
《焚烧的屋宇》由十六个短篇组成,可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看来似乎并不美妙。幸福依旧是每个人孜孜以求的;只要还在追求之中,则幸福对每个人说来,总还有点儿意思。但是到了某一阶段,多半都泄了气。有的则勉强维持局面,一个接着一个换对象,象攀高梯似的头晕目眩,愈近顶点就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级,愈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十六篇故事中,除了两篇以死亡作主题,其余十四篇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遭殃的倒霉鬼。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生活,生活过得太舒适了。出乎意料的,则是人人在争取某种自由。实际上,他们一无拘束,也没有不可摆脱的枷锁:不论是什么职业,婚姻、爱情的山盟海誓,甚或至于身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等等。这些问题,在她的笔下都是动荡不定、一无约束力的。因此一切事物看来都如过眼烟云,难以捉摸,临时应付;明天都得从头来过,谁也不能信赖谁。男女双方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幻无穷的实用主义激情来相互依恋;正因为如此,所以谁都是小心翼翼,唯恐由于无意的中伤或无心的姿态,触怒对方,而关系就此告吹。
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高呼自由。现在的青年则把这种自由理解为堕落的自由,或飘飘欲仙、无牵无挂的自由。如书中的主题小说《焚烧的屋宇》中,一位年轻的丈夫对妻子说,“男人都爱把自己比拟为蜘蛛精或超级人(Superman)。你不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向往于向星空射去……从太空中看凡人的生活……我已经飞向太空了。”安·佩蒂的故事写的不是一般的悬疑,而是使用一种悬念笔法,由读者自去捉摸下文和故事含义。
作者所谓的“自由”是想入非非、飞离生活的自由,特别是各个故事中各式飞离生活现实的男女主角所具有的异样感觉。但是在生活里,说到底终究要回到现实,或是说从太空飞回地上来的。别看蜘蛛到处爬,它的目的就在于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青年男女则在找寻安乐窝,可惜他们所找的却是陷阱。《焚烧的屋宇》中一再暗示“家”已非复是安乐窝了,因此包括共同生活中最起码的家务:做饭,喂狗……都弄得人心神不宁。有些青年人为了怀念幼时欢度圣诞节用的那种松树,宁肯抛弃眼前的城市生活,去追寻旧时宾夕法尼亚式的农舍,床上铺着的镶拼式的花被,留声机上放着的老唱片,等等。
故事的气氛和细节,往往是在不经意中灌入读者的印象之中的,正如屋里安放的一只花瓶或是一座时钟,毫不使人起眼;用同一种语调来处理恐怖事件和生活中的琐屑,就会使读者猝不及防而显得惊慌失措,这就是安·佩蒂的风格和笔法。这一技巧现在已大为成熟,而且在安·佩蒂的创作中有所发展。同她早期的作品相比较,这种使用特殊的伏笔伏线的方法现在更为得心应手了;对她笔下的人物既不粗暴对待,也不令人反感,倒是使读者更能同情这些男男女女。她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只表示一种惋惜与遗憾。故事中绝大多数男女,都以客客气气的分手告终,但作者绝不提分手的起因而只提影响和后果,因此谁也无法指责对方应对罪过负责。这样的结局难免冲淡了道德意义,悲剧不以地狱告终,只是某一个人之被孤立或遗弃,竟似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月球上一般。这就是美国当前青年所面临的生活之谜,而安·佩蒂就是利用这一使人飘然而又略带忧郁的气氛,来吸引住同样囿于生活之谜而不能脱身的青年男女读者们。
书评家玛格丽特·亚特乌德说:“〔安·佩蒂〕的文笔和才华,当然不仅于此,可是她的过于含蓄的淡漠和黯然神伤的情绪,不免会使读者不耐。而她的素材与生活视野又局限了她用武之地。她如今正象一位芭蕾舞的主角,而你只能向熟悉她的人来推销她演出的戏票。”旨哉言乎!
(Ann Beattie:The Burning House,266pp.Random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