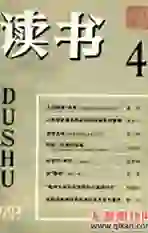骆寒超与《艾青论》
1983-07-15罗仲鼎
罗仲鼎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里那种质朴而深沉的抒怀,富有感染性和启示性的形象,一下子打动了骆寒超的心。三十一年前的骆寒超还是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从此,迷上了诗歌,与艾青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中华业以后,骆寒超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他才十八岁。在这所古老而又年轻的高等学府里,师友的教导和鼓励,进一步激发了骆寒超探索诗歌的热情。他在诗歌这座神秘的殿堂内徘徊,巡视,考察,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有关中国新诗的笔记。那时他决心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新诗史,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是骆寒超不管那一套。他是那种一旦认定目标就决不回头的犟脾气。
应该说骆寒超还是幸运的,就在他多少带点盲目性的追求中,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著名学者陈瘦竹先生给这个执拗的青年人指点了迷津:“研究中国新诗的历史,首先要确定一个能够承前启后,代表新诗发展主潮的诗人加以研究。”这一句话使他顿开茅塞,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热爱和景仰的诗人——艾青。大学二年级,骆寒超完成了一篇两万字的学年论文:《论艾青的创作道路》。一九五六年秋天,他又决定以《艾青论》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从此开始了对艾青的全面研究。当时,学校聘请南京师范学院吴奔星教授做他的论文导师,吴先生对他说:“研究艾青,也必需了解现代派!”于是他又开始广泛阅读徐志摩、李金发、闻一多、戴望舒、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深入研究形成艾青诗歌思想艺术风格的各种源流……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劳作,十一万字的《艾青论》初稿完成了。论文受到了陈瘦竹、吴奔星以及刚从国外讲学回来的赵瑞蕻等学者的肯定评价,并且打算向出版部门推荐。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艾青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了政治冤屈。研究艾青的青年学生骆寒超也未能逃脱厄运。他“怀着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屈辱”,被分配到东海之滨的浙江温州远郊的一所中学,开始了漫长而艰准的生活历程,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并没有扑灭骆寒超心中的希望之火,他是坚强的,执着的,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些“迁”。他随身带着使自己几遭灭顶之灾的《艾青论》原稿,执拗地写着一篇篇无处发表,也不想去发表的诗歌论文。他并不叹息,因为心灵深处还埋藏着希望的种子。……但是,十年内乱的灾难蔓延到全国各地,连僻处边城远郊的骆寒超也未能幸免。《艾青论》以及其它几十万字的文稿和资料统统被付之一炬。……他的心被烧伤了,他仿佛觉得自己“生命的列车突然进入了一个阴暗、潮湿而又漫长的隧洞,它仿佛通向遥远的天际,永远没有尽头”。
然而,暗夜正是黎明的起点。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骆寒超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一九七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党委改正了他的错案。在师友的鼓励下,骆寒超迫不及待地在“一堆书刊和文稿的废墟上,捡回了残存的《艾青论》提纲,毅然重写这部稿子。”不到半年时间,十六万字的《艾青论》脱稿了。同年十一月,陈瘦竹、赵瑞蕻两位老教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向艾青谈了骆寒超写作《艾青论》的经历,老诗人被深深地感动了,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因为研究自己而受难的无名作者。一九八○年八月,骆寒超到了北京,艾青热情地请他住在自己家里,详细地向他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自己的人生见解和美学观点,也谈了他对《艾青论》的意见。一个早秋的薄暮,两人坐在房间里已谈得很久了,老诗人指着桌上一大堆从全国和世界各地来的报刊、信件说:“它们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期评述我,谈及我和寻访我的,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关怀着我,为祖国和人类的光明而歌唱还有什么可犹豫和惧怕的呢?!”这一席话使骆寒超对艾青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们两人的心完全相通了。回来以后,他又对文稿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和扩充,二十万字的《艾青论》终于完成了。从一九五六年秋天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写定,历时整整二十五年!
作者在《艾青论·后记》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充满感情的话:“这部稿子纠缠了我整整二十五年,可以这样说,我的青春,我的屈辱和眼泪,我的沉重的叹息,以及我的再生的喜悦,都和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骆寒超写作《艾青论》经历了如此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正因为命运之神不由分说地把他和艾青紧紧地捆缚在一起,这就造成了《艾青论》不同于其它一些论述艾青诗歌的文章。读者可以感到它有一个异常鲜明的特点:作者似乎并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他的心在写;在整个《艾青论》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并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评判者,而是一切事件的热情参与者。读着《艾青论》,我们仿佛觉得,作者心灵的脚步始终伴随着诗人,伴着他来到了大堰河的乡村,伴着他穿过监狱的大门走上诗坛,伴着他高举火把迎接光明,伴着他越过迷茫的旷野,沐浴在延河边上。作者为艾青的成就而赞叹,为艾青的迷茫失误而惋惜,为艾青遭受冤屈而悲愤,又为艾青获得新生而欢呼。这就使得《艾青论》这本评传具有诗的魅力,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对于一个严肃的评论家,热爱不应该导致偏爱,景仰也不能够变成盲目崇拜,如果一味用热情的赞颂来代替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评价,那是没有意义的。《艾青论》的作者没有让自己对艾青的热爱和景仰之情淹没理智的客观评价。在《艾青论》中,作者从不回避对艾青各个时期思想艺术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既不是表面化的现象罗列,也不是简单化的政治鉴定,更不是粗暴的帽子和棍子,而是把历史时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个性紧紧结合起来,进行辩证的、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作者、对读者都颇有帮助。
《艾青论》是以艾青生活道路为中心线索来对他的诗歌创作事业进行考察的,是一本艾青评传。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纵线型的研究体例,而努力进行横向的面上的发掘和开拓,《艾青论》之所以称为“论”,而不叫做“传”,正是反映了这种意图。作者总是注意把艾青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放在时代的各种思想思潮和美学风尚的交汇冲突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来考察,尤其注意把艾青放在六十年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与当时各种诗歌流派作深入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中去考察,从而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多年来,艾青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在人类追踪客观世界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他的感情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并且扩展到全人类命运的疆域。”在艺术上,他一直不倦地进行着诗歌艺术的探索和成功的创作实践,“走出了一条朴实而又焕发着独特光彩的创作道路”。因此可以这样说,《艾青论》实际上是以艾青为中心,论述了中国现代诗歌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表明了作者对新诗发展历史以及趋向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酝酿已久的著作——中国新诗史的雏形。
《艾青论》对艾青诗歌所作的艺术分析不是只重视局部的具体的艺术特征,而能够着眼于整体。他紧紧抓住艾青诗歌艺术中的形象、意象和语言等要素,从它们的发展变化和相互关系中来说明它们的特点,而不纠缠于枝微末节。例如在谈到艾青诗歌的散文化倾向时,作者指出,这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因为艾青诗中的意象特别丰富,意象组合特别繁复,格律的句式无法容纳,非得用散文结构的句式不可,于是就出现了诗歌形式上散文化的倾向,“这是艾青式的诗的形象的绚丽多彩所达到的一个必然结果”。又如在分析近年来艾青诗歌中出现的哲理化倾向和构思的机巧时,作者对此并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着重指出哲理诗往往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从感觉导致形象的联想,另一种却导致理念的推论。巧思也有两种,一种是引起形象的联想,产生感受,达到抒情的目的;另一种是引起哲理的感悟,产生回味,导致思考的目的。在艾青近年的创作中,既存在前一种情况,也存在着后一种情况;前一种是应该加以鼓励的,而后一种倾向却是应该防止的。这种辩证的、细密的艺术分析的方法,不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作者本人,都是很有启发的。
骆寒超在《艾青论》中曾经说过这么一段含义深刻的话:“艾青生涯里默默无闻的二十年,并不意味着他诗人生活中的一长段空白,可以说,这是艾青在突破他以往的创作水平前扎实地积累生活和顽强地探索人生的沉思期,而坎坷的经历又使他获得了一个真正能投身于人民大众实际生活中的大好时机。”《艾青论》的出版虽然推迟了整整二十五年,但是我也想说,这二十多年也并不意味着骆寒超研究事业的一大段空白。拜伦曾经说过,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与语人生。对于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坚强的人,厄运的打击和坎坷人生的经历,不仅不会使他意志消沉,反而会使他的精神更加昂扬,思想更加成熟,感情更加深沉,胸怀更加宽广。正是这种苦难的经历,使他能够满怀激情地去分析,去研究,去思考;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才使他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