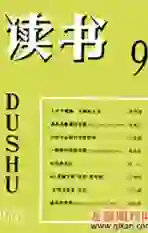《辛笛诗稿》自序
1983-07-15辛笛
辛 笛
这本诗稿结集了我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八二年诗作中选出的百余首,共分五辑:
一珠贝篇(一九
三三年七月——一九三
六年七月)
二异域篇(一九
三六年十月——一九三
八年)
三手掌篇(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
四泉水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
五春韭篇(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这五辑在时间的顺序上本来打算是由近而远来排列的。我是经过思考之后,有意识地这样做。自认为:任何人不论他在那一方面的写作都应该是以此时此地的作为来判断,但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好意相告:这样远近倒置的编法总令人感到有些别扭,不易从发展中看变化,还是以编年体为好。我感谢他们的建议,因而在此改作排列如上。
多年来,诸承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友好都曾亲切地向我指出,以往出的《珠贝集》和《手掌集》中有一些诗作抒情性较强,因而得到他们的偏爱。这是我一直衷心铭谢,引为宽慰,而又感到十分惆怅的。因为那两本小小的诗集当中,有不少实质上是幼稚而感伤的东西,值不得大家的称许。随着年事和阅历的增长,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的深化,我总觉得提笔写来,如果能多触及一点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哀乐相通,才能说得上是称心而言的真情实感。
我爱上诗,自幼年始。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常把唐诗藏在四书五经下面偷读,戒尺也镇不住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篇使我入迷,就此养成我爱好诗歌的习惯。至于懂得宋诗的一些不同的风味,那还是渐入中年以后的事了。回忆最初产生写诗的欲望却是这样几件小事,举例来说,一、我到七、八岁还在念私塾,父亲是个老举人,日课之余,还督促我上晚学。窗外月明如洗,秋虫唧唧,我正好背诵欧阳修的《秋声赋》,心中模模糊糊地萌发了写诗的兴致。二、十岁左右,第一次和母亲离别,男孩子是倔强的,没有流泪,但送别回家后我蒙被大哭,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诗情。三、十二、三岁时,赶上军阀混战,全家在乡间逃难,一路上正是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时节,而流离途中无心观赏,感受到一种愤恨、惋惜又夹着凄凉的心绪。在这样思想和感情交织激荡的时候,我总是渴想用诗来表达,于是我学写起旧体诗。
考入南开中学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年轻的心。十六岁,我试写了第一首白话小诗,是很不象样的东西。随后,由于在阅读鲁迅和创造社的书刊的同时,大量接触到旧俄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哈代、曼殊斐尔等人的作品,以及斯宾诺莎、叔本华的哲学影响,我常常徘徊于呐喊和哀愁之间,对当时现实深致不满,却又无力反抗,既探索而又
大学读书时,我曾广泛地吟味了西方诗歌,如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英国湖畔诗人以及雪莱、济慈,十八世纪蒲伯,更早的有密尔顿、乔叟,但我对莎士比亚和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敦的诗篇,下至法国象征派的玛拉美、韩波,现代派中的叶芝、艾略特、里尔克、霍布金斯、奥登等人的作品,每每心折。同时对我国古典诗歌中老早有类似象征派风格和手法的李义山、周清真、姜白石和龚定庵诸人的诗词,尤为酷爱。在校内进步学生会的支持下,我主持了《清华周刊》文艺栏编辑工作,并在《文学季刊》、《水星》等刊物上,发表诗作,一九三五年和弟弟辛谷合出第一本诗集《珠贝集》,现大部收入珠贝篇。
毕业后,在北京(当时称作北平)作了一年中学教师。随后,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在那里,我会晤了艾略特、史本德、刘易士、缪尔等诗人,时相过从,也亲眼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荒原”景象。度假期间,我曾在巴黎的一些画苑、博物馆里流连忘返,在伦敦也听过一些音乐歌唱演奏会,使我深深爱上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印象派绘画和音乐的手法和风格,在写作中受到不小的影响。远离故国,孤身负笈异域,不禁沉浸在浓重的乡愁之中,写了一些诗,有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当时戴望舒等主编的上海《新诗》月刊上,现在收入异域篇。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再也无法安心读死书了,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忙于在英国各地四出奔走,宣传募捐,支持抗战。当读到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时,我满怀振奋,看到中华民族希望的曙光已经开始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就此下了决心从缠绵的个人情感中走出来,基本搁笔,不再写诗,以促成个人风格的转变。
回国后,我先在上海的大学中教书。太平洋事变起后,大学停办,改入银行界工作,在地下党的外围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银梦在死叶上复苏,我才又拿起了笔,重新开始写下了一些诗作,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领悟到古中国凡鸟在大时代中的啼鸣,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它一定的意义。这一期间,除先后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和《中国新诗》月刊编委外,一九四六年编辑出版《民歌》诗刊一期,即被迫停刊,一九四七年收集了在《文艺复兴》、《诗创造》月刊、《大公报》、《文汇报》等处发表的诗文,出版第二本诗集《手掌集》和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现将诗作部分连同其后刊见于《中国新诗》月刊的一些短诗收入手掌篇。
我这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也是到过西方不少国家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民族走上真正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解放后新的生活天地吸引了我,改入工业战线工作,一切从头学起,无暇写诗。与此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人第一,写诗第二。即使偶尔有时动笔,现今可以看得过去的也只是零星有数的几首,在此选了三首收入泉水篇。一位评诗的友人曾经引用了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旧译作梵乐希)的话:“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我感谢他对我的激励,我也但愿能够如此。可是当我从个人内心走入广阔的社会时,不可避免地偏到另一个极端。我的写作在艺术方面大大地忽视了,这无疑是一种缺陷。十年内乱,我和绝大多数同辈一样,在经受种种磨难和折腾中,当然也被剥夺了提笔歌唱的权利。之后,我也正好对诗歌创作中的偏颇加以反省,更深地理解到诗的艺术在表达思想内涵时的感染力量是何等重要。在此春回大地之际,七十岁的我返老还童了,洋溢的诗情又往来于胸中。春韭篇中所收的四十余首就是近六年来所写的一部分。在屈指可数的余年中,我又开始了思想和艺术风格上的一些尝试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自己仍然感觉远远不能满意。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有机会出国去加拿大参加第六届国际诗歌节。会上,诗人亨利·拜塞尔向我谈起:难道现实主义的诗歌就不需要讲求艺术了?这话对我是一个有力的提醒。这也再次使我坚定了以下的看法:诗歌是不能脱离现实的。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诗歌的源泉既是来自生活,就必然和社会、时代密切相关联。但诗终究首先必须是诗,而不是政论,一定要有丰富的想象,有思想的深度,谋求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同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给想象留下空间的容量,这才能增强诗歌的魅力。人有七情六欲,感情是十分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诗歌要表达浓缩的真情实感,也可以说要有七情六感。照我的初步设想,六感就是:真理感、历史感(古今中外的传统)、时代感;形象感、美感、节奏感。前三者主要从内容上讲(即思想性),后三者主要从形式上讲(即艺术性)。诗歌既是属于形象思维的产物,首先就必须从意境(现代化说法就是指印象、意象等)出发。善于捕捉印象是写诗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五官甚至包括第六感的官能交感(或称通感)、亦即运用音乐(声调、音色、旋律)、绘画(色彩、光影、线条)和文字(辞藻、节奏,包括格律)的合流来表达、促进并丰富思想感情的交流。好诗总要做到八个字:情真、景溶、意新、味醇。
这次对自己过去诗作进行一次结集,对我来说,确是一次有益的回顾。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固然,往日的很多篇章,不要说到了“文革”十年一扫而空,自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也是毫不心痛地随写随丢,了无足惜。《珠贝集》(一九三五年)至今更是遍寻不得,就连《手掌集》(一九四七年)现在根据的也还是香港友人寄来的那里书商前些年私自影印的本子。说来惭愧,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逝去了,自己写成的诗实在少得可怜。而且也写过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每一思索之余,心中总是十分难过。但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平生最喜爱诗歌,甚至在十年内乱时期,在牛棚中无书可读,无话可讲时,我还忘不了暗自哼两句心爱的诗,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古人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简明而全面地道出了诗的功用,也是我在本职工作之外始终丢不开诗歌的理由,我深信广大读者一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
最后,检阅了三十五年前出版的《手掌集》后记,我觉得在今天仍然能表达我的心情,因此,将它附录在此,作为结束语:
“奥登(W·H·Auden)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诗集冠有小序。他说:在每一个作者的眼光中,自己过去的作品大抵分为四类。类一,是不堪卒读的东西——他一直后悔着何以写了出来。类二,一些很好的意思——他所引为最痛苦的——总是由于才华短拙或率尔操觚而糟踏了,没能写到好处。类三,一些自认为尚看得过的篇什,但缺乏重要性。任何集子无可避免地必以三者为主。因为,第四类果然才是他自己真诚激赏的诗歌,但若即以为限,结集成书,那么他的集子可就薄得太令人气短了。
“我很喜欢奥登这一段简洁完整的文字,虽然写来平易,创作的甘苦却给他轻轻道破。我写了这些年的新诗,纵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用在与诗歌全不相干的研究和工作上,写存的诗原本不多,更禁不住拣选,而论起品质来——倘果有何品质可言,却大体属于奥登所列举的前三类的东西。……除了惭愧,我竟一无可说。谨此感谢每一个读者,他将是我的最适当的批判人”。
一九八二年
(《辛笛诗稿》,王辛笛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