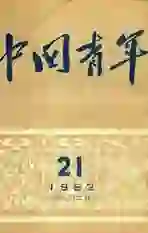建设伟大水道的人们/古象
1952-08-16鲍里斯·波列伏依
鲍里斯·波列伏依
“这道溪流在地图上另有名称,可是我们喊它作“蛇沟”,因为这里面,蛇装得满满的,特别在最初,第一条吸泥船从河边驶来的时候。这名称上了口,我们甚至打乱告的时候也山上它:蛇沟的工作计划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多少……。我又动了吗?。请你原谅,我一定站稳。”
亚历克赛·依兹麦洛夫,一个在工地上出了名的一条吸泥船的总技师,满脸都是不耐烦的神色。他从来没有让人画过肖像,要他站稳显然是一个苦刑。那画家把他摆了个姿势,站在吸泥船上层甲板的栏杆前。他那宽阔的前额和嶙峋的、雄鹰似的侧影,锋利地刻划在峻削的、正逐渐退却的河岸的背景上,那儿的松弛的沙土不断地崩裂而落到河水中。在这个姿势中,残留在他左颊上的那个紫色的大伤疤是看不清楚的。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的脸,而此刻脸上又是毫无表情的。
画家是在很闷气的感情中。他用像皮来工作还比用铅笔来得时候多,显然说明他对于自己和模特儿都不满意。“就这样下去,就这样。不要理我。把我忘记。我不在这里。只是谢谢天啊,你的头不要动。”他恳求着。
“你正要和我谈古象呢。”我提醒那位技师。“啊,对了。可是我先要把周围环境给你介绍一下。因为它跟所发生的事情有直接关系。我们正在蛇沟的口子上工作。河床很好,是沙土的,像硬麦粉,筑坝最合适了。挖土机在溪流的上游地带工作者,那里的土比较乾,它们比较容易把这些土装上卡车去。
亚历克赛·依兹麦洛夫是退伍的坦克部队里的校官,在卫国战争中经历得真不少。他从最初起就参加了战斗,他的坦克燃烧了不止一次,法西斯也真的射中了他,可是没有把他杀害。他躺在坑里的同志们的尸体中间,入夜后就爬出来,摸回了村庄,有些集体农民收容了他。伤愈后,他越过敌人防线,回到自己的部队里,又一路打去,直打到易北河上。他穿的那件古老的军衣上新换了领子,口袋上方勋章的针扣还留着痕迹,左颊上还有那扭曲的伤疤;但战斗生活的遗留还不仅仅这一些。他整个风度和说话的姿态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兵。
“我可以讲下去吗?”他问那个画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不要动。”画家回答,眯起眼睛来,好像在瞄准一样。这一刻敏锐洞察的眼睛似乎在解剖那模特儿的脸。
“我们已经提出了保证,要超额完成百分之二十的任务,来庆祝五一节。可是春水发了,我们损失了一个半星期。因此我们召开了会,决定放弃节庆日,发动一个全面的突击来弥补损失的时间。事情就有了起色。和我们展开兢赛的小组里党的组织者从坝上打来了电话:“五一节致意!你们搞得不错……”可是,突然间,正在我们像房子着了火那样紧张的时候,机器房间一声巨响,响筒就停住了。一定是一块大石头或者什么哽住了,我们想。你可以想像我们当时的感情的。我们连节度日都牺牲了,而现在却停工啦!”
“忙坏了修理机器的同志。片刻间,他们把吸泥机的龙头打开了。我浇进雨铅桶水去,洗掉了沙子。一点不错,吸泥机的两个牙齿切断了,那里面嵌着一块大石头,总有四公斤重。鬼才知道它怎么跑到这柔软的河床里来的。照地质学家的说法,这里完全不应该有它。而且它又怎么钻进那保护网的呢,又是一个神秘。我们可没有时间来破除神秘。我们用破纪录的速度给换上了牙齿,这成就使我很骄傲。两小时多一点儿吧,我们又在最高速度里将软浆倾泻到坝去、这个我且不谈它。我们修理完毕,我就向水流走去,打算喝点水,这时首长来找我了,说,‘依兹麦洛夫,你知道是什么吧?给我们开这个玩笑的并不是石头呢。‘不是石头?那么是什么?‘我还不能肯定,可是我看,它很像史前期的古生物的牙齿。照尺寸看:可能是古象的。说着,他把它拿了出来。果然是一颗精致的牙齿,大约四公斤重。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欣赏它,我们赶快把吸泥船开上前一些。以免再遭受史前期的古生物的‘袭击。可是交班以后,我们正打算回家去,党的组织者把我们拦住了。‘孩子们,我们不能一摔手就走。他说:‘我们的集体农民还没有饲养过大象呢。我们有了伟大的发现了。既然我们捡到了它的牙齿,我们就对科学界欠了一笔账,那古生物的其余的残骸也得挖出来。我们必须从全国的观点来认识这个古象的价值。他
说:“让我们四处找一下,把它的遗骸全部发掘出来,不然的话,坝筑成了,水一放满,又要一百万年,科学界才能找到这种古象。
技师认得起劲了,他的神情就越来越活泼。他的脸刚不久还是阴沉沉的,缺乏表情,使得画家大大失望的,现在焕发起来了,黑眼珠里闪耀了温暖和快乐的光芒。他似乎突然间年轻了,现在红润的脸上连那个伤疤也看不清楚了。画家也完全不用橡皮了,他的手在纸上迅速地移动,他的眼睛,一忽儿睁大,一忽儿眯细,将他的模特儿脸上的每一个经过的表情都吸收了进去。
“党的组织者知道,要发动大家都起来的最好方法是他自己以身作则。所以他跨上了一条小船,开始把外衣脱下。跳下了还没有全退的冰冷的春水里。他游泳,潜水,浮上来又跳下去。伙拌们都已经准备回家去,至少还赶得上节庆日的尾巴,可是现在他们也回来了,脱下了衣服。轮机手跑来了,嚷著说人人都下水受冻是没有道理的。他把人分成两队。一队下水,另一队在船上取暖。同时,党的组织者从水产喊叫起来:“我找到东西了,石头还是骨头我还不清楚!”我们把它拉了起来,当然若是另外一颗牙。”
“连我们的首长也忍不住了,他也下了水。我不多讲了。我们就这样搞下来了,一班下水,另一班就工作。我们一米缠又一米缠地直到我们把这一段河床整个儿搜索完毕。机械工人还给自己制造了特别的钳子。你知道,我们干的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掏出了许多骨头来。天色很黑了——我们开亮了大灯——那时我们拉起了一只巨大的象牙,好重的家伙!可是我们上上下下的摸,总没有找到那另一双象牙。我们下的结论是这条古象当年必定是个角斗家,在太初时代一场恶斗中损失了一只象牙。五天之后,我们在沟底又找到了它的头壳。我们用起重机把它拉上来。总而言之,一星期之后,我们的吸泥船上,有了一个正规的设备俱全的自然博物馆。”
故事讲得有劲,技师就掉过头,用手指出那曾经是博物馆的地点来。于是他想起来了,向画家投出了犯罪的眼色。可是画家不再生气,他嘴里衔着两枝铅笔,正用第三枝铅笔飞速地工作着,工作这样地紧张,来不及把铅笔从嘴里拿下来,只用眼神告诉依兹麦洛夫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姿势去。
技师腼腆地服从了。他努力不再作大动作,继续他的故事:
“我们从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关于史前期的巨大生物的书。我们还找到了一幅古象骨骼图,我们就设法把我们挖起的骨头按回来排列。结果,我们所发现的只是一部分头部和山些脊椎骨;其余的都找不到了。我们尽量找也找不到了。我们自认为这已经不算坏了。那个镇上的古老的博物馆曾经被法西斯焚毁,我们这副骨骼虽然不大完备,送给新建的博物馆还不失为一件上好的礼物。就在那时候我们要到镇上去配零件,伙伴们委托我把这件礼物送给博物馆。我们用稻草将这些一史前期的胜利品谨慎地包扎起来,放在卡车上,就出发了。我迅速把事情办妥当后就开车上博物馆。找到了馆长,他是一个白胡子老人。您瞧,有了不起的意外的东西送给您,老祖父。我这么想。“请容许我,”我说话了,“以伏尔加——顿运河的建设者的名义,献给您几件古象的遗骸。”你信不信,他一点都不在意呢。自然,我必须说,他是很高兴的。“从蛇沟来的吗?”他问。“一点不错”,我说,“从蛇沟来的。可是,我倒要问一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业余时间里,从事于猎取古象的工作了呢?“代替回答,他把我带进了隔壁的房间。在那里面,地板上放着好些巨大的骨骼。“这是四立方米挖土机上的工人送来的。”他说。“这是开动那些小的按土机的同志们的礼物。我敢说你们是在河流的下游工作的,是吗?“这又对了。”我说,并且问他怎么知道的。“你看这张图吧,”他说。“这一条古象有极大可能是在洪水时节。淹死在这个沼泽中间的。你看,河向这方向流,骨骼的许多部分就给水流冲列河流的各段去了。自然,河流后来改道了,留下来的就只有你们称为蛇沟的这一条小溪了。现在,你们这些在小溪的上上下下工作的人把全部遗骸都挖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结果是有考古学癖好的不仅是我们这一帮聪明人。挖土机的伙伴们的确赶在我们前面了……
“好了,这就是蛇沟古象的全部故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听得这样高兴。总起来,我们的古象是比不上他们在齐姆良海所发现的东西。那里的建设家帮助考古半家发现了在未来的齐姆良海底的古城萨尔克尔。他们硬是把沙子筛过了一遍,连一颗小珠子或一件小玩意都给科学界保留下来了。古象是好大家伙,只要你发现了它的痕迹,找到它并不困难。”
技师大笑起来,可是立刻抑住,斜视画家。画家正在作息后的修饰,现在他眯细着眼,批判地视察他的作品,然后签下名,又在右下角上写了一个“51”号。那时他从本子上撕下画页,一跃而起,把宜交给亚历克赛,依兹麦洛夫。
我从技师的肩上望去。画得像极了,一而且那个讲故事的脸一点不冷酷,一点没有我们相识的大部分时间里的那种无表情的表情。他生动、活泼、愉快,像那个古象故事讲完的时候的脸色一样。画中的面貌比真人的面貌年轻得多。
“我问你,你多大了?”我忍不住问他。“二十九”依兹麦洛夫回答,那扭曲的脸微笑了。“你不信我?,我给你看党证……没有滋法,只好怪战争。”
(徐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