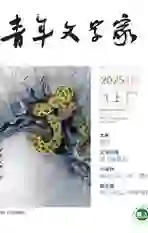如“镜”的宝水: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宝水》中地青萍的身份建构
2025-02-20苏安航
《宝水》是乔叶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聚焦于现代乡村世界,展现乡土中国的变迁。文本以主人公地青萍为第一叙述人,讲述其见证了乡村发展的同时,自身对童年时期创伤记忆的态度也经历了从逃避过渡到了主动和解这一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平衡又波折的精神转变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理论。自我确认这一过程的完成,符合拉康的镜像理论对主人公身份建构的切入,镜像场域因素的对比也影响了她从身份焦虑到自我定义的过程。最终,在后镜像时期她完成了主体身份的建构。
一、他者的构建:初期身份的探寻
拉康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在其镜像理论中提到,婴儿在6~18个月的成长过程中,通过镜子中他人和自我的映射逐渐完成自我感知,从完全依赖他人向自己独立转变,从而确认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在自我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还存在着代表社会法则和文化秩序的“大他者”与代表自我投射和理想自我的“小他者”。
在宝水村这个“大他者”的环境中,出身于福田庄和象城的她并不能清楚地分辨自己在宝水村的身份。虽然主人公与宝水村的住民都出身于豫北农村,但由于文化人的身份标签,使得她在介入宝水村建设的大事小情时只能以一种介于“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微妙地位自处。她觉得自己“既不是白蒸馍,也不是黄窝头,好像就是花卷,一层黄,一层白,层层卷着,有时候能利落分开,有时候根本就不能掰扯清楚”(乔叶《宝水》),身份焦虑一直在困扰着她。而主体只能在与他者的碰撞和相处中才能发觉自己的存在。于是,刚进入宝水村的地青萍从他者的目光与话语环境中开始构建自己在宝水村的定位。如在村委会工作,担任妇女主任一职的大英、乡建专家孟胡子等人都视她为外乡来客;在西掌组长张大包、秀梅和小曹等人的眼里,她是人见人敬的“地老师”;在与她处于亲密关系的老原和九奶眼中,她是孝顺认真的好儿媳和好闺女……在此过程中,主人公不断修正着自我的身份,来自外在他者的感性形象形成了她的自我主体。即使是在她面对村民口中的“地老师!原家的”这一调侃时,在“浑身的血就突然热了一下”的感觉过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酸涩又真实的情感。她虽然在宝水村生活着,但她内心依旧存在着与村庄、村民之间的隔阂,不过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有了适应这里的想法。这是处于分裂状态下的自我,组合成最初形象之后迈入“小他者”的第一阶段。
语言的使用变化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也起到了逐渐推进的作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构成了拉康对主体意识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那种无意识的“我”也是靠着一个巨大的意指关系的能指链来运作的。在地青萍的人生发展阶段中,她回忆起自己刚从福田庄去象城读书时,因语调里的乡气被大家嘲笑的过往。她的那句“怪卓哩”被城市里的同学们争相模仿,让初来乍到的她产生了自卑感,这种表现其实是一种能指链的断裂。同样,在宝水村乍一听到不知所云的土家话时,对于刚从象城到宝水村并早已熟悉普通话的地青萍来说,也总会产生一种与自己所习惯的生活环境毫不搭边的割裂感。在“扯云话”这一最普遍频繁的叙事场景内部,不管是“接生毁眼”的典故还是“种谷要种稀溜稠,娶妻要娶个剪发头”的民歌,都给她展示了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土壤和语言环境,为她编写着独属于宝水村的文化符码。在城市与乡村两栖的她,语言交流的困境也使她在原地周旋,得不到他者的认同是造成地青萍自我身份困境的根本原因,与宝水村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相顺应、融合也是她的手段之一。于是,她带着别扭与陌生的体验再次被他者建构,去尝试融入宝水村的能指链条,这便逐步形成了“土话—普通话—土话”的主体话语构建过程。
二、镜像场域的碰撞:追寻主体的助推器
拉康认为,在可供观测的场域中,自身是被凝视的一幅画,对镜中世界的旁观定会造成对真实本我的构想。文本提供的客观具象影响着主人公主观内心的情感世界。在主体身份的认知与建构的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自身存在的场域。在《宝水》这部作品中,宝水村和福田庄、九奶和奶奶这两组影响因素构成了影响地青萍身份建构的镜像场域。从他者的投射中,她会不由自主地将自我的成长经历形成比对,这充当了她在宝水村中形成主体意识的助推器。对地青萍来说,从福田庄到象城再到宝水村,她不仅重新获得了再度踏入乡村的宝贵机会,同时也迈进了一个二次审视主体和情感记忆的镜像世界。
从村庄的角度来说,在宝水村的日常生活与人情往来会无意识勾起主人公在福田庄的记忆,所以她用福田庄的主体来尝试构建自己在宝水村的身份,在此过程中她产生了明显的情感变化。如在与老原基于二者进行关于老家的对谈中,老原说宝水村与福田庄一样,都属于怀川县,怎么不算老家时,地青萍用五六十公里的距离为自己构建了一道厚重的心理屏障,她认为自己只是参与性的旁观者,所以她说:“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乔叶《宝水》)但提到“水”时,地青萍却因“宝水村”的村名含水,而勾起了自己对福田庄算命五行缺水和七十二个泉眼的记忆。看到宝水村的老祖槐便能想起福田庄院子里的槐树,从聪明伶俐的曹灿身上看到了小时候在福田庄生活时没心没肺、胡天胡地的自己。她将自己对乡村的依附感投射到了宝水村的一切,所以她已经开始从旁观者逐渐步入了“既内且外”的阶段。
在地青萍以宝水为镜重新体认乡村与自我的过程中,老原的亲奶奶—九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九奶的存在让地青萍想到了与福田庄联系最为密切的、自己的奶奶。比如与九奶一起睡觉时,她回想起小时候因那封“玉兰吾妻”的唯一信件与奶奶共同经历的“闺密”夜谈;关于人情,九奶与奶奶都有着各自的态度:九奶为了救人而受伤,她说:“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这一辈,哪能只顾自己。”(乔叶《宝水》)她的仁义与智慧也映照出了在福田庄的奶奶煞费苦心“维人”的道理:“人情似锯,你来我去。”截然不同的情感牵连再一次激发了地青萍对人情的再理解与再认识。回想起奶奶这套人际往来的方式间接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她失掉亲人的苦痛以及对奶奶“维人”道理的逃避与苛责,构成了自己对奶奶和福田庄诅咒与厌恶的来源。
经过这两组镜像场域的碰撞和对自我本质的探寻,地青萍获得了多次镜像认同,逐渐在宝水村找到了主体的复杂情感,主动迈出直面过去的脚步。那些曾带给自己苦痛与悔恨的回忆,她也不再将其悬置上空,而是选择向内窥视,并自我接纳。她因失眠症将自身从大城市中抽离后来到宝水村,再度被激活的土家话使她在与村民的交流中如鱼得水,重新衔接上了语言的能指链。地青萍从人际交往与情感体验中实现了对乡村逻辑的重新梳理,不仅包含了自己内省性的身份探索,更是在他者的世界中逐渐看清了主体身份的本质,并将多股错综复杂的情感纽结进宝水村这一“大他者”中。
三、和解的达成:身份建构的最终确认
在与大英、老原和杨镇长等村民的人际互动中,地青萍感受到了疗愈的力量,从初期的身份隐忧和保持悬置的参与观察,到逐渐融入与不断内省,终于在最后与过去的自我达成了和解。土话与普通话的先迭更替让她在自身的语言系统里不断完善着自身与再构建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他者”帮助“主体”找到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后镜像时期。
面对之前伤害过父母亲的福田庄,带着创伤性记忆的地青萍一直对它保持着厌恶与躲避的态度,甚至等奶奶咽气之后才赶回故地。望见平原旷野时,老原询问她是否见到福田庄时,虽然没有真的看见,但她心里却想着:“可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看见她嘛。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我看见她。”(乔叶《宝水》)主客观的矛盾展现了她内心对乡村从对峙到和解的心理过程。她对九奶更是将其视为自己在福田庄的奶奶,有了一种不愿看自己的奶奶再死一次的依恋。最后,当七娘替奶奶转述完“能恨出来就中。不闷着就中”时,地青萍终于为她落下了眼泪。九奶去世也让她想起了奶奶去世前的以“好”为终结的话。在九奶和宝水村的感召下,地青萍产生出了一种诅咒越毒、心里越痛的愧疚和忏悔心理。主人公既介入又悬置的叙事姿态终于在最后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获得了更贴近村庄内部的观察位置。地青萍在乡村中得到了疗愈,最终完成了自我的身份建构,在他者和主体的统一中走向趋同。
地青萍完成了身份建构的过程,也显影出了土地、风俗对人精神创伤的疗愈与修复。作者很注重小说中“土地”的描写,写道:“最能让人较真的也就是地。”主人公的姓氏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用意,可见在地青萍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土地始终与她产生着紧密的联系。她作为适应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来到另一个陌生的乡村,对未知生活的隐忧和对福田庄的怀念与逃避催生了她的身份焦虑,但宝水村自然风貌和风俗文化的和谐统一使她在镜像场域的互动中强化了建构主体的自信。宝水村的自然环境无声地建立起对主人公的保护机制,让地青萍在主体与他者对话、碰撞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我。“花草不分家”中铜锤草和金鸡菊两种花卉吸引了地青萍的注意,她闻到它们细细的香气时,竟也觉得“有一种神奇的治愈性”;她哄睡九奶后和老原返回中掌的路上,看到了淡如牛奶、无处不在的白雾,呼吸间发觉自己早已与它互相融合,化作了它的一部分。除却自然风光对返乡者的疗愈,村庄的风俗文化也不断加深她与宝水村的联结,不管是摘香椿、打艾草、闷坛肉还是“扯云话”,作者精心雕琢的日常生活正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治愈着地青萍的身份焦虑与精神创伤。对宝水村的现代化治理也在拉高主人公在乡村生活的存在感,“孟胡子”建立宝水村村史馆的提议勾起了她对福田庄记忆的回味与依恋;她的创意使名为“一青三梅”的抖音账号扩大了村庄的影响力,赶上了乡村旅游热的浪潮;地青萍和利用假期支教的研究生畅聊的“废话文学”也让自己逐步适应着城乡流动过程中的身份转换。作者乔叶的用意不只是让读者了解地青萍在宝水村找寻自我的过程,更是想揭示出现代人“还乡”情结对土地、乡村的亲昵。
借助拉康的镜像分析理论,《宝水》中地青萍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审视,影响其身份建构的场域因素也在她自我认同的路上被收集、探索,最后得出她达成了自我和解的圆融状态这一结论。这不仅折射出人本身对所居土地既依恋又逃避的情感,还体现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主体与他者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能聚焦到土地与人之联系的思考和对命运的敬畏,以及隐现出的乡土精神文化对身份焦虑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