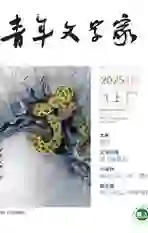寂静的清晨
2025-02-20水色云裳
我是小区里个子最高的路灯,站在进出小区的中心位置,左侧是路,右边是休憩的广场,前后是高高的杨树,在他们中间,我是夜晚最“亮”的仔。
蜿蜒的路像琴弦,一端锁在小区里,另一端通向未知的斑斓。上班、上学、赶公交车,各种匆忙,在左侧道路上流淌,而右侧截然不同—打太极拳、跳广场舞、下棋,慢得悠闲,像草原上的羊群,尽情享受日光、月光,还有我的照射。
只要灯泡不耍脾气,我就可以长期不被打扰。黑色收腰窄裙,穿了十几年,颀长的颈上挂着羞涩的圆脸,随风摇摆。太阳得意的时候,我闭目睡去,等太阳慵懒地离去,我才睁开眼睛。
与黄昏相比,我更喜欢清晨。黄昏过于匆忙,忙得想在路上就把家里的灯点亮。比黄昏深一点,出来遛弯儿的、健身的、聚会的、闲说家长里短的,过于拥挤。更深的夜又太清冽,除了一两个晚归的路人、落单的野猫,我要独自冷好久好久。但是,清晨就不一样,越来越有烟火的味道。
哗啦,哗啦,扫把的声音越来越近,老王头儿跛着脚,哼着不变的曲儿,还是那身发旧的橙色工作服,保持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用力姿势,有节奏地准时过来。抬抬眼,面前八楼一号果然有亮儿了,那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人姓陈,微胖白皙,热衷于研究美食,儿子复刻了爸爸的DNA,又黑又瘦,刚上小学。她坚持早起,钻进厨房,闭紧房门。点一盏橙色的小夜灯,开始熬粥,一下一下轻轻地切菜,或煎或炒,尽量不发出声响。即便这样精心,还是常常提不起儿子的胃口,只有好奇的小夜灯在蒸汽曼妙的厨房里恨不能跳入锅中,品尝她的杰作。
对门的灯也亮了。七十多岁的张大妈先下床,一边从床底掏出老张踢进去的拖鞋,一边唠叨“天天这样,就不能自己放好吗?”然后,扶着床边捶捶自己的腰,开始洗漱。张大爷也起来收拾妥当,摸出手机看天气预报,开窗试一下外面的温度,准备出门晨练。他们不用做早餐,连午饭、晚饭也可以省略。社区助老餐厅很方便,两种粥,四样主食,六个菜品,吃得饱,吃得好,还物美价廉。前天在广场上走圈的几个老哥儿夸张大爷“老张两口子多潇洒,都不用开火”“人家儿子了不起啊,是博士后”……张大爷扬扬头,摸了摸光亮的脑门儿,脚步轻快了许多。等他走远了,刘爷爷才哼了一声,“有什么用,好几年没见回来,过年过节还得对门小陈两口子照应着!”
怎么还没见四楼一号亮灯?这几年有业主多次反映,他们家噪声太大,又是蹦又是跳,能开戏班子。昨晚,他家的吵架声更大。欢欢弹琴总是出错,被妈妈训斥得一直在哭。欢欢妈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就是打个鸡蛋,把鸡蛋壳刮漏,也不能放过一滴蛋液。不止如此,她还强迫欢欢爸戒烟、戒酒、戒朋友,下班准时回来辅导孩子功课,钱都用来报各种兴趣班。欢欢学得如何不知道,欢欢妈就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了。这次欢欢爸终于爆发:“还有没有家的样子!每天鬼哭狼嚎,不是学跳舞就是学弹琴。全家人多久没睡一个囫囵觉了。”欢欢妈啪一下,把曲谱摔到钢琴上,振得自己好心疼。“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孩子好!”欢欢肩膀抖动着想:我又该为谁好呢?
粉红色的光从十一楼二号伸出来,窗上的“喜”字还很新鲜,小周两口子也起床了。他们的工作单位离得远,得早些起来。
五年前的一个晚上,小周被人搀进小区,扶着我呕吐,弄脏了我的脚。七尺男儿,眼泪和着鼻涕又甩我一身。毕业的风吹碎了他的梦,爱情的花儿也顺势逃走。于是,我和我脚边厚重的黑土掩下了他那晚的狼狈。从做代驾开始到如今西装笔挺,他的公司生意红火,还买了属于自己的车。两个月前领回一个姑娘,红红的“喜”字,引得整个小区的花儿都提前开了。小周妈来广场给老姐妹们撒喜糖,说女孩儿几年来一直陪着小周,她抹抹眼角,真是让这闺女受委屈了。
树屏住呼吸,我也感觉到有人走进了小区的大门。看那忽明忽暗的影子,还有负重的单薄,我就知道是十五楼一号的亲家—杨阿姨来了。小两口儿去援疆支教,孩子放在奶奶这里,因为奶奶家离学校近。听说新疆那边天黑得很晚,亮得也晚,他们应该还在睡梦中,梦里有没有妈妈的味道呢?
杨阿姨总是早起蒸包子、送饺子、送菜。不知道她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只见她提着保温桶,又挎着从早市买回来的青菜、水果。果香夹杂着天然的植物清香,回应着露珠的问候,悠悠飘来,它们张大嘴,并不发声,尽情呼吸,再闭上眼睛,融进寂静的晨。
整个小区,无数窗,凝视着黑夜。黑夜落下帷幕,所有的窗都变成同一个模样。如果只有一扇窗,是多么孤单。这么多窗,被楼房聚在一起—有的怕黑,有的失眠,有的暴躁,而更多的是找到了温暖……
一扇扇窗,亮了起来。清晰的、模糊的,行色迥异,我同身边的道路和广场相视一笑,是时候离开了。
相信每一扇窗里,都有很多美好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