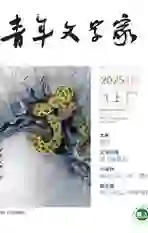我与文飞文坊
2025-02-20朱徐雨
我与文飞文坊的故事要从十岁那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开始。
因为一些机缘,经过相熟的朋友引荐,我加入了一个叫“文飞文坊”的写作班。
每周五晚上七点,我坐着地铁一号线,在乐桥站下车。走出地铁站,穿过窄窄的、老旧的小巷,到达这个大石头巷的一个大院门口。大院门口是一家面条店,我路过了无数次,也在内心说了无数句“改天一定要来吃”,却从未踏进过一步,现在想来也是憾事一桩。
从大院门进入院子,先是看到一道老门。当时的我从未想过门内是另一番天地,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看到这道门后往右拐,便是一棵参天的老树。径直走到大院的最深处,就是“文飞文坊”的入口。推开玻璃门进入走廊,左手边是韩树俊老师的个人简介和夸张的肖像画—这大概是我对韩老师的第一印象。沿着走廊进入教室,就是文飞文坊了。一块硕大的黑板、一张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的讲桌、四排木头桌椅,还有放在教室后面的一帧书法“文飞文坊”。这些简单的陈设集中在一间略显逼仄的老屋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编织起了我的童年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还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我是第一个到达教室的。那时候的我性格比较内向,和韩老师打过招呼后,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抱着上“作文补习班”的赴死心态,我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每个走进教室的同学。他们似乎并没有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哭丧着脸,但我仍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第一节课的内容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记得我被韩老师叫上讲台,讲过去一周在学校发生的趣事。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能胡诌。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一直都不太好,说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因为紧张而有些语无伦次。我讲完后,一个调皮的同学举手说,她仔细数了数,我一共说了二十三个“然后”。于是,所有人哄堂大笑。后来,那个调皮的数我说了多少个“然后”的同学,和我成了同桌。她永远都带着小说杂志和我分享,我们也在上课的时候讲小话,她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也要写小说”,语气自信而又坚定。
从那以后,我每周都在这间小教室里听韩老师讲课。听他讲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过去的大石头巷、陶行知的故事;听他讲生活中拾起的点点滴滴的诗的碎片—姑苏水八仙、他刚去黔西南布依族采风的所见所闻、他小孙儿的妙语连珠……除此之外,我们也能讲。我们讲过去一周在学校发生的趣事、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所思所得。或许语无伦次,或许童言无忌,只要是一个故事,就能登上讲台。讲完了,韩老师便让我们写。每周都写,作文纸积成了厚厚的一沓,至今都在我的书房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很庆幸,我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记录下了那个社交媒体并不发达的童年时期的“黑历史”。其中有一些感觉良好的练习稿,经过打磨、汇编,有幸登上了一些报刊,成为我平凡的人生履历上不平凡的闪光之处。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记得我在“文飞文坊”的一节课上,韩老师指着我身后的那一副字,说:“在书法作品中,相同的两个字一定有不同的写法,‘文飞文坊’四个字中的两个‘文’字写法就不同。”我回首—一个“文”笔力劲挺,一笔一画,端端正正,骨气洞达;另一个“文”连笔,秀逸潇洒,行云流水,飘逸洒脱,字体果真不一样。许多知识,我们就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明白了,记住了。
我参加的课程名字,叫“小作家班”。我曾经一直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现在想来其实“文飞文坊”的每个孩子都是真正的小作家,至少在大石头巷的大院里,是能提笔描绘眼中世界万物的小作家。我们写的不是应试作文,而是自由的诗文。就这样,我在离开了老师旅欧夏令营的那段日子,我不由自主地写起了诗日记,又是韩老师第一个在我的微信里像发现珍宝一样发现了我的诗日记,他欣喜地代我向《散文选刊》等一一投稿,居然都发表了。
后来,我由于学业繁重,离开了“文飞文坊”。但“文飞文坊”早已在我的心中扎下根来,只要我提起笔,哪里都是“文飞文坊”。是的,初中毕业那一年,是韩老师把我推荐给《散文选刊》(原创版)编辑部的,让我成为签约作者,有幸在北京听多位知名作家的讲座。著名作家梁晓声抚着我的肩膀和我亲切合影,并为我题词:“祝徐雨同学写作实践不断进步!”高中毕业前夕,在高考备考的日子里,韩老师推荐我参加首届“长三角青少年散文大赛”,我很荣幸获得了银奖。有意思的是,这次“长三角青少年散文大赛”,苏州大市(含四县市)总共获得一银两铜,还有一位铜奖得主,也是我们“文飞文坊”的同学。我们两位“文飞文坊”同学的现场获奖征文刊登在了《中国作家》杂志,并成为韩老师主编的《蓝月亮" 红月亮》(苏州十位“05后”小作家诗文集)一书的作者之一。
尤其令我欣喜的是,进入大学的我和另一位获得铜奖的同学,我们有幸一起跟着韩老师,汇聚在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文飞文学社的旗下,一起放飞我们的文学梦!